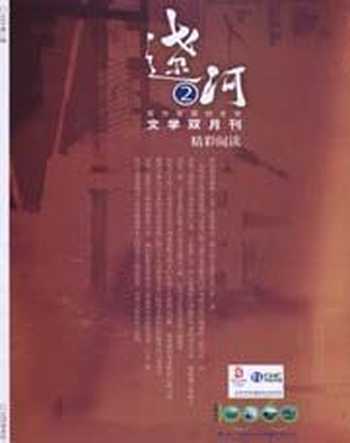散文四章
淡红深碧挂长竿
什么地方没有缸?石门的缸让我有印象。以致我觉得石门就是一只缸,石门的丰子恺故居也是一只缸。丰子恺故居这一只缸里,我第一次去,装满黄酒,杯盘草草供笑语,灯火昏昏话平生,这两句诗如果没记错,是王安石妹妹的绝妙好词;第二次去,相隔不到五六年,丰子恺故居这一只缸里,对面青山绿更多,我觉得装满掺了水的黄酒,味道不对了。尽管我对黄酒兴趣不大,喜欢喝啤酒。
黄昏,我从丰子恺故居出来,黑漆漆的门发出摇橹一般声响,在我身后摇上。码头,石门像码头的话,码头上没几个人,形体黯淡且瘦。抽烟的;咳嗽的;一边抽烟一边咳嗽的;帽子下警觉的神色;老头;老头。我在石门镇上瞎转,走进供销社,瓶子里装着红红绿绿的硬块,我知道这是糖。肥皂。套鞋。柜台里还有连环画,是营业员自己的读物。我看着那个已过中年的男营业员,他见我进门,忙放下连环画,朝着我看。我就买了一盒火柴。他坐下后我走到农具柜台前望了一阵。
第一次去丰子恺故居,许多房间都没开放。我觉得好,有想象。想象丰子恺在这间房里喝酒,在那间房里读书,或者干一点不可以给我看见的事。这多好。后来再去,修茸一新,全都打开了,成了展览馆:到处挂着复制品。有一件很有意思,是丰子恺代孙子还是孙女捉刀,画了一个红小兵在听半导体,图画老师在上面打了个分:“良”。想象丰子恺的孙子孙女回家,缠着爷爷不放,我们作弊,让你代笔,结果还是没得到“优”,早知道自己画了,也不用老忐忑不安的,怕被图画老师发现。啪啪啪,揪下丰子恺三根胡须——为什么是三根?他们要去玩三毛流浪记。一个丰子恺,一个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中国这两个艺术家,对孩子是真有体会的。但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或者足同的,都为了吃饭。
丰子恺故居外有一块空地,临河萧散,连野草也懒得从泥里爬出。是一块泥地,颜色较深,一直没干的样子。现在想起来它的尺寸大概有我读过的干将小学的操场那么大小。在这个操场上,却只有三只缸。一只缸独自站立,在那里练习立正;两只缸套在一起,在那里练习叠罗汉。不知道会不会跑来一个愣头愣脑的体育老师,他刚从师范毕业,浑身是力,把挂在胸口的哨子猛地一吹,让三只缸排成一队,绕着丰子恺故居连跑六圈。
这三只缸是何用途,我颇费周折。问了几个经过我身边的当地人,他们瞧瞧我,咕哝一句,立定两脚,陪我一起看,有个人还走上前去,敲敲一只缸,回过身来瞧瞧我,再敲敲另一只缸,最后回到我身边,继续陪我看。
其实我在打听这三只缸是何用途的时候,已经认定它们是染缸。即使它们是米缸、酒缸、水缸,或者是从陕北长途跋涉而来的酸菜缸,我还是认定它们是染缸。问问当地人,无非是听听石门话吧。结果他们咕哝一句后,再不说话。
从书本上看来,丰子恺家是开染坊店的。放在民国二三流小说里,他就是一个怀着理想去日本求学的染坊店小开:梳着分头,抹着发油,戴着金丝边眼镜,一身缩水西装,皮鞋却怎么也穿不惯,常常穿的还是黑布鞋。这形象更像郭沫若。但我真想象不出丰子恺当初东渡之际的形象。丰子恺在我的生活里,是没有少年,也没有青年的,他是从中年开始,渐渐须发皆白。
范成大有句诗“淡红深碧挂长竿”,说的是染布卖布的小贩。用来说染坊店也是传神的。用来说丰子恺的绘画也是押韵的。他绘画中的色彩。丰子恺绘画中的色彩极其鲜艳,他是在染坊店玩大的,淡红深碧,耳濡目染。这么说毫无道理。在酱油店里玩大的,他就乌鸦一只?朱屺瞻不就是酱油店里玩火的小开,他的画照样五颜六色。“屺”在古书上指的是光秃秃的山,朱屺瞻郁郁葱葱地活了一百岁。
夕阳独红,大家普蓝。
怎么又黄啦?防冷涂的蜡。
淡红深碧挂长竿,底下坐着个丰子恺。
三只缸,排成队,石门镇上跑起来,咕咙咚,掉下水,呼噜呼噜沉没了。
墨黑一段滋味
从黄山上下来,下雨了。一过黄山,雨就停了。我上次去黄山,也是如此。两次都在歙县住了一晚。歙县一带现在好像全改了地名,乱七八糟的,我也没能耐记住。第一次从黄山上下来,到歙县已是夜晚,在招待所放下行李,洗了把脸,趁着月色去看八角牌坊,黑黝黝的,直挺挺的,与一盒劣质的徽墨差不多,在凉气和祖母绿的猫眼中磨得咯吧咯吧响。有位迷恋西方现代主义丈学的小说家,她捅捅我腰,满面惊恐,神经质地说这是卡夫卡的城堡。我听了,竟然一阵颤栗。不知道是卡夫卡的城堡还是她的手指让我如此颤栗……咯吧咯吧响。那时年轻,大家年轻,看完八角牌坊,敲开一家店门,买了几瓶烧酒,都兴冲冲地跑上碎月滩,唱歌,喝酒,或站,或躺。也有躺着躺着睡沉了的,说起梦话。自深夜至月色渐淡,鸡鸣渐起,脱衣作席,彻夜饮酒游玩,这是常有的事。碎月滩上,女子面容娇好,男子争风吃醋,争累了,吃累了,亦与水声、月色交谈。众人皆悠闲自在、吟歌喧闹,松尾芭蕉曰“有人衣裳浅柿黄”,此句最得悠闲的味道。上黄山的事我是记得的,在碎月滩上彻夜饮酒游玩,就忘了。去年读到松尾芭蕉的俳文《四条河滩纳凉》,碎月滩忽然雁落平沙。日本的俳文,学的是苏东坡之流的笔法,随意到了,天真与酣饱还没有。岛国的气太急,因为在弹丸上刻经。
印象里,碎月滩的边上,独耸红楼,像打开装水果的纸板箱,鸭梨的香气朝我撞了过来。我问过安徽的画家老许,他说没见过有那幢红楼。那是我的红楼梦了?歙县过去是个海,那是我在碎月滩上见到的海市蜃楼的回光返照?
那幢红楼里,黄宾虹画着画。黄宾虹是中国传统绘画在他身上的海市蜃楼,也是在他身上的回光返照。人一说起安徽,我就想到黄宾虹。黄宾虹是安徽的指示牌。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有关黄宾虹的随笔。二十多年前,我喜欢许多艺术家,现在没几个留在心里了。但对黄宾虹,还是欲罢不能。我对黄宾虹的认识是“蓬头垢面,天生丽质”,没人会这么说。我以为黄宾虹的花鸟画比他的山水画更有意味,这意味在于江南对于一个人的滋养。以后也会有人以为车前子的散文比他的诗更有意味,已经有人这么以为了,结论也是这意味在于江南对于一个人的滋养。但这是不同的。我还是写我的诗。写诗是我的天分,写散文则是修来的,我自己明白。
近来寒暑不常,希自珍慰。
近来我上了趟黄山,是与妻子同游。从黄山上下来,到歙县的路途上,看了几个景点。我都兴趣不大。安徽的民居像密不通风的卧室——病人或者产妇睡在里面,黑压压,看不清,也没什么好看,卧室里就一张架子床。对我而言,安徽民居就是一间卧室或者一张架子床,喘不过气来。如果我的前世生活其中,侥幸没死掉的话,也会成为革命者吧。我觉得这样的建筑风格构成大背景中的风水,它会产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而是杰出为能够与世无争的革命者,因为安徽民居同时也是深不可测的、学有所养的、与世无争的。真正具有革命观念的革命者,他能做到与世无争。他反对权力。他反对权威。当他所处的时代只剩权力和权威了,他就深不可测,用学术与艺术来保持尊严。在我们历史上能用·学术与艺术来保持尊严的人在我看来都是真正具有革命观念的革命者,越革命越与世无争。他在革自己的命。到歙县已近黄昏。第二天去歙县的老街转转,旅游点兜售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我还是大有所获,吃到了一种小吃,叫“徽墨酥”,也就是芝麻酥糖。糖度、酥度,恰到好处。把芝麻酥糖叫“徽墨酥”,安徽要打墨文化的牌了?安徽出墨,不是人磨墨,而是墨磨人,墨不但磨人,还能轻易地把什么抹黑——我小时候学写大楷,用的就是徽墨,知道这一点。
红菱艳
独坐桥头,水巷冷冷清清,但并不暗。这是古镇同里,为了旅游,把电线杆都拔了,电线埋在地下,路灯从墙上冒出,愣头愣脑,更显得孤单。偶尔走过的人,他们的影子会晃动到水边的合欢树上。合欢花早谢了,叶子也就肆无忌惮地交叠一起:发出沙沙声,如果起风。
有一天风真大,院子中的树都要往房间里奔跑,床单与外套在麻绳上魂不守舍。
以前我到过这里,电线杆都是木头的,很有味道,像黑白。电影里的一个个镜头——慢慢的过去,会有人在那里等的,摇着折扇。折扇的一面画着枯藤、草堂、远山。
河里泊着木船,全是些游船,白天有穿着蓝印花布的船娘,在流水中挣份饭钱。船娘的脸都黑黑的,说不难看就不难看。
走下桥,转个弯,沿着驳岸稍走几步,下午有一个油炸臭豆腐干的小摊,它只在下午摆出:
傍晚去吃油炸臭豆腐干,在乐乡饭店前的河边,是同里最好的一家,摊主自己用苋莱杆做的臭卤卤制而成。吃了十二块。吃油炸臭豆腐干一定要蘸平望辣酱,只有平望辣酱才能更好地把油炸臭豆腐干的暗香激活。
这是我从2004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摘出的。这些日子,没什么好写的,我就记记日3L:让我还有一个在写的感觉。否则会越来越厌烦了。
在油炸臭豆腐干的小摊前,前几天有一辆黄鱼车停在那里,一个半老的女人坐在车上,脚边是几只塑料桶,一只塑料桶里装着红菱。
其实是泡着红菱。就为了增加点重量,红菱都被泡得发白了,甚至有点浮肿的样子,仿佛得了绝症。
正是吃红菱的好时候,到了水乡,我却一次也没有吃,除了浮肿的红菱让我不舒服外,还有另一件事,像强迫症一般。去年我把历年所写有关吃的随笔编成一本书,其中也有红菱。出版公司想做成图文本,就插了许多图。我翻阅校样的时候,或许是插图太多的缘故,编辑忙不过来,我发现在红菱的丈字部分所插的一张图,像点石斋的画风,上面有“红菱”如何如何的字样,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一班人马在玩赏女人的小脚。我这才想到红菱的确还有另一层我不会想到的意思,从此常常想到了。你说恶心不恶心!
不写红菱了,写写同里吧。但一时又不想写,就把日记中的同里摘出:
(2004年9月20日星期一,晴)四周寂静,九点半,对小镇而言,已经是深夜了;在北京,此时好像才是生活的开始。
(2004年9月21日星期二,晴)同里的旅游资源其实贫乏,只在三桥一带。昨天傍晚小祝与周先生和装修者交涉,我就去镇上转转,老陈坚持要陪我。在三桥的其中一座桥下,有渔鹰表演。渔鹰苏州话叫“水老鸦”,因为通身抹黑如乌鸦也。老陈说,“水老鸦”叼的鱼不及钩钓网捕的鱼有鲜头,鲜头都被“水老鸦”先吃没了。这倒是第一次听说。但我想总比用炸药炸毒药毒的鱼鲜吧。有一时间的渔利手段是用炸药和毒药,市场上兜售的都是死鱼,有的血肉模糊,有的颜色奇怪地发青发黑。恐怖主义无处不在。
(2004年9月22日星期三,晴)站在住处的楼道里,朝底下望,老房子和它的院子很有情意。
(2004年9月23日星期四,晴)晚饭后在三桥一带散步,雾气茫茫。
(2004年10月6日星期三,晴)中午出门吃饭,只有白烧螺蛳还过得去,小饭店觉得与我们熟了,就乱烧一气,咸得卵泡都掉了。吃完饭在三桥转转,今天老外较多,有一与乞丐差不多的本地老头,见老外拍他照,就索钱,他张大了手掌,五根黑手指粗糙地微笑,意思是五块钱,老外掏了半天裤兜,掏出了一块钱,老头接过一块钱,继续晃动五根黑手指,老外就上前拍拍他肩,咕噜咕噜给老头上课。与周先生坐在桥栏上想看美女,一个也没见。一个三十左右的女人边走边咬着绿色的菱角,臀部掉在膀弯弯里。
(2004年11月1日星期一,晴)傍晚与周先生在叶家墙门一带散步,还能感觉到一点镇上人的生活。后来转到明清街附近的一条街上,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逛了两家小古董店,店主都很奇怪。第一家一见我们进去,店主六十多岁,就说我这里都是老末事,你们别碰。周先生与他闲聊,他就说谁,谁谁(古董行里的大腕)都是从他那里拿东西的。我想买几个筹码,他说倒给你先看见了,明天吴江的某某领导要来,他专门收藏这个的。搞得我没了兴致。第二家的店主是小伙子,闷头在那里玩电脑游戏,我们在那里看了一件铜器和一件木器后,他就气鼓鼓地说,我这里没老末事的,全是新东西。走到大街上,见点心店有买袜底酥的,就买了五只,两块钱。我见点心店里苍蝇狂飞,就对店主说有苍蝇,你给我拿底下的。店主拿袜底酥的时候一边赶着苍蝇一边说:“今天没有苍蝇”。以致吃晚饭的时候我与周先生一想起这件事就乐——“今天没有苍蝇”。
还有一些,不想摘了,越摘离红菱越远。我曾经把红菱比喻为江南的肚脐眼,这就是报应,因为既然是肚脐眼,那么肚脐眼里总会有脏东西。
南浔夜雨
三点半到南浔,南浔与苏州这么近,我却是第一次来。舍近取远,人之常情。
又:
南浔。小莲庄:清光禄大夫刘镛的庄园,始建于光绪十一年,占地二十七亩,由义庄、家庙和园林三部分组成。园林分内外园,外园以十亩荷池为中心,内园湖石纵横,仿杜牧《山行》诗意。因为要随大流,不及细看,但估计也没什么‘好看——气息上就不对。
这两则日记——虽说是从我自己的日记中抄出,但还是抄。我现在写文章常会抄上一段,有时还是一大段,看来是未老先衰的症候。老了,认了。
我在南浔呆了两天,其实是一天。下午三点半到的,翌日午饭后离开。在南浔的时候天气晴朗,我却有夜雨之感。为什么?努力弄出点诗意呵,否则坏了我的幻想。我对南浔足有幻想的。南浔给现代文学史贡献出一位很好的诗人,尽管诗单薄些,也混杂些,质地倒是上流,甚至可以说是天才的。我看过他的自传体小说《江南小镇》,说到了他在南浔的往事。
如今的江南小镇,虽说人的生活还在其中进展,但都城市化了。
以前江南的所有小镇都可以拿他的诗作比,单薄,混杂,而质地上流。不会像平遥那么乏味。我觉得平遥只有一棵树——一棵苹果树,在黄酒点心铺的院子中。我再去平遥,这棵苹果树竟然还死了。没有植物的地方,风土当然乏味。虽说乏味在那些艺术家眼中会显得浑厚,或者说有思想。
所以小莲庄后面那一片香樟林,使我徘徊。主人在树下喝茶、饮酒、谈情说爱,女人的脸浓浓地绿了,樱桃小嘴在这一张脸上,像被大片芭蕉叶托住。
南浔的著名建筑物,皆有中西合璧交错的阴影,商人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我觉得南浔的建筑物对那位诗人的熏陶,超过流水对他的影响。
散就散吧,南浔的景点比较散,开发者雄心勃勃想把它们串起来。本来还是不错的珍珠,现在要用麻绳去串,又不是上吊,要这么粗的麻绳干什么!
置办酒席的厨师真的消失,满世界全是卖盒饭的伙计了?
藏书楼的院子宁静,几个当地人在河边喝茶,我对同游的老刘说,不错。它与小莲庄一河而隔,我坐在那里,还能看见小莲庄的香樟林,林中正有一位红衣姑娘洗脸洗头,铝皮的脸盆搁在骨牌凳上,水从黑发间滴落,周围湿了一圈。土的色泽深了。
平日我爱睡懒觉,出门在外,又有同游者,只得早起——大伙儿一起去吃早饭。街头和空气一样清冷而潮润,地面上充满水分,我的南浔夜雨或许与这有关。爱睡懒觉的人对早晨是有幻想的。经过一座桥,桥上零星地摆着菜摊,还有一辆卖定升糕的手推车,糕的颜色红得像假古董,我就不敢吃。据说定升糕是南浔特产,一如嘉兴粽子。我至今还为我没吃南浔定升糕而耿耿于怀,我吃过不少地方的定升糕,就像许多画家画马,而作为徐悲鸿的特产,没见到他的总有遗憾,至于好坏,另说。我在手推车前站了一会儿。我一会儿看摊主做糕,一会儿看他身后的一座桥,也就是我正站着的这一座桥对面的一座桥。
我正站着的这一座桥是水泥的,对面石头桥,桥拱高过两岸水墨的屋顶,一只燕子轻飘飘地桥洞里飞着,那位南浔诗人过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