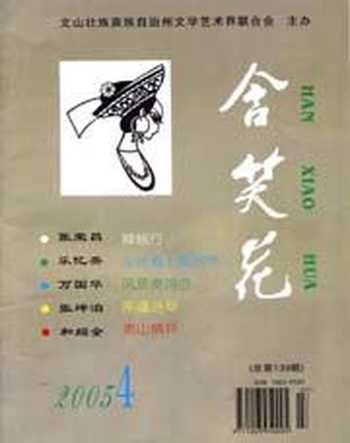梦里落花知多少
郑长春
曾有过多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云”的感慨;也曾有过多少“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惆怅;也曾有过多少“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的无奈。
站在时光的脊背上,看着人来人去,世事沧桑,岁月留痕;看着朝露日映,年华逝去,时光如水;看着人的“暮年岁除,老之将至”转眼间——也就是那历史长河的一个漩涡,我已步入了18岁。
十八年来,我并未经历过什么坎坷和磨难,只是一如平原跑马,快乐地生长在这多彩而无奈的世尘之间,似乎早已忘记了何谓伤心,何为失意,何谓对世事的无奈。
惟一能令我感动的是,那悲壮的落红。那寂寞梧桐深院,那—地太阳走过叶脉留下的斑斑点点……
记得年少无知时,我曾对这满庭的落花,不胜嘘唏,就像一位岁月垂暮的老人,对着即将要沉睡的夕阳,发出凄凉的叹息。然后,把落花堆积一处,随着风刮日晒,小心埋人地下。那时的我,已似懂非懂地感悟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悲壮和伟大。
再大些时,我到华山观光旅游,满怀憧憬,登上山顶,面对那远如青黛的群山,悠悠然,为自已似乎感觉到达了人生的巅峰而振臂高呼。那时那地,我终于读懂了杜甫的“荡胸生层云”的豪迈,体会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豁达。
当时钟沿着固定的轨迹,每天准时地爬进深深的夜幕,我就会闭眼任思绪驰骋在我脑海中的群山峻岭,深谷秀涧;驰骋在那奔流到海不复返的黄河之上;驰骋在浩浩荡荡横流不尽的长江之上,看“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悠闲和自得。
博古览今,由此及彼,古往今来,历代文人骚客描写最多,竟是那一幕幕令人心醉神往的高山流水,碧海长天;那一阙阙优美的诗词歌赋,无不诉尽了人生在世的最终归属——回归自然。
当所有的一切都已看遍,我就再无奢愿。可天下之美景,岂能用肉眼体察得清么?
渐行渐远的历史车轮,碾碎了我多少年轻的美梦。山已不是绿山,水也不是碧水。看那葱葱如盖的绿树,已被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所代替;潺潺的,涓涓的,清澈透明的河流,已被五彩缤纷的颜色所感染;那如诗如画的山峰,早已为迎接“开发”,创造经济效益,被利欲熏心的“弄潮儿”换上了土黄色的人工外套,摇摇欲坠,不堪人目,像遍地生花的“牛皮癣”。
我的梦想,也被碾碎在,渐被风化了的人类的意识行为下。如诗的思绪再也推敲不出该用什么来“赞美”它的“时尚”,如歌的喉咙再也唱不出岁月迁移带来的“进步”。
惟有怀念。也只有怀念那曾经年少,在树阴鸟鸣中,我酣睡的一觉,却不觉朝露沾衣;怀念那些因远眺群山,而激荡出的泪水;怀念那些乱红飞过千秋时,我不由自主的感叹……
惟有怀念。惟有怀念是真。
但愿多年以后,我还能乱红飞处,蓦然,凝眸回首,看尽那绵绵的风土人情……
乱红飞处,凝眸回首,不知一切真如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