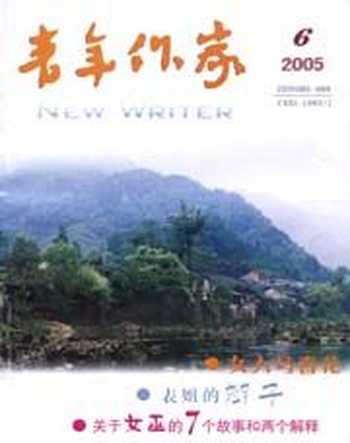太阳花
西门媚
天花板上有一张脸。
几天前,那张脸是一个半鸟半兽的怪物。现在竟变成一个傲慢无比的富家女子。中间还经历了许许多多。
贝宁在床上已经躺了多长时间了,她都不想去算算。每天只盯着天花板看。每睡一次,天花板上的印子就可能变一个样子。
贝宁陷入低沉的情绪里已经有很长一段日子了,原因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越来越不快乐,渐渐地睡眠质量变得很差。可能是冬天的原因吧。冬天的这个城市阳光很少,贝宁的办公室又是冷灰的调子。同办公室的杨晓到外地分公司去支援半年,办公室只剩下贝宁一人,每日守着两台电脑,两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复印机。偏偏还没什么工作,贝宁在办公室只好每天发呆。自从隔壁的办公室开始装修,贝宁听见电钻,闻到香胶水的味道,就开始持续的头痛,回到家里又很难入眠。贝宁去看过医生,医生说,这是初期的抑郁症,建议贝宁服药。而贝宁却想的是请假或者辞职,因为她太烦了,想着每天早上要从温暖的被窝里起来,缩手缩脚地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她就觉得难以忍受。
可贝宁并没有向领导提出什么,找领导她也觉得没勇气。正巧贝宁在办公室就出了点事。那天,装修到贝宁这间办公室的时候,贝宁和大家一起去搬文件柜,没有配合好,文件柜一下子朝贝宁倾了过来,贝宁拧了一下身,并没有砸到,可贝宁半天都站不起身。送到医院,检查了很久,医生说,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如果再发展,可能会引起瘫痪,一定要卧床治疗。就这样,以前盼了很久的假期一下子就有了,而且好像无限期似的。
贝宁回家以来,除了必须下地出门去看医生的时间,全都躺在床上。一般能见到的人也就是钟点工赵姨。每日赵姨都来给贝宁烧饭。但有时,贝宁连赵姨都不想见,听见赵姨进门了就假装睡着,赵姨在卧室门外叫一声小贝,见没有应声就悄悄去做饭了。
这些天来,贝宁的头不再痛了,但越来越多地陷入一种浅睡状态。一会儿昏沉沉地睡一下,好像又醒着一样,胡乱地看见有好多影子飘来飘去,清醒的时候又明白那是在做梦,梦见什么并不清楚。
还不算晚的时候,贝宁听到有人敲门,贝宁没有吭声。反正也不会有人来看她,她可以肯定这一点。同事们都会在上班的时候代表单位来。接着敲门声停了,居然就听见有人在开门。
会是谁?贝宁在迷迷糊糊地想。会是小偷,还是赵姨?又听见有人进来了。贝宁假装睡着。那人并不在客厅停留,直接进了房间。
贝宁并不十分害怕,只是想到,小偷来了应该装睡才对。但听见那人直接往床这边过来了。贝宁故意嘟哝着说,怎么才回来,我不舒服,先睡一会儿,饭在桌上呢。贝宁想,这样小偷应该以为我的老公会马上回家吧。可那人并没有停下来,直接走到床头,抓住贝宁的双肩,使劲摇晃起来。贝宁实在无法,只好睁开眼。
看到这人长得很干净英俊,非常吃惊,不由得说,你长得这样好,为什么来做这个。那人也奇怪,跟贝宁答话,说,不做这个做什么?贝宁说,咦,你是达川人?我跟你是老乡啊。贝宁并不是达川人,只是急中生智。她觉得靠说服教育有可能摆脱眼前的困境吧。
那人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穿着白色的T恤,问贝宁,你的钱在哪里?贝宁说,在衣柜里,那人翻了一会儿说,这么点儿?贝宁说,我本来就没钱,你真的是小偷吗?这么帅,不如做男朋友。那人凑过来,低下头说,是吗?贝宁闻到淡淡的刮胡水味,很安宁的气味。贝宁说,我们去吃饭吧,我饿了。
那人看看贝宁说,好吧。便挽了贝宁出去。他的另一只手里有刀,贝宁很清楚。
在一家小饭馆里,人很少,他们坐在窗前,贝宁说说笑笑的,跟平时完全不同,贝宁内心也很惊讶,觉得自己原来可以这样。对方并没说几句话,到后来,贝宁听到了原来从达川来了一群人,结伙在这座城市里行动,贝宁有点着急了,跟对方说,你回去向你的同伴说说,别再到我家里来了,贝宁想了想,又说也跟他们说,别再到我们这幢楼来了。对方说,好啊。贝宁说,说定了哦,伸出小指就去跟对方拉钩。对方有点勉强地笑笑。贝宁回来的时候,在楼梯上碰到房东,房东就住在贝宁的楼上,房东说,哦,刚才男朋友来了啊。贝宁很想解释,但又不知该如何解释。
贝宁回到床上,天并没有变得更黑,反而一下子亮起来,贝宁忽然清醒了一下。因为她听到一阵阵叮叮当当的声音,她睁眼望向窗外,居然天空很晴朗的样子,完全不像前些日子的阴郁。
贝宁心中一阵明白,刚才那些大概都是梦中的事情吧。
贝宁望着天空,湛蓝湛蓝的,十分漂亮,心里沉静,什么也没有想。她忽然看见一张小伙子的脸出现在窗台上。贝宁望着,也没有什么表示。
那小伙子隔着玻璃和防护栏向贝宁打着招呼,你好。贝宁对他轻轻一笑,没有说话。对方指了指窗台上的两盆花。贝宁有点不解地继续望着对方。对方一番比划,贝宁明白好像是说要把花盆拿下来。贝宁摆摆手,又指指床,意思是说,我动不了。
那小伙子又把手朝旁边指了指,像在征求贝宁的意见。贝宁也还是没明白到底他想怎样,胡乱地点了点头。
一会儿,贝宁听到客厅里有些声音,接着就有人来敲卧室的门。贝宁说,进来吧。她说的时候心里都是一阵迷糊,不知怎么回事。就看见刚才在窗口的那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走了进来。他说,我从你阳台上进来的,你们这儿的防护栏都要拆,拆了防护栏还要给外墙面刷涂料。你窗子上的两个花盆太大,不搬开怕打坏了。
贝宁说,你搬吧。那小伙子打开了窗子,伸手搬动花盆。贝宁看见他穿得十分单薄,褪色的蓝牛仔服,但他反而很热的样子,脸色很红,贝宁忍不住掖了一下被子,自己盖得很厚了,却仍然有点冷意。
花盆搬了进来,先是放在了靠窗的书桌上,一盆是桂花,一盆是剑麻。贝宁都想不起什么时候给它们浇过水了。桂花树很弱小灰暗,在一个大盆里非常的不相称,剑麻倒是长得十分旺盛,姿态非常嚣张,像要把花盆胀破的样子。
贝宁看着那两盆花摆在那里,十分厌恶,就摆了摆手。
那小伙子仿佛明白了贝宁的意思,把花盆放到了地下,可自己也觉得不好,就说,我帮你放到阳台上吧。然后就端起花向客厅走去。贝宁一下子就对他有了点好感,可小伙子去客厅逗留了很长的时间才过来搬另一个花盆。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冲着贝宁笑了笑。贝宁有些诧异,听到他嘟囔了两句都不明白。贝宁笑了,说,什么事?小伙子说,我看见你阳台上有两本《路遥全集》,我想借一本来看,很快就还给你。贝宁愣了一下,才想起阳台上那堆书也是以前的住客留下的,贝宁就说,你两本都拿去看吧。小伙子说,不用了,我看过下集的《平凡的世界》,我很喜欢,上集那些短篇我没有看过。
小伙子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很快搬好另一盆花,说,谢谢,打扰了。就从阳台翻了出去,一会儿又回到贝宁的窗前,和另一名工人开始拆外面的防护栏。
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贝宁又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常常在睁开眼的时候,一阵迷惑,不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她看见床头的小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她拿起来,翻了翻,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这不是那个年轻的民工要借的书吗?贝宁翻到目录看起来,有些还有点印象,可能是中学的时候看过的吧,她已经很久没有读过小说了,大约在高一、高二的时候才喜欢读小说。书里面夹着一页纸,贝宁把它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我所热爱的事物曾如此触手可及
直到世界只留下一张床
直到所有的爱面露愁容
除了时间我们一无所有
城市的骨架在窗外疯长
能看明白的只有这些,其它还有些潦草到认不清的字。都是铅笔写的。纸张很新,边缘用手裁过。中间还有些折痕。
贝宁小心地把这张纸按折痕一点点地复原,最后居然折出了一个纸飞机。贝宁发现那几句话都是写在飞机的机翼上的,斜斜的,是折好后写上去的样子。
这张纸这么新,那一定不是原来书中夹的吧,一定是那个红脸的年轻民工夹进去的了。
贝宁想,是他写给我的吗?为什么?而且这几句话写得还真不错,我的世界不就只有一张床了吗?
贝宁准备再看见那个红脸的民工就要问个明白。如果换了其他人写一点纸条之类给贝宁,贝宁是怎么都不肯去追问的,但面对这样一个小孩子,贝宁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赵姨做好午饭,贝宁吃了一些,又躺在床上,盯着窗外。
果然就看到那张红红的脸出现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快餐盒,说,你好!我早上来还书的时候,看见你还在睡,就放在你桌子上了。
要是在往常,贝宁听到有人在她睡着的时候看过她,她心里一定会很恼怒,不过,现在她好像一点感觉也没有。她笑笑说,好看吗?他在她的窗外蹲着,说,好看,不过,没有他的《平凡的世界》好,那个感觉很真,就是结尾太快了点,结尾不大好。贝宁听他这么讲,很惊讶,说,你多大了?
他说,我十九了,去年高中毕业才出来的。贝宁说,怎么不读大学?他说,没考上嘛。贝宁想起要问他的事情,说,这是你写的吗?一下子他的脸就更红了,半天才说,我是说这张纸到哪儿去了,不是我写的,是我捡的,那边那栋楼也有个不能动的人,他在窗子那儿飞纸飞机,就飞在我旁边,我看到上面写的诗,觉得有意思,就收起来了。
贝宁说,我也觉得写得很好,还以为是你写的呢,还给你吧。
他说,你喜欢就留着吧。然后他一起身走开了。
看来这栋楼的防护栏已经拆完,因为外面的声音已经不是很嘈杂,偶尔听到一两声吆喝,应该是正在刷外墙吧。
太阳斜射进来,应该是黄昏了吧,贝宁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手里还拿着那个纸飞机。
窗口又响了一下,只见窗口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奇怪的东西。贝宁沉住气,一声不吭。只见接着一个人就出现在窗口,那个白色的东西原来是一只打了石膏缠了纱布的脚,那人双手抓住旁边的脚手架,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弯下来,往里面看。他忽然就看见屋里床上那个苍白的女孩一双大睁的眼睛,也吃了—惊,然后就笑了起来,说,你醒了?
贝宁一点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本能地回答说,是啊。
那人说,那个纸飞机是我的。
贝宁还是不明白,说,那还给你吧。
那人连忙解释说,我不是来要它的。我叫杜建,我听那个小民工说你也在生病,又很喜欢这首诗,就过来看一下你。你叫什么?
贝宁说,我叫贝宁。
那个叫杜建的人有点不自在起来,说,我可以进来吗?
贝宁才想起应该邀请对方,连忙说,请进请进。
杜建一个很灵巧的动作就从窗外进到了屋里,看见屋里没有什么椅子之类,便就势倚在窗前的桌子上跟贝宁说话。
杜建跟贝宁讲,他是C大登山队的,前段时间去一个地方攀岩摔坏了腿,这段时间打着石膏闷在家里实在难受。家里人不让他出门,但他们一定没想到还有窗户可以爬,而且在脚手架上,比拄着拐杖走路要灵活多了。说着说着,杜建就嘿嘿地笑起来,黑黑的脸孔上出现一排白牙。
杜建讲了半天,忽然意识到一直都是自己在讲话,顿了下来,说,你呢,你是怎么了?
贝宁不擅长讲述自己,只能简单地说,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就对杜建说,你平时都写诗吗?
杜建愣了一下,说,哦,不,那首诗不是我写的,是我住院的时候,我同病房的一个叫文迪的诗人写的,我很喜欢,就记了下来,本来很长的,但只记住这几句了。你平时也读诗吗?
贝宁说,不,很少读诗,一般都读不懂,但这几句我觉得像在说我一样,就有点喜欢。这个诗人是什么样的呢?
杜建说,挺帅的,年龄跟我差不多吧,说话很有趣,也是摔了腿,躺在病床上不停地接待朋友,很多女孩来看他,偶尔空下来就和我聊天下棋,出院的时候我们还互留了电话的,约着以后腿好了一起打球。
贝宁说,以后还可以打球?杜建说,当然,这点伤算什么?你躺在这儿不好过吧,下次我把文迪约着来看你,对了,你喜欢养花吗?
贝宁说,哦,我种不好。杜建说,我看见你阳台上那两盆花了,是不大好,我下次来的时候给你带个小的带种子的花盆吧,你只要每天浇浇水,放在床头,一个月就可以开花了,开花的时候,你的病也差不多好了吧。我得走了,不然家里人回来会发现我从窗子溜出去了。杜建说着就从窗口翻了出去,两只手吊在脚手架上,像个猴子一样荡着走了。
贝宁在一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忽然发现床头的桌上真有一个小花盆。贝宁下了床,走到窗前,发现外面的脚手架中间踏脚的地方居然是空的,那些地方原本应该铺着木板才对啊。她看着就觉得一阵眩晕。
贝宁去厨房接了水来,很小心地把花盆浇透。
此后贝宁每次醒来就仔细观察花盆,小心浇水。几天后,果然就发出了两个小小的芽来.看着嫩芽一点点地长大,贝宁猜测着这到底是哪种花。贝宁很缺乏植物知识,所以她是一点头绪也没有。也许那个年轻的民工知道吧,但好几天都没看见他从窗前经过了。
贝宁有点盼着杜建来了,她想让杜建看看这些嫩芽。嫩芽一点点地长大了,是什么花,她仍然看不出头绪。但这棵小小的植物,每天都有很大的变化,一点点抽出了一些肉肉的细叶,贝宁发现自己的心情都急切起来,想早一点看到开花的情景。慢慢地贝宁发现这棵植物已经结出了一个小小的花蕾,贝宁一下子觉得这是个极熟悉的画面。
贝宁使劲地回想起来,啊,是的,小时的窗台上就种了这种花,太阳花,花开了会有红的黄的,十分漂亮。这种花需要日照,她把花盆放到了窗台上。为什么这么多天杜建都没来,她想,如果能看见那个年轻的民工也好,可以让他带个话去。
可站在窗前,贝宁什么也没有看见,连脚手架也没有了,外墙光光的,远处的墙涂上了一种淡黄的涂料,在涂过来的过程中忽然就没有了,更衬出水泥的旧墙格外肮脏。
中午吃饭的时候,赵姨挺高兴地说,小贝,你最近的饭量好很多啦,身体应该快好了。贝宁就问赵姨,为什么外墙的涂料还没涂完就不涂了。赵姨说,我也不知道,只是前两天在菜市场听说外面搭的脚手架上摔下了一个人,所以就提前把脚手架拆了。
贝宁拿起电子钟,仔细看了一下日期,原来离开始生病已经差不多两个月了。贝宁看到窗台上那个小花盆,觉得有些什么不同,原来花蕾已经绽开了一点,是红色的,那一点已经是艳艳的,旁边包裹着没有褪去的青色。
外面的阳光耀眼地亮,很暖和的样子。贝宁穿好衣服,准备出去走走。
这时听见外面有人在很大声地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