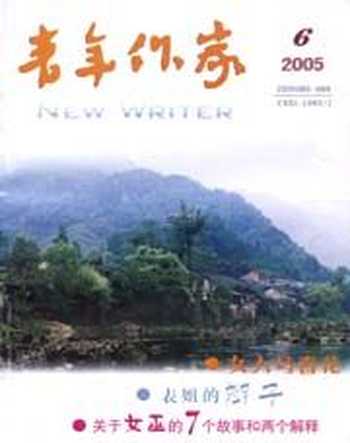仿恋
简 卮
零零星星的雨和暮色一起降落下来。
灯光照在海报上,像那女人的眼泪。另一幅海报上有个趴在断头机承颈孔上的人,瞪着一双没有瞳孔的眼。继红要他们在这里等房东。
“房东拿着份《蝶城晓报》。”她是李妮的朋友,在租房中介待过。照继红的说法,房子离李妮的单位更远,不过坐地铁,上班却比原来方便。
翦小乙陪李妮来接头,好像这种事还会有什么危险似的。环球影院对面新竖了个雕塑,一个打破伞的裸女。翦小乙不敢说她像李妮,可她就是像。只是李妮的胸脯没那么饱满,也不会那么明光锃亮。青铜女人像戴着一副金乳罩,那是游人摩挲的。
翦小乙又是他们初次见面那副样子。李妮甚至想抽烟,是那种陌生感逗的。她都有点怀疑,这些天的来来往往是不是梦,它们很像是想象,但不是因为离奇。相反,是它们没能给她清晰的印象,它们躲躲闪闪。
所有的梦都给李妮这样的感觉。也是经理给她的感觉。她感觉经理就是这么个人。
她和翦小乙并不想这样。他们之间的事都类似他陪她在电影院等房东。
李妮给他打电话,他没说这没必要,来了。显而易见,他的兴趣不大。几乎每次碰面,他都会使李妮想起初次见面。那次李妮有点歉疚,翦小乙则始终都像在犹豫。他还给人不知所措的感觉,那不是因为李妮,她宁愿是,就有歉疚感了。
“来蝶城就住在这里?”
这不是他有兴趣的话题,但总得说点什么。
雨和暮色使街景变得混沌,又混沌又稠密,而且虚幻。往事的虚幻感和眼前的景象有关。它虽然紧贴我们的肌肤,却像一瞥那样难以觉察。
“住过鸳溪路。”
“怎么样?”
“窗外是一条黑乎乎的河沟,隔壁又有个联谊会。天地联谊会。”
“在哪里了?”
“依你应该在哪儿?”
“猪湖路天地大厦。”翦小乙说,“我以前是会员。”
“我住进去没几天他们就在那里了。”李妮说,“没通知你?”
翦小乙正要说话,房东出现了。他拿着报纸,可要是继红说他穿着夹克,他们会早点看见他。
“你们?”
“她。”翦小乙说。
房东看着他点点头,带他们去那空荡荡的房子。房内有一股糨糊味。
“是因没住人。只要不住人,一准这样,就是皇帝的行宫也一样。”
李妮付了钱,房东又说了几句口气诚恳的话。
李妮左右看看,踩了踩地板。地板像是朽烂的。
“塌不了。”房东说。装好钱,走了。
不知哪儿的门哐一声,整个房间都颤,像要塌。
李妮说:“我得换把锁。”
他们去车站的时候,李妮电话响了。
“继红在凤翔路那边等咱们。”她说,“我还以为是老板呢。”
“我得抽支烟。”继红说。她的确需要这支烟,点燃烟,她立刻优雅起来。
李妮和翦小乙都没抽,他们喝了点。这家酒吧的灯光是酒红色,那酒看上去就是黑的。它还装饰着靴刺、左轮手枪和牛仔帽,帽带是仿响尾蛇皮的。
继红颧骨有点高,但不红,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中,还是吸引人的。她很伤感,但他们都没受到感染。李妮甚至没像翦小乙那样装作受了点感染。
“他们不过是继红的伴当。”来的路上李妮告诉他,说这是继红亲口说的。不过此时李妮要是提这个,继红只能生气,虽然她不便生气。她对翦小乙有好感。
“我在海冰研究所上班,混。”
“混?”继红捏灭烟蒂。
“你没听说过这个?”翦小乙很惊讶。
“经常听。”继红说,“可我还是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就不能正常生活吗?”
“这就是正常的生活,是最正常的。”
“我更糊涂了。”她不高兴地看李妮: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这种人,”李妮说,“偏执。”
“我以为只有认真的人才说得上偏执。”继红说,“我是这种人,我知道。”
李妮的腿在使劲蹭他。
继红又说那男娃,这次说的是她为什么欣赏他,有那么点让翦小乙惭愧弗如的意思。
“他说话的姿态简直像接受电视采访。”继红说,“说几句就稍作停顿。”
像咽唾沫?翦小乙想说。
“受不了她。”李妮用的是翦小乙常在影院听到的得意腔调。他们走在仿佛布景搭成的瑞金路上。“以前她没这么过分。”
“这不算过分。”
“我是和她以前比。”李妮说,“像是表演。”
“我们都在表演,还都是主角。谁也不能当配角,这不是在舞台上。”
“有人想当配角吗?”
“我有时非常想。”翦小乙说,“但是这不可能。”
“为什么?”李妮喃喃地说,“既然依你说没有配角,这么想就不对了。”
“这样想的意思是:必须这样想。”
“这不过是想象,我是说有的想法。”
“可生活就是这样,它甚至是假象。”
“好吧。”李妮说,“那你又何必认真呢?”
“荒唐的是,你要说生活是假象,你就是认真的。”
虚假的景象消失了,他们来到街口。
继红问李妮:“你怎么认识他的?”
“第六医院。”
六院是看精神病的。继红以为她在开玩笑,而不是说谎:“他衣服上绣着姓名?我怎么没看见?”
“你没看他的眼睛吗?他眼里有那种东西。”
“我没那样的眼,”继红说,“只有你看得出来。”
李妮至今也不知道继红说得对不对,她用的是戏谑的腔调。
不会是盗用继红的网名翡翠烟嘴吧?李妮有点歉疚。没着落最难受,她宁愿是。
翦小乙把自己看成装在电杆上那种鸟一样的瓷瓶,他的名字是绝缘子。
这个能活动的绝缘子走过来,也没拿报纸,李妮还是认出他来——这很怪,他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样——他的样子像狮子,也像鹿,有鹿那样的驯顺。在继红那里,李妮看过一本写动物的书,说:猫科动物进化出这模样来,意在迷惑猎物。
李妮不是鹿,不是斑马和野驴,他这张脸对她不起作用。
是你吗?
“我是男扮女装。”李妮说,他以为她是个男的。
李妮梦想着乔装打扮,可是她连一副怪模怪样的眼镜都没戴过。在网络上,她装成继红。这人很像继红以前的朋友阿蜜,他觉得,可如果是阿蜜,他就会知道翡翠烟嘴是谁。
李妮想抽烟,这说明她不自在。她要是抽,翦小乙无疑会更不自在。在李妮那里,烟是和不自在、继红联系着的。以前,她的烟都是继红给,准确地说是继红的姐夫给。追她姐的时候,姐夫整条整条地送烟,像个搞腐败的,还送了她一个水晶烟灰缸,看去像观音的莲座。继红正好有个孚佑观请来的慈航真人。她请菩萨也像地摊上买花瓶,和人家砍价。
那菩萨正好能坐进这只烟灰缸里。
“烟就是他的玫瑰。”继红说,手腕放在桌上,烟几乎像一炷香那样竖着。
要是香烟也鲜花一样五颜六色,彩纸卷制,李妮可能抽得更多。她怀疑政府对香烟还有颜色的限制,免得烟商引诱儿童。
涂着鲜红唇膏,一支淡蓝纸烟,过滤嘴深蓝色。她以为自己做过这个梦。
就是一支普通的烟,要是她拿出来噙着,也可能吓着这只忧郁的百兽王。
她的感觉在浮动,他时而歉疚,时而悒郁。她始终没平衡好。
第二天,李妮走在凤翔路上。市政工人在换路牌,路牌广告仰在人行道上。原来那个卖保胎药的被换下来,换上的这个是宣传恋爱日,蝶城的恋爱日正是昨天。路也不叫展览路了,改叫狂欢路。蝶城的狂欢日是哪天,李妮还不知道。市长公布了三个特色日,据说不久以后,蝶城还要改成恋爱城。
她想到阿蜜,看来是有道理的。和继红分手后阿蜜和李妮谈过一次。他还是继红的伴当时,李妮就对他有好感。可他已经做过继红的伴当,即使分手了,她和他也不可能了。李妮当然深感遗憾,深感惆怅。
她想看看这个像阿蜜的人是谁。她没想给自己挑选形象,那完全是受了翦小乙的影响,虽然是无意识的。
如果出场的姿态是腼腆的,那就得始终如此——演员不能说和角色抵触的话。李妮想起她在服装店试穿旗袍的情形,再穿几分钟,她的两只手就会握在胸前,一扭一扭地走出来。
她放弃了优雅地掏出纸烟的机会。有翦小乙的场合,就只能节制了。仅仅因为这个,便足以使她想到放弃这个关系。这想法比掏一支烟出来、戴上一副蛇眼镜更不可思议。
李妮就是从这个勉强的笑开始的,对翦小乙来说。
没准会有点新鲜的。她是这么想的:也是个调剂。虽然生活就是一系列常识,常识又告诉她不可能有她想象的东西,她还是想试试——只有常识还不是常识的时候,比如念自然常识那会,李妮才喜欢常识。
她挑了个离网吧很近的地方。这使她有找好了退路般的轻松。街上熙来攘往,警察成双成对,有如猪湖上的恋人。不会有故事里的浪漫,至少也不会有社会新闻里的危险。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李妮也不知道。如果她不来,和继红去泡吧,又有什么意思呢?
翦小乙说:“我忘了带证件。”
“警察?”
他的嘴做出笑的样子,眨着眼。
李妮摆摆头问:“我像警察?”
她就像是在摆那齐耳短发。她也没戴耳环,没化妆。
他笑笑。
“我是间谍。比警察还厉害。”李妮说,“我上网和我的职业有关。”
“贝利亚说,真正的勇士是无法收买的,只能用美女引诱他。”
李妮模仿电影里阴险的笑声。
“我在海冰研究所上班。”
李妮说:“我还没见过海呢。”
“没什么遗憾的,”翦小乙说,“我常听人这么说,那可能是最没看头的了。”
“我从没听说过。”李妮说,“我倒是听说过稠密的糊状冰。”
“没人爱听这个。”
“海市蜃楼呢?”李妮说,“我有个朋友看见过海市蜃楼。不过他说的是沙漠里的海市蜃楼。”
李妮没有这么个朋友,可她要是不这么说,海市蜃楼就只能是传说。她等着他说话,能感觉到随时会消失的微弱吸引。
“准备干点什么?”翦小乙说,他的意思是说作为补偿。
“这就是我的日程安排。”李妮说。
她已经完全相信这就是她的想法。她知道男人怎么看逛街。
“我的朋友常这么说,你在街上就像个游魂。你没看出来?”
“我看你像英雄路给人做形象设计的。”
“我是做物流的。”李妮略微停顿,似乎在想象中体验她那日常工作,好给他个准确的描述,“事很稠,老板会把电话打进我的梦里,来确认一张订单。”
“要是梦都做不成,”翦小乙忧愁地说,“会精神失常的。”
李妮笑笑,不以为然。
“我没夸大其辞。”
“做梦影响睡眠。”李妮说,“我以为是这样。”
“看来有两种说法。”翦小乙说。
“梦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吧?”李妮说,“至少想不做梦是不行的。”
“所以要做补救,消除缺梦的影响。”
“怎么补?”
“看电影。”
“我觉得烟火也像梦。”
李妮以为他不会来,上次他说,他不知道烟火有什么好看的。李妮故意把那些话想象成他随便说的,尽管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在随便说——什么话都不会从他嘴里随便说出来。他不会随便说话,看来是这样。
这就不像阿蜜了。觉得他像阿蜜的时候,李妮想到的是那天晚上的阿蜜,只有那天晚上的阿蜜是那样。
给翦小乙打电话前,她已经准备好和继红去。她首先会想到继红,这是习惯。继红会怎么反应,她很清楚,她会先说不舒服,或是很忧伤。她就喜欢这一套,直到李妮说算了,她才会装作上帝迁就她。其实她一接到电话,就开始收拾了。
就算翦小乙上次是随便说的,李妮也没真想和他去。可是,如果不希望有什么效果,干嘛打这个电话?
翦小乙的愉快,好像是在掩盖他的尴尬,免得她难堪。
车站贴着布告,凡是去英雄广场的车都不能去那里了。
“还去吗?”他的话就含着回答。
“去地铁吧。”李妮不想就这么回去,虽然她的兴致也不高。
燃放点附近的四个站都封锁了。
“蝶城老站离燃放点近点。”她是凭感觉说的。
“走吧。”
挨挨挤挤,列车一直开到蝶城老站。出来再往回返。李妮没走过这条路,用不着她辨认,跟着看热闹的人走就是了。
“在蝶城新站。”翦小乙说,“有一次我也这么随着人流走,最后走进一条死胡同。”
不单是交通管制,街口还站着一排人,有男有女,穿着深色便衣,戴着医生和病人那种口罩,似有阻拦之意,却又并不阻挡,只是那么站着,给人以荒诞感。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一看这伙人的架势,翦小乙就不想过去了。
英雄广场还远,要看见焰火,除非它有星星那么高。
“已经到这里啦。”李妮说。
如果你一定要过去,这些大口罩不但不阻拦,还示意你沿墙根走。
这样的限制线有好几条。
到银蝶路的时候,李妮已经兴味索然。
这里不再是限制线了。挡路的都穿着制服,武装警察服,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过去。几个想闯过去的人都被带走了。翦小乙和李妮不想被带走。
有人说,这里也行,那些腾得高的烟火,这里能看着。翦小乙和李妮想的可不是在这里看。他们掉头回去,走过一道道限制线,谁也不说话。在最后一道限制线那里,能从老站前面的大屏幕上,看见烟火晚会已经开始了。
翦小乙越走越快。
“这就像我在缠你,”李妮说,“不能慢点吗?”
“鞋跟断了?”
“腿。”李妮气吁吁地说。
翦小乙送李妮回瘦佛路。这种晚上,在瘦佛路这样的僻处,可能有浑水摸鱼的人。
一溜门墙上都写着河马脑袋大的“拆”字,淋淋漓漓,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革命和凶杀。不是拆,李妮会在这里住下去。这里的房子老,李妮以前听人说,因为它已经足够老,有政策,不能拆。
翦小乙没进去,对李妮说:“收拾东西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这也是可有可无的。
有那么个瞬间,他们都有虚幻的感觉,而且几乎产生错误的判断。很暧昧,他们都有紧张感,也可能是激动。
床上用品都在编织袋里。编织袋是李妮从公司拿的,各种各样:中药饮片啦、饲料啦、食用碳酸钙啦。
十点半,搬家的人还没来。打电话问,说车堵在体育路,可能那里出车祸了。
翦小乙来主要是陪着李妮枯等,这是他们都没想到的。他想去买张报。可是报摊在拐角处。还好,他从李妮不要的桌子抽屉里找出几张名片来。她的东西都是原先的房客卖给她的。他还给了她几张名片,说:都是收旧货的。
“只有张进宝收旧家具和清仓货。”
“那人说都是。”
“郑有成,东南亚档案公司制作部主任,制作未婚证结婚证。”
“未婚证?”
“蓝霞,新蝶标牌店维修部副主任。西门莲,蝶城大酒店泰式特服部经理。要吗?”
“要东南亚那张。”李妮说,她想换个工作。合适的工作比房子更难找。
“他昨晚又打电话来了。”李妮揉揉眼。
李妮提醒他:“我请了假呀。”
他是那么客气,好像当时就后悔了。他还在陪客,听背景音乐就知道,有人在鬼哭狼嚎地唱。老板不像李妮,喜欢卡拉OK,他待在极乐时光是不得已,要应酬官僚和生意伙伴。说起这事老板就唉声叹气,他们夫妻关系都因此有裂痕了。
“他干嘛对你说这个?”
“他说我能理解他。”
“你能吗?”
“有时候我能体谅他。可是,他半夜打电话。要是我在网吧也就算了,我在睡觉,在做梦——你说过做梦很重要——我没把做梦的时间卖给他,虽然梦的往往就是他打电话。”李妮说,“除非我换个单位,不然就只能迁就他。他是那么客气,甚至可以说小心翼翼。”
“你上班去对他说:前晚梦见你来电话,订单的事。”帽舌的阴影落在他脸上,有点像戴着佐罗的面罩。
李妮铺好床,他们都乏了。她仰在床上,他趴在床上。屋内光线黯淡。时间缓慢地流淌着。
翦小乙鼻翼翕动着,像脉搏跳腾。光线黯淡的地方,就给他缓慢的感觉,能缓和他的内心。可是他仍很紧张,心收得紧紧的。没有痉挛,肉体松弛着,绷不起来。
李妮只能装作没有觉察他的窘状。他们像拳击手那样紧紧搂抱,沉浸在彻骨的孤独里。
电话蓦然响起来。他们如释重负。是继红。翦小乙从李妮口气中听出来。真感激她。
“你就好的那个调!”李妮捋着头发,气咻咻地说。她是在对谁嚷?不是继红,说是他,也不准确。
他一动不动地待着,像个被当场戳穿的人。
“烟呢?”李妮收起电话。
他看着她。
“烟?”
李妮一声不响地吸着烟,拿了张纸搁在床沿,弹烟灰。
翦小乙疲倦地坐在床上,打了狮子般的哈欠。
李妮的梳妆台就摆在那里,镜子清冷地照着他。
眼光只能使他感到不适,即使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