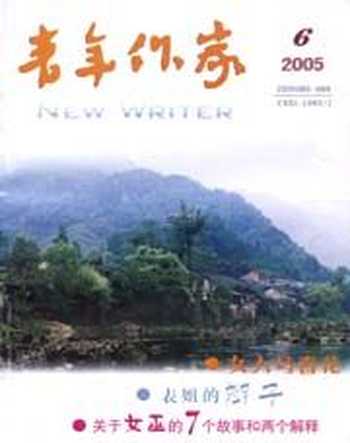一碗杂碎
马步升
具体的人
吾乡直到世风日下的现在,仍然堪称民风淳厚古朴,别的不说,单是日常的一些用语及其传达的意思,听起来常常既令人摸不着边际,又感到温暖,比如:具体的人。
什么是具体的人呢,我也算是吃语言饭的人,可多年来,却始终没有搞明白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我只能把一些具体的人和事略作罗列,以求同好帮我解疑释义。
其一,周二长得人高马大,力大无穷,与别的大力气的人角力,可以把数百斤重的石碌碡抱起来,绕打麦场转几圈。可他居然是个懒虫,懒名与他的大力气名一样大。他家住在山尖上,田地在河川,两口子日出而作时,挑着两只空桶搁在水泉边,日没回家时,舀满一担水挑回去。那桶是特大号的铁皮桶,一担水刚60公斤。他家离水泉有将近两公里的路程,都是六七十度的陡坡。两口子在田地里共同忙活了一天,回家时,媳妇挑着一担沉重的泉水,吭吭哧哧爬山,周二跟在后面,双手拢在背后,嘴里叼着一根粗大的旱烟棒,间或还撂出一段酸曲。他常唱的是这样几句:
绣花枕头抱上楼,
看郎睡在哪一头?
这头那头我不睡,
要在妹的怀儿打瞌睡;
在妹的怀儿睡一觉,
身子快乐人轻俏。
周二心安理得,媳妇无怨无悔,村里人也习以为常,有几位老年人看不下去,恨得牙痒痒,恨完,叹口气,说:这个具体的人!也有对周二媳妇恨铁不成钢的,便咬牙切齿道:两口子一个比一个具体!
其二,候爷半辈子只好一件事:嫖风。吾乡把男人乱搞女人的行为叫嫖风。风者,风雅颂之风也,这里面有风流的意思。侯爷从小毛手毛脚,上窜下跳,跟猴子相似。老了手脚不利索了,可手脚还不安生下来。60岁那年午后,他在山上砍柴,年过半百的赵大婆在山头放牛,他心里起了意,蹭过去厮磨一番,赵大婆不肯,他便自己动手,只顾眼下快活。这事让人看见了,一声吆喝,村民们都赶来了,赵老大也赶来了。他抡圆扁担抽了侯爷两下,边抽边骂:你这头驴,咋这具体!村长也在场,他劝赵老大说:算了,他干了坏事,你打了他,两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半辈子了,一直这么具体。
这事就这样了了。
其三,白老大是个贼,活了70岁,偷了60多年。他不偷什么值钱的东西,也就是偷东家一个西瓜,摸西家几颗梨而已。走在路上,看见什么好吃好玩的,不摸一把,不尝几口,给自己没法交代似的。幼小时,小偷小摸解嘴馋,人多不在意,小孩子淘气!长大成人还管不住自己的手脚,那就是贼了。可他不偷什么值钱东西,人便不好把他当贼看,被偷的人说给人听,人会说,就那么个具体的人,被偷的人生气罢,也会说,这人真具体。其实,根本不用偷,乡里乡亲的,无论谁到了谁家门前,小吃小喝,从来都是大家共享的。可白老大还是偷,他说:偷吃的,香!白老大年过花甲了,腰来腿不来的,还偷,一次翻墙偷苹果时,跌伤了腰,从此卧床不起。村里人都去看望他,自家田地里产什么好吃的便送什么,一送好几年,一直到他死为止。大家都说:真是个具体的人,到老了,还这么具体。
被视为具体的人的人很多,被视为具体的人的具体的行为很多,比如,好说荤话屁话混帐话的,好搬弄是非的,不拘小节的,说话做事不分场合的,等等,等等,鄙人阅历有限,在此,仅列荦荦大者,不尽一一。看得出来,具体的人,其语义倾向于贬,是那种轻微的贬,多指那些言行越出常规的人,今天越轨了,今天便说是具体的人,明天回到常规了,明天就不是具体的人了。
从学理上说,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更无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可吾乡人不懂什么学理,更不是从学理上说的,从具体的人这个内涵与外延都极不确定的判断句衡人论事,更多的则是出于对生活的宽容,忍让,以及无奈。或许,还有一次次无奈后的麻木。
不正确的人
吾乡是周人先祖的发祥地,在一般的文书中或口头上,都说这里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浓厚。其实,谁都知道,这只是个说法,说顺口了,换成另外的说法,说着不顺口,听着不顺耳。周人,而且还是周人先祖,那是多么遥远而又遥远的年代啊,周人脚下的大河如今都干涸了,如云如雾如魂如影的传统还能在风霜刀剑严相逼的漫漫历史征程中走到如今?传统肯定是有的,只是此传统非彼传统罢了。一个简单的例证便是,而今存活在周人先祖开辟出来的土地上的人,已经没有几人读得懂先民留下的典籍了。当然,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了,即以现在的脱盲标准说事,文盲率仍是很高很高的啊。
然而,有传统和传统断档毕竟不同,传统深厚和传统浅近毕竟有别,就如大河干涸了,河床总是在的,高楼大厦崩毁了,地基是在的。吾乡人,哪怕是目不识丁的普通到底的人,内心储存的话语好似这里深厚广袤的黄土,无穷无尽。上小学时,我随父亲去县城,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内心那个激动,那个荣耀!十几名乡亲结伴穿行于二十里长的山道上,经过一个村头的打麦场时,突然看见一伙人头戴纸糊的尖尖帽,胸挂厚木板,被五花大绑着,佝偻在土台上,台下一帮人磨拳捋袖,群情振奋,呼喊声直冲云霄。那时,我已识得不少字了,见这些人的胸前写着各种“分子”的名号,但我不知道这些“分子”究竟何所指。问一位见多识广的乡邻,他淡然道:
“都是些不正确的人。”
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增广,我发现,在吾乡人的话语系统里,把行为越轨,甚至干了坏事,但不曾受到国家追究的人,都说成是“具体的人”,把被国家认定为坏人的人,则统称为不正确的人。前者为纯粹民间的是非判断,后者则是对公权已做出是非判断后的民间是非判断。他们很少机械地搬用已经成型或流行于天下的公权话语来衡人论事。在特殊年代里,把那些戴着各种帽子的“分子”们,他们统称其为“不正确的人”,在后来社会逐渐开明的日子里,他们仍然拒绝使用权威机构使用了的、并且流行开来的话语。比如邱和平把婆姨杀了,被枪决了,法院布告上明明说他是故意杀人犯,那婆姨贤惠善良,大家一致认为,邱和平让国家枪毙一百次也是该当的,但却拒绝说他是故意杀人犯,仍说他是个不正确的人;比如柳黑娃从小就是个坏种,偷鸡摸狗,打人骂人,长大后,变本加厉,骚扰得四邻不安,民愤极大,在被国家关起来前,逢他干了坏事,人们都撇嘴咬牙说:这个具体东西,咋不挨枪子呢!判刑入狱后,人们又都撇嘴咬牙说:那个不正确的东西!
事有例外。樊子昌是个远近闻名的逆子。两口子都不是什么好鸟。樊子昌幼年丧父,靠寡母含辛茹苦拉扯大,娶来的媳妇是个悍妇恶娘,过门没几天,便开始虐待婆婆了。初则克扣吃穿,继之拳脚相加,樊子昌初则不闻不问,继之助纣为虐。有一次,母亲不堪儿媳侮辱,回了几句嘴,樊子昌大怒,竟然冲上前去,将母亲一顿暴捶。乡人看不下去了,他们结伙上告村委,村支书不管,又联名上告乡政府,乡长一推六二五,他们气不过,我家老姑爷大手一挥,喊声:打这两个不正确的狗东西!樊子昌两口子遭到乡邻一顿暴捶,收敛多了。这次,吾乡人用他们纯粹民间的是非判断代替了公权的是非判断,樊子昌两口子已失去了做“具体的人”的资格,而沦为“不正确的人”了。
语言是权力。忘了是哪位大哲说的这句话,不论是谁说的,这话说得好啊。公权的强弱,在于它创制了多少话语,在于它所创制的话语占据了多大的公共空间;私权的有无,则在于私人是否拥有创制话语的自由,和究竟拥有多大的自由度。而对话语权的占有,则是每一群体和每一个体共同的,不由自主的内心冲动,可是公权过大,群体则会僵硬,失去活力,私权泛滥,又会导致群体的一盘散沙。
“具体的人”,“不正确的人”,从这两个极具地方色彩的命名中,我似乎理解了:吾乡人呈现给世人的常常是两种面目,一者是那样的安贫守道,言行拘谨,一者又是那样的放达自任,口无遮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