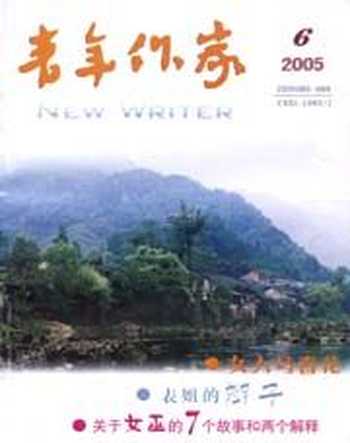无何有之恋
吕昕星
心情如此低落,心灰意冷。一个人活着,为自己活着,驱逐,消解,排遣着郁结心里的抑郁。于是容易被众人认为有意义又热闹的事吸引,是因为想做些和忘记些什么。
很有兴致地去听某某的讲座,在今晚。但要说的无关这个讲座,因为某某没有给我触动,他从头至尾讲到的东西所阐述出来的道理我都想过,并且有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这个讲座对我无意义。非说有的话,那就是我见到了当代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大作家,他是一个干瘦的满面皱纹的老头,有很能令人起敬的气质。
我一直站在过道上听,占的座位太靠前被划成嘉宾席了。我是以厌恶的目光去看“嘉宾席”上的人物的。看见了几个必不可少的大人物,最后看见了他,他坐在离我很近的座位上,看见他的时候我很快收回了目光。这个动作我没有细思为什么。他和我仅仅认识而已,知道对方的名字,偶尔在路上遇见打个招呼,很浅的交情,几乎算不上交情。我认识他的时候是怎样的过程我忘了,大约是在几次或大或小的会议上见他发过言,话不多,但人和话都让我很容易就忘不掉了。所以我认识他极其简单。而且我也不认为整个中文系会有谁不认识他。他如何认识我的,我只能猜测了。我想那应该是我初入学生会的时候,虽然分属于不同部门,但有几次在一起碰到过,应该也说过些什么话,要不以后遇到就没有理由打招呼了。
在今晚之前我没有意识到什么,至少什么也没有多想过。后来某位院领导终于致完了过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哗哗哗的掌声响起,某某缓缓上台,大家一片激动的笑容。我注意到他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我站到这里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一直就是那样子。这是我眼角的余光注意到的,然后忍不住就转过头看他一眼,他这时抬起头去看前台的某某,表情没有什么激动。也许像大家一样笑了,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固执地认为他当时一定是微微严肃的表情,甚至像习惯的那样轻皱着眉。
他有很吸引人的面容——请不要仅仅理解为帅、英俊或是与这些相似的形容词,虽然我不能否认这样的面容肯定和这些字眼有关——还有表情。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无意中看了他好几次,然后才忽然惊觉。是的,我发现他有好看的面容的时刻只在那么短短的一瞬,然后马上觉得脸烫,就继续认真去听讲座。当时我没有多想很多事。心里有点慌,刻意没有去想。仅仅是意识到一个问题而已。
现在,我从从容容想来,上面所说的意识到的问题其实应是很早就感觉到了,很早已感觉到他说话、走路、奔跑的样子,以及流露出来的一种我的文字所不能形容的东西,都是我所喜欢的类型。只是,他一直都是以感觉的状态不动声色存在于我的感觉,我什么时候把他在我视网膜前出现的画面,所有画面,统统摁下右键点了复制粘贴在记忆里我都不知道。现在我居然有些后怕,这些画面复制得逼真,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被删去了。
所以,在人头攒动呼吸混乱的报告厅里,我几乎才刚刚意识到,触目惊心地意识到:这么久了,我忘了把一种感觉告诉自己。
报告接近尾声。虽然我心不在焉,但因为平日是喜欢写小说的,所以对于这个会编故事的人的创作话题基本都捕捉到耳朵里。我有五个问题想问,于是高高举起了手臂。我一再举起手的时候,前面很多同学直接用话语截获了机会。我看看四周,发现问五个问题的想法不但不可能简直愚蠢,但我不能一下子放弃,我想问一个总行的吧,不论是哪一个。我仍然高高地举起手,一边打量前面的情况一边盘算五个问题选哪一个。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转过头来看到了我。我在这里犹豫是不是要把“看到了我”写成“看了我一眼”,因为在这之前他是看见我站在这里的。但我不能确定他这一次有多少可能是为了看我,这种可能应该很小很小,但应该不是几近于零吧。当时我高高举着右手,他在我右边看过来,不为什么,我就是很自然地在这个时候低了一下头,并且恰巧从举起的右臂下看到了他的脸,和眼神。我在这里用“自然”和“恰巧”来形容这场偶然,但实际上,你知道,有些事情发生时候的天衣无缝和恰到好处是没有办法描绘的。至少我还不能。以前我常把很多没办法形容的事归于造化的离奇和精巧,除了如此,我找不到更好的解释。
我看见他有微微笑容的脸和眼神出现在我白色外套的袖子下,我透过紫色的眼镜看见了。然后眨眼之间都消失。我想在不足一秒的时间里有两个人同时收回了目光。像逃避一样匆忙,或者是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自然。但我感觉到了尴尬,因为我更像故意看过去的,可是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我的眼镜是紫色的,镜框深紫,镜片淡紫。从侧面看过来的时候,镜片也会成为水晶一样的深紫。但愿深紫色保护,谁也不能从侧面看清楚我的眼神。
我再也不敢转身了,直到报告全部结束。我是再没有去看什么,和同学混在人堆里离开。
回来的路很长,从教学楼到寝室楼贯穿了大半个校园。路灯很暗,我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走完一截又一截幽幽的校园路。她在我旁边比着手势对我说着没完没了的话。我不时地点头哦哦回答。我前面说过,我记得许多他出现在我面前或者是视野里的画面。几乎全部。但我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些,我根本不知道我会记得关于他的那么多。直到走过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悠悠记得在这里碰见过他。其实一条方方寸寸都一样的路,承担校园最重要的交通,又已经过去了一年加半载时间,而我究竟在这条路上遇见过他多少次,早已经数不清了。之所以独独在这里想起了他,大概是……大概是……我说不清楚。我试图解释试图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因,可我还是说不清楚。
那天,是去年夏日的某一天,午后。因为时间逼近了期末考试,我在这个下午背上挎包提了一小袋面包去上自习,走过小超市又买了一支冰淇淋拿在手里。天气热得要死,阳光照在灰扑扑的路面上。我因为今天好不容易起早赶去教室有一点点勤学的自我安慰,所以心情比较好,很贪婪地吃冰淇淋。我居然记得那支冰淇淋是黄色的,而我穿米黄色前面印有很大的加菲猫的宽T恤,显得特别孩子气。路上几乎没人,远远看到他从对面走来,右肩挂着书包,左臂里是他的女朋友。那个午后我戴着眼镜,不论平常我是多么厌恶眼镜总之那个午后我是戴着的。所以我远远就可以看见他们一起走过来,在金黄色光芒的照射下。我的脸在看到他们的一刻缓缓绽开了笑容,他们一定不知道我的笑容是因为他们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到了“幸福地相亲相爱”之类的句子。我微笑着对他说“嗨”!
现在我可以承认,当他们走近之后,我的记忆里没有关于她的任何印象,只有他的脸清晰得不像样子。他本是微皱着眉头的脸——我说了这是他最经常的表情——在看到我之后缓和下来。我知道这种出于礼貌的表示不具任何意义,但我后来很多次想起——我现在才明白后来我有很多次把这个画面想起:我仍然觉得他脸上有一种明朗,让我从他们身旁走过以后,感觉到如同花开一样让人开心的光芒,并且念念不忘。
是的,他有女朋友,他们一直看起来是很好的样子。我甚至听说过他们的故事,同学讲述的关于他们最初的故事。我那个同学很会讲故事,讲述的情节以及形容的活泼逼真让我留下了看电影一般的感觉。但是请原谅我不能在这里对谁复述,因为别人的事情我不能随便讲。
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已经走过了餐厅,那个同行的女孩子去餐厅吃晚饭了。我独自走回寝室楼,然后又提了两个水壶走下楼来,去打水。晚上寝室楼到餐厅的一段路永远很热闹,我走在热闹的人群里有很不协调的忧愁。大体上我是知道自己在为什么事而忧愁的,但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解决掉,只好任自己一再忧愁下去。我极慢极慢地走在路上,两旁的路灯要比回来的那条路上多一些,有昏黄昏黄的灯光。黄色总让我觉得温暖,所以对我来说走这一段路如同在穿行一段幸福时光。如果你是中文系的女孩子,这样的灯光,这样的路,一定会让你想到王安忆的《雨,沙沙沙》。但也只有中文系的女孩子才会想到。
我当然不会想到今晚还可以再遇见他,然而在我走上这条路还没多远的时候,他从我身旁走过去了。他以有些匆忙的脚步从我身旁走过,手里也提了两把壶。我落在他身后看着他走过我眼前,越来越远。其间有个同学和他打招呼,他很快地和那个同学说了几句什么,但距离已远,我没办法看清楚他的脸了。
我就是在这段路上在他走过之后开始想起和想念许多许多有关他的事,而许多许多感觉就随着想念一点一点兜上心头。
秋天,他穿着浅灰色长袖T恤,肩上是黑色的书包,在排球场边观战。暂停场时走进去叮咛交代一番,仍是一副微微皱眉的冷峻表情,透露一些指挥若定的风度。我在人群里看比赛看到他,感觉如看着蓝色天空一样舒爽。他的浅灰色上衣奇异地给我留下铺天盖地的印象。假若我记错了,那不是T恤而是衬衣或者别的什么,但我肯定我不会记错它的颜色。
只有一次没有那么多别人在场的偶遇,似乎只有一次。那时我从楼梯上走下来,他往上跑。他看见我的时候停下来问我是不是要去听讲座。我说是。他说是关于哪方面的。我说是考研。他问是哪些老师来讲。我告诉他不知道老师只知道是哪些专业方向。然后仍旧是他往上走,我下楼来。
我是个不爱运动的女孩,除了体育课和运动会之外让我去操场应该需要用刀押送的。相反,他是个体育极好的男生,他在跑道上的奔跑会引来全院女生激动的喝彩。我站在跑道边看着他跑过的心情甚至有一点点崇拜。我只有一次关于这里的运动会的记忆,关于他的就是他跑到离终点的最后一个转弯处,有人拿来一面中文系的红色大旗披在他肩上。在一片轰轰烈烈的掌声和尖叫声中,他披着那面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旗帜轰轰烈烈地跑向了终点。
后来,我被一个女孩子抓住问生日的那天是几月几号,她说因为我生日那天也是他们部长的生日,可是她忘了那天是几号了。我告诉了她。然后知道了我和他同月同日的生日,不同年。
后来,再后来……
到了现在。我打水排队排在长长的队尾。他在我前面,只隔了一个人。我惊讶他走得那么快,而我仍然可以排在和他仅隔一个人的位置上,像是在这一段速度的落差里只有一个人恰巧赶在了中间,当我姗姗来迟之后还可以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我居然想我有时真是幸运。我就这样站在后面看着他,以一种告别某个季节的心情一直一直静静地凝望。直到我们站在了门口,直到他对那个刷卡的老头说出两个字:“两壶。”
我挑了一个离他很远的地方灌好水,离开了开水房。
午夜写完作业,我在白色的书桌上开始写这段过程,所有感觉随着书写越来越混乱,我忽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明天看到他,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
我还不知道,第二天,我没有遇到他。
《逍遥游》上说:将一棵无所用的大树种在无何有之乡,无论是徘徊树旁,还是仰卧树下,都不需要担心什么。如果每个人的无何有之乡就是自己的心,无所用的大树就是一份不需要担心什么的爱情,那么,我悲观地认为很多人的心仍是一片荒芜虚幻的布景。因为这世间难有不需要担心什么的爱情,和一个让你无须担心的人。
后记:很多天之后再看这篇文字,忍不住想要补充几句。上面所说的“不需要担心什么的爱情和一个让你无须担心的人”影射的不是文中的他,而是我在这里不想铺开阐述的一种针对爱情的恶意见解。我从未想过要走近他的原因也极其简单,无关勇气,信心甚至手段之类,我只是极反感第三人插足的典故。情人眼里容不下一粒砂,插一只脚趾可能会让两个人痛一辈子,何况掺一只脚进去。我不想用自己一时的薄弱的感觉去挑战别人的珍贵。情路多艰,愿意尊重别人的,也许就可以更好地珍惜守护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