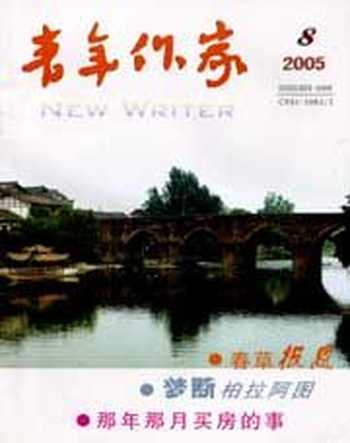温和的美丽
车茂娟
从《我在天堂等你》谈起
认识裘山山是从《我在天堂等你》开始的。没有想到我会被如此地打动,竟然流着泪一口气读完。我当时认为裘老师一定是进藏军人的后代,才能对那片神秘与苦难的土地体察得那么深切,对那些鲜为人知的经历、追求和感情,理解和把握得那么准确,表现得那么真切和细腻,好像她就是那样赶着牦牛一路走进西藏的。虽然裘山山老师谦虚地说,这部小说所获得的关注和荣誉已经超过她的预期以及付出了,关于这本书她已经说得太多了,已经“说腻了”,我还是固执地请她就从这部作品说开去。
有人评说《我在天堂等你》使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又一次成为文学创作中鲜明的亮色,作家自觉地在艺术创作中实现文学的价值。我也注意到裘老师在《我在天堂等你》中,几次写到女兵行进途中遇到的朝圣者。我不是很清楚,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来自一种天职的规定,还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欧战军和白雪梅她们,其行为是不是也是一种朝圣?
准确地说,是一种信仰。我到西藏,看到那些朝圣者独自行走,或者一走一匍匐时,心里就会涌起一种敬意和感动。他们也许衣衫褴褛,也许饥肠辘辘,但他们目标明确,步履沉稳;他们的目光越过人类的头顶直视天边;他们有与生俱来的信仰。有信仰的人精神世界很强大,面临什么困难都可以去克服,不易被打垮。不像一些现代人,心灵很脆弱,可能也包括我自己,遇到一点挫折或困难,比如失恋啊,工作上受委屈啊,考试不理想啊,生意挫败啊,等等,都很难承受,常常会有过激反应。而欧战军和白雪梅们,却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和困惑,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信仰很单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要统一祖国。当时全国就剩西藏和海南岛没有解放了。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正觊觎着西藏这块宝地,在他们看来,身为军人就有责任把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守住;具体来讲,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既然上级已经下达了这样的任务,就没什么二话好说,必须去执行,并且圆满完成。
那时候的人没有那么多私欲,很少去想自己将来怎么办,或者考虑这样做对自己是否有利。我不能评价个中的是非,我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虽然生活很艰苦,甚至要献出生命。但我总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现在的人幸福,他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们热情,坚定,明朗,因而也就没有我们现代人的彷徨和迷惘,痛苦和颓废。他们把自己的命运自然而然地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而且觉得很神圣,没有一点儿作假或作秀的成分。我特别理解他们,他们的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既是被天职规定的,又是一种自觉的行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西藏和西藏文化就越来越成为热点,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西藏的歌曲、歌手也格外吃香,甚至连西藏的佛经都制成了CD。而裘老师把西藏称为自己灵魂的故乡——“它如同故乡一样无法携带呵。但它的气息已随我而来,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嗅着它的气息而生活,抵御都市对我的中伤。待到它的气息渐渐弱小时,我会再次登上与它邂逅的旅途,一次又一次。”
春草也开花——小人物和悲悯情怀
裘老师不仅关注那些有历史深重感的题材,不只是写她熟悉的人和事;更可贵的是,她能跳出她的大院、她的世界、她的自我,把饱含同情的目光和负载着某种责任的笔触,自觉地深入到社会底层,把生活中默默无闻、艰难挣扎的“小人物",甚至所谓反面人物的酸甜苦辣呈现给人们,让人们在流泪的感动和揪心的疼痛中不能不去思考一些什么。比如《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中秋夜登三轮的老人》、《非常爱》、《周末音乐会》、《靳师傅的太阳光》等等,再比如她最近即将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春草开花》。
《春草开花》写一个生在很普通、很没有地位,甚至生活艰难的农村家庭里的女孩,从小没有读过书,没有得到过母爱,但她却有着非常倔强的性格,就是不服输,不断地与命运抗争。她的一生几起几落,几落几起,备受折磨,她依然不屈不挠地、一点点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什么也不能把她打垮。有点儿像日本的阿信,但不同的是,阿信最后成功了,而春草直到小说结束还在挣扎,还没有过上她期望的好日子,40岁的她依然辛苦劳作,要做七八家的钟点工,以便能让两个孩子在城里读书,他们还处在非常艰难的城市边缘人的境地。我想通过她的命运告诉人们:就是一棵草也想开花,就是一个小人物、最底层的小人物,也想过上好日子。而春草的魅力在于,无论怎样她永不放弃,拖不垮,打不烂,她不懂什么叫坚忍不拔,但她以自己的人生诠释着这四个字。
曾经有人问我:现在的作家最缺什么?老实说,我不是一个喜欢评头论足的人,不想谈论现在的作家缺什么这样一个比较尖锐和泛化的话题。我只是写我想写的东西。但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特别应该有一种悲悯情怀。在我的创作中,悲悯之心永远是比使命感更强大、更持久的动力。我之所以在缺乏农村生活的情况下斗胆写了春草这样一个农村女人,是因为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人群,看到菜市场里摆摊的夫妇,看到每天骑车赶场似地从这家到那家做钟点工的农村妇女或下岗女工,看到街头修自行车的男人擦鞋的女人,特别是看到他们身边跟着的脏兮兮的孩子,我就会想,他们怎样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和立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和悲伤?他们的希望是什么,他们得到过快乐吗?他们靠什么在坚持?他们的很多小事小细节都会触动我,使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咯噔”的一下,也许就是裘老师的一篇新作品,一篇也会使我们心里咯噔一下的作品。
女性文学和女人
裘老师说,她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军人,一个是女人,她的作品不会离她这两个身份太远。的确,在她的作品中有各种各样鲜活的女人。有人说写女人的作品,尤其是女人写女人的,难免会有“小女人气”。但读裘老师的作品,我却感到有一种天然的大气,甚至是大美的气质。如一些评论家所说,她从来不追求“先锋”,她放弃了外在的、表面的“尖锐”和“深刻”,但她那平淡的、感性化的叙述,却能直指人心,掏出人们隐藏最深的东西来。
我在作家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我是一个女人,比起其他军队作家多一些女性化的、温情的、细腻的特质,我的几乎所有军事题材的作品都是从感情入手的,没有大刀阔斧地宏观地描写过部队进军、作战或者训练的场面,即使是《我在天堂等你》,也是从感情入手去写的。但我同时又是一个军人,一个军人的后代,是从小听军号声长大的。几十年的军营生活潜移默化,使我不自觉地染上了浓厚的军人气质,军人的果敢、坚定、开朗和热情,修正了我天性中那种很柔弱、很忧郁的情愫,我也在有意识地克服那种眼睛只盯着自己鼻子尖的自恋心态。至于我的作品是不是属于女性文学,或者该划为什么流派,那是评论家的事,我从不去关心,也搞不懂。
在我看来有的女作家是很大气的,一点儿也不亚于男性作家。比如杨绛先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却从没有在作品中声嘶力竭地控诉,或者哭哭啼啼,或者仇恨,而是以非常平和的语气叙述着。她写她在“五七”干校,被剃了“阴阳头”,戴了一顶假发套,还调侃说,一边出汗,一边出不了汗。就是派她去打扫厕所她也非常尽职,每天把厕所打扫得干净明亮,全无异味,然后坐在便池旁看书、翻译。人生的态度到达这样的境界,才是一种真的大气。我一直很敬佩她。还有马丽华,她的《走进西藏》等作品,也是超越了自己的小世界,直接把自己投身到大自然中去感悟、去思考、去表达的。
我曾经看过裘老师的一篇文章,叫“一个无聊的话题”,是就电视台讨论“女人是否该回家”发表的议论。看到她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对一个社会问题的看法,并流露出明显的情绪,让我感觉有些奇怪。当我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时,这个一直保持着温柔的笑容和温柔的语调的女性,突然间语气激烈起来,正像她的那篇文章一样,让我们看到了她性格中犀利的、原则分明的另一面。
女人该不该回家?这的确是个无聊的话题。因为这是极少数嫁了有钱的丈夫,自己又想过安逸的生活的女人才会面临的问题。谈论这个话题,首先要刨去占一多半的农村妇女,她们要在地里劳作,在家里操持,哪里会想到什么回不回家啊!其次要刨去下岗女工,她们哪里想回家啊,她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个工作,把这种无奈的回家称为做全职太太,是一种可怕的冷漠;然后还要刨去离婚的女人,她们要一肩挑起家庭和工作,哪敢回家啊;最后还应该刨去那些热爱自己的工作、认为工作着是美丽的的女人。把这些人一刨开,还剩多少女性?我们的媒体为什么不去关注大多数的女人,不去关注更多的连送自己的孩子上学都很艰难的母亲,而去关心那些极少数好了还想好的女人?这纯粹是在讨好有钱人,这就叫媚俗!
有人竟断章取义我的话,说裘山山说女人该不该回家,主要是看男人挣多少钱。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认为女人回不回家取决于男人挣钱多少,那是对职业女性的侮辱。女人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女人也可以为社会作一份儿贡献,女人也需要有社会交往和社会的认同。多少时代多少女人的经历都已经证明,女人只有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才能拥有独立的人格——工作着是美丽的。
“养尊处优”与坚韧倔强
有文学界的人士曾告诉我,裘山山一直是养尊处优的,甚至是娇生惯养的。可是我看她的第一部长篇时,就有些不信,看了她更多的作品,尤其是看了《一路有树》以后,更是完全否定了这种说法。那个需要在幼小年龄就承受家庭突然遭难的懵懂女孩,那个在“首长”云集的军营中生活在一个普通工程师家里的女孩,心思越来越敏感细腻,性格却越来越坚韧倔强,所以她可以在学习上遥遥领先,可以成为技术标兵,可以仅仅复习一个月就挤上上大学的独木桥,还可以像个村妇一样,挑着百十斤的担子忽闪闪地自如行走,更可以独自一人在寒冷的冬天进藏采访,走遍高原的军营。
采访她那天下午,当看着她骑着自行车干净利落地迎向我们,之后听她那么温婉平和地谈论大大小小的话题,感受着她始终微笑偶尔又热情奔放的情绪,我的最终感觉是——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我不太走极端,我的角色和气质在作家和主妇之间,更偏重于主妇。我比较理智,什么都比较顾全,既支持丈夫、培育孩子、照顾父母,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方方面面都想做好。我不会为了写作抛开所有的一切或冷落什么,写作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事情,也不是生活惟一的目的。
就是这个“顾全”,体现了一种她对生活与取的态度,也给予了她幸福的充足理由和心理优越。这也许是使许多人对她产生“养尊处优”错觉的原因吧?但是,这种幸福和优越有什么错呢?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得失的多少,而在于对得失的看法。从这个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样的幸福,如果你不去争取和享有,就无须指责和嫉妒。
“人生是路,我们总在路上。你不能指望鲜花开道,但你可以企求——一路有树。”
看她的作品,看她的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深邃的思想、这样饱满的笔触、这样悲悯的情怀和这样一颗对生命中的点滴恩情充满感激的心灵呢?
“我的短篇小说的确极少有激烈的冲突,也极少有大喜大悲。我不否认生活中时常在上演大悲剧或大喜剧,但我这个人却不适合去表现那些‘大东西。天性使然吧。再者从某种意义上看,生活本身大都处于温和甚至是平庸的状态,但在我看来,这种状态正是寻常生活的魅力之所在……但愿我的温和的叙述,能对读者产生一种温和的魅力。”
这段摘自《一路有树》的话,可以作为裘老师对她的作品和她的这次谈话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