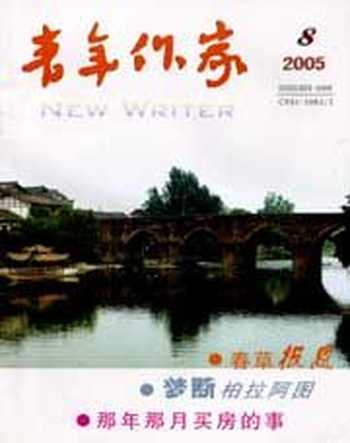眷恋今生
达 娃
勇来家那年,八岁。
大舅死了,很突然的消息。母亲伤心欲艳,悲痛地收拾东西准备去奔丧。母亲和大舅的感情很好,她是趴在大舅的背上长大的,母亲不止一次给我们说过她那辛酸的成长历程。
勇怎么办?母亲伤心地挂念着大舅的儿子勇。我们知道,勇的母亲,已在勇一岁的时候就没了。
“把勇给我接来。”我们的父亲发话了。在那样一个物质非常贫乏的年代,一个仅靠44元工资抚养三个孩子的工人,在大舅去世不足三小时就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们并不清楚这个决定在以后会带给父亲多大的重荷和压力,只是为父亲做出的决定莫名地感到暗暗惊喜。
终于,太阳落山的时候,母亲搭厂里运输的便车回来了。母亲的手里牵着勇,勇的怀里抱着一只鹅。勇怯生生的,带着一点点惊惧。
勇老表。我对着勇大叫。
不许叫老表,叫弟弟。父亲非常严肃地纠正我的称呼。勇来了,父亲是很高兴的,他带了勇去澡堂洗澡,剪去了一头鸡窝似的头发,从里到外换上全的衣服,我听他对母亲说,勇的衣服上尽是密密的虱子。
父亲做了包子,勇吃得很香,我们都猜测勇是很难吃到包子的。父亲和母亲在饭桌上给我们宣布:从今天起,勇是家里的人了,是我们的弟弟、哥哥,并要勇和我们一样叫他们爸爸、妈妈。勇一边喝着稀饭,吃着包子,一边很憨厚、很老实地点着头。
勇很快就和我们熟悉并玩在了一起。勇来之前,我们是很循规蹈矩的,采点野花,捉几只蜻蜓已经乐不思蜀。勇的到来,使我们对童年有了很深刻的记忆。勇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个空旷的世界:他会捉鸟,无论什么样的鸟他都喜欢,他会在我们不提防的时候脱去鞋袜,“噌噌噌”几下爬到树上,掏出一窝羽翼刚满但还无力飞翔的麻雀,用一根绳子拴住小麻雀的腿,像养一只小鸡一样。他会捕鱼,勇的水性是很好的,即使不下水,他也可以手到擒来。走在河岸边,他会突然俯下身去,用手一抄,一只泥鳅或者黄鳝就会稳稳地落在他的手里,从不落空。父亲会用他捉回的黄鳝做成香喷喷的鳝鱼面,母亲用面粉裹了小鱼小虾炸了给我们吃。我们跟了他去采“地末儿”,那是一种近似木耳之类的野生菜,加了豆瓣爆炒,香香的,好吃极了。勇最喜欢一窝小白鼠,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他用装眼药水的塑料瓶子做成奶瓶,里面装了米汤来喂养小白鼠。
勇非常熟悉田园中的一切,和他在一起,我们学会了在自然中释放自己。春天,勇和全举着自制的简易风筝,像个疯子似的在野地里奔跑,我和静则把母亲编织的风雪帽拴在腰上,采撷着各种野花野草,“顺便”也摘一点田里的胡豆,用家里带出的小奶锅煮了吃,就像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描述的一样。胡豆叶是很好玩的,用手揉匀了,放到嘴里吮吸,会变出一个像气球一样的东西。胡豆也是很好玩的,可以做很多东西,我们最喜欢做的是金鱼:选一颗胖胖的胡豆,穿过一根火柴棍,两边缀上两颗红红的蛇泡果做金鱼的大眼睛,在胡豆的底部刺一个小洞,插上一片很嫩很嫩的桉树叶,一个漂亮的小金鱼就做成了。做上十几个漂亮的金鱼,牵上细细的绳子,顺水而漂,真是好玩极了。
勇的到来让我们认识了萤火虫,夏夜,关上蚊帐,放出捉来的几十甚至上百只萤火虫,披散了头发坐在床的中间,任那些小小的闪亮的虫儿飞在自己的身上、头上、脸上,一闪一闪就像天上的星星调皮地眨着眼睛,自己也像童话中美丽的白雪公主。
秋天的夕阳是我们最喜欢的,我们常常在落日的余辉里,烧烤着勇捉来的泥鳅、黄鳝(有时还会有螃蟹),也烤“叫花小鸡”:把麻雀剥光洗净,抹上家里偷出来的盐巴,随便用什么叶子裹住麻雀,埋在预先挖好的小坑里,等那堆篝火燃尽时,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刨去灰烬,迫不及待地把烫嘴的麻雀往嘴里塞,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麻雀肚子里塞上几个鸟蛋。作料肯定是不够的,但我们食之甘饴,快活极了。
冬天的记忆都在屋里,成都的冬天阴冷潮湿,穿了母亲亲手做的小花棉袄,是不允许出去疯玩的。我们就缩在屋里游戏,“藏猫猫”、“捉强盗”……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也有着我们无尽的乐趣。勇和全专心专意地拆掉了家里的闹钟和小收音机,想弄清楚那些神奇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结果闹钟和小收音机在他们手里变成了一堆没用的废品……外面的那些孩子,因为羡慕勇的“能干”和我们之间的默契,也主动来我们家里和我们一同嬉戏玩闹,我们就像一群花果山没了大王管辖的猴子,上窜下跳,狂欢乱叫。
在我的童年,发生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小学末,我居然莫名其妙地“爱”上了班上的一个男生。此事在学校掀起了轩然大波,那个男生毁坏了我所有的文具,女生们像看怪物似的对我避而远之,我在接受完十几位老师连讽刺带挖苦的教诲后,又挨了母亲重重的一记耳光。如果不是父亲的阻拦,我可能就被母亲退学,做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半文盲了。我无法去说明自己的清白,也没有人相信,只好夹着尾巴做人,畏畏缩缩地生活在周围鄙视的眼光里。但是静他们不管这些,照旧和我做游戏,他们并不懂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需要去懂,他们只是觉得,四个人缺一不可。所以,在我无处伸冤的时候,他们那种很自然的亲情无形中弥补了我很大的创痛。多年以后,我偶遇了那个男生,仍然能够感受到对他当年暴行的恨意,也更眷恋和静、勇、全的那份亲情。因为这件事,我对人群有了一种敏感和恐惧,也不愿意再相信任何人,只是和静他们过着我们单调而又快乐的童年。
二十几年的相依相伴,相亲相爱,我们早已忘记了勇的身世,只觉得是一母所出。他服兵役,我和静、全眼泪汪汪地送走他,四年后他回来的那个夜晚,我们又是欢天喜地地闹腾到天亮,儿时的亲情与友爱已在我们心里扎根。
人是很容易去怀旧的,在我们的年龄随着季节的变化摇曳时,我们的思想已经定格在了被尘封的却又无时不为之眷恋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