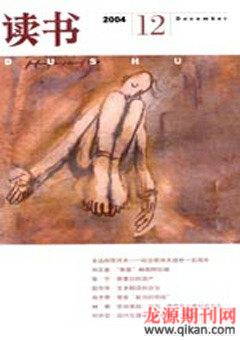新媒介世界中的社会
章文峰
上个世纪后半叶,我们还在为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媒介社会的前景而憧憬,今天已经真真切切进入了新媒介世界。早在一九九七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塔洛在《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一书中就提出了广告正在推动新媒介世界分割美国社会原有结构。今天我们可以说美国没有被完全分割,但是这一现象无疑正在引起人们关注。从广泛的角度看,约瑟夫·塔洛的观点也是今天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写照。
我们通常把新媒介世界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媒介资源过剩、媒介趋同、大众传播走向窄播、个人化互动媒体出现等等。约瑟夫·塔洛认为这种新媒介特质对如何将合适的信息抵达合适的受众形成了挑战。个人化视听选择的变化使得美国“正经历社会塑造媒介和阶层塑造媒介之间的重大平衡转换”,“这种转换鼓励的生活形态的分割对于社会结构是不健康的”。而左右媒介这种变化的正是一直支撑媒介产业的广告业。
约瑟夫·塔洛把阶层塑成型媒介定义为“鼓励社会的各个零散部分与自身沟通的媒介”,而社会塑成型媒介是指“具有潜力使得社会各个阶层进行相互沟通的媒介”。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向受众提供其他阶层狭隘而充满偏见的观点,强化各个利益群体的身份,而后者使得某些群体边缘化,使得群体超越狭隘立场而相互对话。阶层塑成型媒介和社会塑成型媒介两者是并存互动的。大众媒介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塑成型媒介在两者互动中成为主导,而新媒介时代则使阶层塑成型媒介成为主导作用。
按照作者说法,阶层塑成型媒介和社会塑成型媒介力量对比的转化动力来自“美国媒介目标营销与大众营销的平衡转化”。目标营销最早开始于R.雷斯的USP,发展到奥格威的品牌形象,直到一九八一年J.特老特和A.里斯的定位理论的提出,才使得目标营销成为主流。目标营销的理论基础在于市场细分。从理论上讲,所有的市场都可以细分,从而找到目标顾客,提高获利性和经营效率。市场细分的基准有人口统计细分、地理细分、心理细分和利益细分。在书中的描述中,传统的媒介往往是前三种细分标准,不免行之无效。而新媒介的细分受众更多的是利益细分。利益细分是一种基于因果关系变量的细分,研究的是消费者消费的理由。作为消费需求根源的生活形态成为了其衡量的主要标准。从历史纬度看,首先是由于一些特殊共同群体的出现如“嬉皮士”等群体,导致特定的个性和行为方式成为关注热点。“婴儿潮的一代”更是自我个性放纵和疯狂生活形态的追求者。生活形态细分已经可能,也成为必要。媒介与广告、营销传播公司“通过合作将消费者与生活形态联结,以使得消费者不断购买,并且对以生活形态为主题的广告与公关信息产生好感”。有人称之为“生活态营销”。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整合营销开始走向应用;其次是数据统计和调研工具的日益完善,使得生活形态细分的操作有了依托。因此,大众营销被抛弃了。
媒体零细化的增长首先是对社会分化的直接反映。社会分化与媒介碎片化是相伴随的。新兴媒介鼓励目标受众减少使用的媒介类型,分化为专一群体,并发展出独特的观看、阅读和收视习惯,从而培养对某些媒介的忠诚,也减少了体验社会多样性的可能。为了出售特定受众注意力的媒介在驱除不相关群体和吸引理想观众上是不遗余力的,广告作为媒介背后的力量,则是分化的关键性推动力量。其次是因为当代传播更多转向视觉文化传播。视觉文化的来临意味着文化形态的转变。商品的非物质化使消费社会趋向视觉文化,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一起引发了后现代特征。尼古拉·米尔佐夫甚至认为“后现代主义即视觉文化”。作为营销手段的广告则更需要迎合急剧膨胀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广告商在社会结构中寻找分裂,并出于商业目的强化和扩展这种分裂。帕雷托法则发展到极致就是必要地排除一些非重点客户,通过完美的价格歧视消除消费者剩余和无谓损失,使得利润最大化。广告以符合消费者个性化的信息抵达目标受众,达到最有效、最少浪费的传播效果。
当然作者并没有忽视媒介碎片化背后的其他社会力量。但他认为新技术只是提供了可能,广告业才是决定新技术运用方式的控制力量。因为广告商以巨额广告支出对媒介节目的制作和购买产生影响。广告主对节目形态的控制决定了节目的观众偏向。同时,书中也论述了,媒介的细分化不光是广告商的驱动的结果,也是媒介资源过剩的情况下竞争激烈的结果。小型的新媒介出于挑战传统媒介,争夺广告资源的自身利益需要一直在片面鼓吹媒介细分的必然性。
按照孔德的说法,大众传播的定位在于保证个人之间联系的能力以维持社会控制的整合和稳定,因此社会是通过传播构筑出来的。但是这个理论可能更多适用于美国社会。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没有教堂,没有政党制度。没有教育机器,没有知识分子,没有管理精英能像媒介系统那样成功加强民族凝聚力”。大众文化第一次给整个美国社会带来形象、思想和娱乐的内容。作为美国媒介商业化主导的广告业可以说正如书的翻译者所说,“帮助美国从移民的集合创造出来一个国家”。
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巨变的时期,社会结构形态正在转型中。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社会中媒介并没有像美国媒介那么大的力量。正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指出那样,中国社会阶层变化的主导力量是经济、文化、政治因素,而媒介只是一个很小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讲,美国这个媒介社会是一个媒介作用放大的典范。
传播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是商品化。即商品生产的逻辑开始制约传媒的运作。一切消费都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实施社会控制的具体方式。资本主义商品化使得整个社会物化,人们的眼光难以超越周围的局部,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和批判力。人们错误地把市场、商品、消费等量化的生活标准等同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在广告中,真实的社会结构被掩盖了,人们之间的阶级区分被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是否消费某一商品带来的区分。“于是代之以与他们生产东西的认同,人们被塑造成与他们所消费的东西认同……把使用批量制造的商品作为一种构成阶级或集团的方式掩盖了阶级差异。资本主义通过广告和市场营销创造出来,并完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显然是一种异化的产物。”人的需要被严重异化了。人的需要被掏空为抽象的需要,依赖于商品的获得。
到“二战”结束,媒介已经创造了一个美国社会共同体,越战等社会民众运动又使美国“同质性减少,日益分裂”,“二战”后的一代开始追求自身的个性和新型的小共同体。里根的自由市场政策更促使了美国民众的张扬个性,以及对个人生活的追求。基于此,广告从业者认为需要以各种视听形态来吸引狭窄的受众。再者是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美国人对新教伦理的丧失导致了消费主义至上,个人享受得到更大的关注。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物包围,并以物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社会。从福特主义强调大众市场和最大受众覆盖面到后福特主义的强调最集中的覆盖面和最小浪费程度的传播的转向说明了消费社会的来临。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起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广告和传媒通过推销有关或无关的形象来操纵人们的欲望和趣味。按照阿多诺的看法,其实并没有量身订做的产品,只是类型化。消费者自觉进入文化工业,成为了消费符号,就像福柯所说人们处于一种“全景式监狱塔楼”的观看。如果观众缺乏自制力,无疑会陷入更物质化的陷阱。阿芒·马特拉认为:“文化资本化也是主体阶层的资本化,扩大了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象征差别。由商业利润主导的文化交流背后隐藏着新的权力形式和新的社会整合形态。在后现代话语中意味着社会的终结,社会意识的蒸发,社会意识的缺失,乃至整个民族国家概念的淡化和消失。”
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来看,新媒介“对目标受众的点射”并不是简单的个人化,它使得个体能接触到某一细微共同点的人群,基于某一单一利益细分点的人群势必会在其他异质的利益点上冲突互动。虽然更多地发生在邻近的阶层,但是不可否认这也是社会互动的一部分。彼特·布劳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可以由一定的结构参数来加以定量描述,类别参数与等级参数相互交叉作用,从而使社会结构的类型显得更加复杂多样。新媒介技术的利益细分使得结构参数更加细化,有效地转化成新的时空关系,重构社会关系和感觉方式。因此,麦克卢汉认为人类正在回归到部落化,“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他说,“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质化的、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要略胜一筹。”广告作为媒介的内容,按照麦克卢汉说法,更像是窃贼吸引看门狗的“多汁肉块”。即使从书中家庭影院和卫星电视崛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受众依然是广泛的、异质分布的,只是媒介内容是特殊的。
所以当我们强调媒介消费个体的自主选择时,却忽视了主体自身被内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惯例正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着主体的行为。即使个体化的媒介也无法保证信息达到目标受众,因此大众化的媒体仍不可避免地存在。正如新媒介从来不会完全取代旧媒介,旧媒介会以更适应的形态出现了。
按照齐美尔的说法,一个阶层总是极力区别于其他阶层,这种模仿与差异化造成了时尚的流行。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从来就是存在的,媒介分割社会和整合社会也是从来就存在的,只是在新媒介情况下,分割的作用越来越引起重视。罗杰·菲德勒认为即使没有流行新媒介,目前的受众和广告分割水平,已经对大众媒介形成挑战。新媒介虽然加剧了这一状况,“但是仔细考察了每一种现存的媒介形式后揭示,彻底的分割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人际传播的电子形式和信息代理人不大可能代替其他一揽子信息产品,人们还是需要有共同消费媒介的。齐美尔认为,个人在个性化的同时也在社会化,因此群体的互动并没有像约瑟夫·塔洛在《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中设想的那样完全消失。
正如丹尼尔·切特罗姆在《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提出:“每一种传播媒介制度都是制度发展、公众文化和文化内容的渊源,而制度发展、公众反应和文化内容应当被理解为辩证的张力的产物。即对立的力量和趋势在时间的进程中冲突和演化。”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进步与新技术被政治和商业手段的误用可能性在冲突中平衡。具体来说,“技术的目的性总是暗示着每个技术对象的自发性适应先于它存在的社会性。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历史逻辑,技术逻辑服从于社会和历史的逻辑。新的个人和集体意义上的跨国化的信息传播生产机制使个人和集体的信息文化接受机制在各个不同领域成为一种消费活动。而营销和广告是任何消费模式的支柱”(阿芒·马特拉)。而约瑟夫·塔洛通过对美国广告业与媒介的互动的描述,部分揭示了这一运动的内涵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