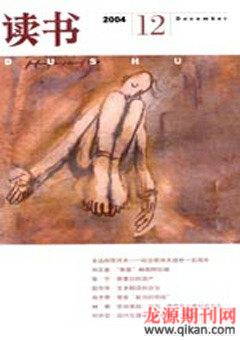手拉手还是心连心:什么是交流?
黄 旦
一八二五年,美国邮政总局成立了一个“死信处”,专门负责处理无法投递的信件,被人称为“邮件太平间”或“无头信收容所”。据估算,每年进入这个“太平间”的邮件多达五千七百万件。然而,让人心惊胆战的还不在于其数量,更在于“死信”这一称谓。它来自于基督教的一个观念:没有灵魂的信件,犹如失去了灵魂的人体,只能是一具尸体。
不过,“活信”变“死信”总有其原因,纵然是“命”不该绝。契诃夫的“万卡”不知道在信封上写地址,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彼得斯(Peters, J.)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英文名为“Speaking into the air”,译为《对空说话》似更宜)一书中对“死信”极尽凄婉之笔,既非为“死信”鸣冤叫屈,亦非为之唱挽歌,而是他认为凄惨的“死信”,恰恰就是当前人际交流特有病态的绝妙写照。人类自身对此至今没有足够认识,差不多都成了“万卡”的爷爷。
对于“死信”的疑虑,追根溯源,似乎可以在十九世纪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中找到轨迹,而且彼得斯也以为,交流危机在认识上的凸显,就来自于这个时期。詹姆士说:我们每个人都把宇宙分为两半,而且用同样的“我”与“非我”给这两半命名。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成为人类既定特征。“思想之间的割裂,是自然界最绝对的割裂。”既然如此,所谓的交流沟通和意识共享,岂不就是痴人说梦般的可笑?倘若说邮寄信件变“死信”尚属无意之结果,日后或许还有补救的机会,那么,按照詹姆士的“我”与“非我”之界限,交流中的“死信”就是必然规律,任凭主观努力也是无济于事,因为谁能在“割裂思想”之间铺设桥梁?
苏格拉底——古希腊的这位伟大哲学家以为可以。
在柏拉图撰写的“Phaedrus”里,苏格拉底把交流等同于爱欲。爱与被爱是一种双向的互惠,就像“和风和回声如何从一个光滑结实的物体返回到发出的源头”,“他不知道,他在爱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就像在镜中看见自己一样”。既然爱可以经过双向回路,互通心曲,那么,在传达爱的同时,不就是成功进行了人际的交流?不就等于实现了心灵与心灵的交接?两情相悦的爱欲,使两个个体心心相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相依相偎在伊甸园中。
当然,苏格拉底不以为交流都是可以飞流直下,畅通无阻。不是爱欲式的口头交流就不行。交流的障碍来自于交流的手段或形式——文字和书写。写下来的字就像绘画一样,“你认为它们在说话,好像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再追问这些字,它们始终是那个老样子,永远是那个意思。一旦写下来,每一段话都会到处滚动,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没有关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它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话、不对谁说话”。这与爱欲不是一回事,而是任意乱交,是信息的撒播(dissemination)。所以,交流的成功要有手段的保障,亲切专一的口头问答式对话,是最佳渠道。只要手段得当,就没有打不通穿不透的意识“围墙”。
这也很符合伟大先知耶稣的基本认识。不过相反,耶稣却是喜欢广种薄收,并且以为交流本就如此。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又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不断重复的寓言,表明耶稣与苏格拉底一样,把交流成功的希望同样寄托在手段之上。只不过他的倾向与苏格拉底截然有别。他执著于撒播种子式的交流,至少这在形式上可以保证人人平等,是一种博爱,(当我们现在百般推崇频道专业化,不厌其烦地罗列分层传播好处时,是否也有必要想一想耶稣的撒播?)不像苏格拉底的“爱欲”时不时透溢出一种贵族气。至于普撒大地的种子,最后是进鸟腹、日晒干枯、被荆棘所埋还是结出丰硕果实,那是听者的“慧根”和福分,与言讲者无干。所以他十分大度地高声宣叫,“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广种薄收,绝不是只求耕耘不管收获,类似于现代传播中不顾自己对象的单向发射。只是在耶稣眼里,交流的结果犹如不同环境中的种子,其命运殊难预料,各人有自己的解读和理解。心灵周围虽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可“风”从何处进入,缝隙有多大,全凭听讲人自己琢磨和意愿,外力无济于事。既然如此,与其不自量力地对症下药,还不如一视同仁,杨柳微拂,遍洒甘露,把解释权交给听讲者。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悉听尊便。否则,哪怕是强按牛头,最后的下场不见得比对牛弹琴好多少。
苏格拉底和耶稣的貌似分歧,掩盖不住他们骨子里的同一。在他们看来,交流中如果发生了“死信”,其根本症结也绝不是意识的隔绝和“我”与“非我”的隔离,而是构建这条“心灵纽带”的材料和方式。于是,交流的问题就变成了手段的问题。只要手段合适,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千难万险只等闲。思想意识的交融就自然轻而易举,不在话下。“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在设法改进其对于周围事物的消息情报的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时又设法提高自己本身传播消息情报的速度、清晰度,并使方法多样化”(《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流委员会对人类传播历史整个发展和走向的概括,似乎就是为苏格拉底和耶稣的看法做注脚。
然后登场的是被彼得斯称为“现代交流观念的基础”的圣奥古斯丁和洛克。圣奥古斯丁认为是“道在肉身”,二者是一个统一体。但肉身不是道,是“道”的符号,“道”的载体。“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因此只要超越符号追寻意义,彼此就能心领神会。符号在洛克眼里,同样是思想的容器。“字眼是沟通思想的必要的明显标记”,“思想若不能传递,则社会便不能给人以安慰和利益,因此,人们必须找寻一些外界的明显标记,把自己思想中所包含的不可见的观念表示于人”。“只有这样,他的观念才能表示于人,人心中的思想才可以互相传达。”(《人类理解论》)由此,如果交流出现“死信”,那也显然不是头脑的孤立和思想的孤独,而是被外在表意的载体迷惑了眼睛,从而无法洞悉各自的内心。也就是说,假若能直接获取符号背后的意义,思想从一个头脑钻进另一个头脑,不仅可能而且必然。“communication”一词从原来表示物质的传输,扩展为精神和观念的运送,其首创者就是洛克。如果说圣奥古斯丁是把基督教中的“天使”形象,搬到了交流之中,那么,后来的培根、牛顿等,逐渐把经院哲学中“天使”转化为科学的范畴。“以太”、“引力”、“流体”等等,为形而上的远距离心理共振和移情感应提供了解释的新依据。十九世纪擅长催眠术的梅斯梅尔医师,用所谓的“动物磁力”治疗人们的心理并因此形成所谓“梅斯梅尔术”,也就绝非偶然。难怪他认为自己就是“研究人类心灵的牛顿”。
摄影术、电影、留声机、电话和电报等等的出现,使记录并远距离传输思想、形象、声音变得稀松平常,圣奥古斯丁、天使、圣灵的梦想得以具体展现。人不仅终于可以离开实在的身体实现精神和心灵的共享,而且与死者的对话也不是奇迹:任何一个人只要留下自己的声音面貌,哪怕乘鹤西去,后来者照样能与之心心相通。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美国全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开通,莫尔斯在第一份电报中,写下的竟是这么几个字:上帝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倒让人想起《圣经》中的一句话:“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新技术带来的震撼、兴奋、好奇、激动与不安,除了把一切归之于上帝的神迹和荣耀,实在想像不出还能有其他。历史学家和早期电报的支持者谢夫纳的话也许更能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态:“闪电,这神话中耶和华的声音,无所不在的云中恶魔,终于被人们征服了,在痛苦的束缚中履行信使的职责——到世界各地去悄声低语吧,高贵的人发出了高贵的命令”(转引自《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人类交流的困难在技术的发展中迎刃而解,时间、距离、生者、死者,一切都不在话下。如果说苏格拉底和耶稣还在为一对一还是“撒播”而各执一词,那么此时的人的关系,人的“交流”,完全就是如何恰当地调整频道,减少噪音。交流的缺陷仰仗于技术,可是任何技术都不能十全十美,新的技术带来新的问题,于是就苛求更新的技术。在彼得斯看来,人类的交流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循环的技术矛盾体:技术既是病人又充当医生。当下互联网被寄予的厚望,探测器对其他星球生命的不断探询,显示人类对交流的渴望和坚信,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对技术的自信。
大众传播的研究和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线路中出现。报纸、广播、电视的产生,不仅一刀斩断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联系,而且传播研究与一般的通讯技术也分道扬镳,开始逐步走向体制化。态度的转变,心理的影响,宣传的力度与技巧,所有衡量的重点和尺度全是关于传播究竟发生了什么作用。至于是否真的有效,真的可以互为沟通而心连心,根本就不在考虑之内。拉斯韦尔的“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有什么效果”的五W模式,处处显露出信息、通讯、控制的理念痕迹。天使的心灵交融,也就适时转变为更有科学理性意味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可人、动物以及机器之间的所有界限因此被抹得一干二净,人像机器那样做出反应,人也像控制机器那样来控制人。于是,交流研究的重点变成公共舆论的管理,变成政治或军事的灌输式宣传与反宣传,变成消费行为和倾向的勾引。传播的功用强大而又无所不在,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希特勒的德国及其《我的奋斗》,就是踏在这样的云梯攀登上理论和实践的顶点。从“魔弹论”到“有限效果论”再到“强效果”,尽管看法有差异,可有谁怀疑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可能性?
当然不是没有。其实,当耶稣把话语的最后解释权交给听者时,就已经明确地留下了一个悬念:听者理解的多样性无法回避。由施莱尔马赫到狄尔泰到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就是循着这一面而展示其疗方。他们所想做的,是试图通过对文本的解释来实现人们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发送和接受之间的不对称甚至裂沟,至少让人们看到,编制和发送信息与解释和接受信息并不配套,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活动。英国的文化研究,尤其是霍尔和费斯克,正是这条线路的延续。
然而,诠释学虽然注意到交流的断绝,但也不以为就是“死信”而无可救药,只要有诠释,“信”还是能够“一息尚存”。跨越距离的传播,虽比不上亲身的接触,也不能否定是接触,更不能贬低其存在,哪怕这只是一种诠释的接触和沟通。这就不像爱默生。爱默生就既拒绝诠释,也不对交流抱任何的幻想。对于朋友试图加强更加密切关系的愿望,其回报的竟是如下的字眼:人与人之间豪猪似的不可接触性。
豪猪似的不可接触,倒也不缺乏理论的支撑。假若是信息理论为大众传播理论搭建了构架,那么,物理学的发展同样也为人与人无法沟通提供了证据:远距离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因此,空间的干涉作用是惟一的作用。通过实验麦克维尔告诉人们,即便是“受重力压迫,透镜也不是绝对接触的”。这就是说,绞尽脑汁,人与人的接触本身仍还是一个幻觉。交流就意味着“死信”。其实也是,如果人与人的头脑毫无隔阂,思想可以由这边直接飞到那边,沙叶新的剧本《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中,那种不同颜色的思想注射液,以及要通过这样的注射给人洗脑,也就不成其为荒唐可笑的闹剧了。
在十九世纪后期的英美唯心主义者的作品中,此种声调此起彼伏。洛伊斯和布拉德利笔下的交流意象,常常是两个各自完全封闭在自己房间里的人物。布氏在《表象与现实》一书中就认定,“有限存在物的直接经验,是不可能相会的;直接占有别人的脑子里隐私的经验,最终是没有意义的”。艾略特的《荒原》引用了布拉德利的一句话,这句话也因此而名闻遐迩:“完全的外在感觉,和我的思想感情一样,是我私密的东西。无论是外在的感觉还是内在的思想感情,我的经验都锁定在我的圈子里,这个圈子是从外面锁定的;圈子内的成分全都相似,对圈子外的人来讲,这些成分是不透明的……简言之,如果把这个世界当作宛如灵魂的存在,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的灵魂来说都是独特的、私密的。”这与《荒原》所试图表达的主题,的确是十分吻合:
我听见钥匙
在门里转动一次,就只一次
我们想到那把钥匙,每个人都禁锢在他自己的囚室
想着那把钥匙,每个人心里都确认了自己的囚室。
艾略特描写的交流失败的场景,在卡夫卡的《城堡》中,变成了与一个看不见的影子搏斗。沃尔夫笔下拉姆塞夫人的同情与热情,与拉姆塞教授的冷漠形成强烈的对照。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是行同陌路人。幽闭、自我,禁锢与隔膜,不时回荡在二十世纪,诸如奥尼尔、萨特、尤内斯库、贝克特、阿尔比等等的艺术和社会思想中,无疑隐藏着对——“死信”——人与人无法交流的恐惧和担忧。
十九世纪末所创造的两个新词:传心术和唯我论,非常巧妙地代表着关于交流的两种传统。交流究竟是桥梁还是沟壑?是心心相印还是远隔千山万水?是精神的纽带还是永久的“死信”?交流到底是什么?
彼得斯以为,交流的鸿沟是无法回避的。即便是爱欲式的面对面,所使用的也是对话的碎片和断续的连接。因此,你心中想到的对象,也许永远不能够和实际的伙伴完全一致。把直接共享真相付托给交流,本身就属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一厢情愿。它顶多只是进行效果的操作,以激起对方心中最真实的形象。再现未经修饰的真相,可能与彻头彻尾的欺骗一样愚蠢。那又何苦为一个人类自己所无法承担的责任——自己的言行在对方心灵中的所谓真实反映而上穷碧落下黄泉?既然如此,交流的互动本来就不是思想的交融,充其量不过是思想的舞蹈;在这个舞蹈中有时也许能够触摸对方。衡量交流是否实现的一个比较实际的尺度,就是看后续的行动是否协调。交流因而不应该成为难以承受的孤独心灵和可怕的幽灵,更不必把无法交流视为人类的悲哀和不幸。事实上,对交流的悲叹正是来自于对交流的期待。说到底,“为我论”和“传心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彼得斯的结论是,交流不是忠实于我们的地盘,坚执自己的理念并施加影响。交流是对别人抱原谅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看自己那样来看我们,犹如你也不可能像他们自己那样看他们。我们的问题不应该是:我们能够交流吗?而是应该问:我们能够互相爱护,能够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吗?我们不可能彼此相同,不可能你是我,我是你。最好的情况是把“交流”用来描绘补偿这个不足的字眼,而不是试图打破你我的界限。交流的快乐,不在于超越、克服彼此的障碍和隔阂,而是在于交流本身的圆满。恰如梅尔维尔在《白鲸》中为我们描画的:来呀,我们大家手拉手,拽紧手;让我们紧紧贴在一起。由是,我们首先所担忧的不应该是意义能否相通,不应该是如何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消除“死信”。而应该是关爱别人,应该担忧关爱邻居、他人、朋友乃至异类所存在的重重关隘——客观的或主观的,好意的或别有用心的。
当然,彼得斯的“手拉手”未必能激起大家的喝彩,更不必说人人响应。然而,如果我们能多一些手拉手,少一些“心连心”,不因无法连心而拒绝拉手,更不是为了连心而使劲拉手,我们的交流是否会更顺利、更轻松而且更充满乐趣?可是有谁愿意呢?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彼得斯著,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二○○三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