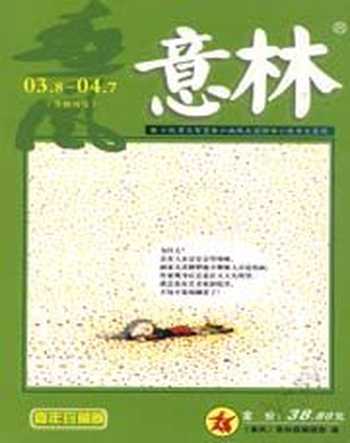母亲的蒲公英
苏珊尼·采琴 杨振国 译
我在一个小镇长大,从我家到小学校只要步行10分钟。在那个年代,孩子们可以回家吃午饭,并且发现母亲在等待着他们。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我认为,母亲理所当然就该做三明治,理所当然就应该欣赏我的手指画,理所当然就应该检查我的作业。那个充满理想、聪颖灵秀的女人在我出生以前本来是有一份工作,后来又回去工作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在我上小学的那些岁月里,每天吃中午饭时都会只和我在一起。
我只知道中午放学的铃声一响,我就朝家里飞奔而去,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母亲总会站在台阶的最上面,低头冲我微笑,那神情分明告诉我:我是她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有时,听见某些声音就会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母亲拿茶花壶那尖厉刺耳的声音,地下室里洗衣机那隆隆的轰鸣声,她匆匆走下楼梯迎接我时我的小狗的牌照丁当作响的声音……而现在这种时间安排充斥着我的生活。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上三年级时的一个午饭时光。学校要演戏,我已经被选中扮演公主。几个星期了,母亲和我一直在不辞辛苦地排练我的台词。可是不管我在家里台词背得多么滚瓜烂熟,一上舞台,每个词儿都从我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老师把我拉到一旁。她解释说,她给剧本加了一个解说员的角色,要我换角色。她的话说得虽然很轻,但还是刺痛了我,尤其是看到我的角色给了另一个女孩子时,我更加悲伤。
那天回到家时,我没有把我的这种悲伤告诉母亲。但是她感觉出了我的不自在,所以她没有建议我练习台词,而是问我想不想到院子里走一走。
那是一个可爱的春日,棚架上的玫瑰藤条在变绿。在那巨大的榆树下,我们看见一朵朵黄色的蒲公英从草丛中冒了出来,仿佛是画家为我们的风景点缀上了一抹抹金黄。
我看见母亲在一片花丛中漫不经心地弯下腰。“我要把这些杂草都挖掉。”她猛地一拉,把一朵花连根拔起,“从现在起,我们花园里只要玫瑰花。”
“但是我喜欢蒲公英呀!”我不同意了,“所有的花都很漂亮啊———连蒲公英也是。”
母亲严肃地看着我。“是的,每一种花都有它自己的美丽,不是吗?”她若有所思地说。我点点头,很高兴把她说服了。“人也是这样,”她接着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公主,但这没什么丢人的。”
她猜出了我的痛苦,于是我哭了起来,并向她诉说发生的事情。她一边听一边对我安慰地笑。
“但是你会做一个出色的解说员呀,”她说,并提醒我,她是多么喜欢听我朗诵故事,“解说员的角色和公主的角色一样重要。”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在她的不断鼓励下,我渐渐对这一角色感到自豪起来。每到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就朗诵我的台词,谈论我穿什么衣服。
演出的那天晚上,我在后台感到十分紧张。就在开演前几分钟,老师向我走过来,“你母亲让我把这个给你。”她递给我一朵蒲公英。花片的边儿已经开始卷曲,从根茎那儿懒洋洋地耷拉着脑袋。然而看它一眼,我就知道母亲正在外面的台下。想到我们吃午饭时的谈话,我心里开始充满自豪。
演出结束后,我把那朵花塞进演出服的围裙里,带回了家。母亲用两片纸巾把它包了起来,夹在一本字典中,她一边夹一边哈哈大笑着说:“或许只有我们才愿意把这么不起眼的一棵草夹起来吧!”
沐浴在中午柔和的阳光中,我常常回想起我和母亲一起度过的午饭时光。它们是我童年生活中的逗号,这些逗号告诉我:生活的滋味不是在预先丈量好的增长中体验到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以及和亲人们随意度过的小小的欢乐中体味到的。
几个月前,我母亲来看我。我请了一天的假,请她吃午饭。餐馆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生意人在谈生意,并不时瞥一眼手表。在这些食客中间,坐着我和如今已经退休的母亲。从她的脸上我看得出来,她非常喜欢上班族的工作节奏。
“妈妈,我小时您在家里呆着肯定乏味透顶了吧?”我说。
“乏味?做家务是很乏味。可是和你在一起可是从来不乏味呀。”
我不相信她的话,于是我说:“孩子当然没有工作那么令人兴奋了!”
“工作是很令人兴奋,”她说,“我很高兴我曾经有一份工作。但是工作就像一只开着口的气球,你只有不断给它充气,它才能一直鼓胀。而孩子是一粒种子,你要给它浇水、精心呵护,然后它就会自己长成一朵美丽的花儿。”
此刻,我看着她,蓦然感到我们仿佛又坐在了她的餐桌旁,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要把那朵变成褐色的酥脆的蒲公英夹在两小片皱巴巴的纸巾中间,保存在我们家的那本旧字典里了。
文/刘宜学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