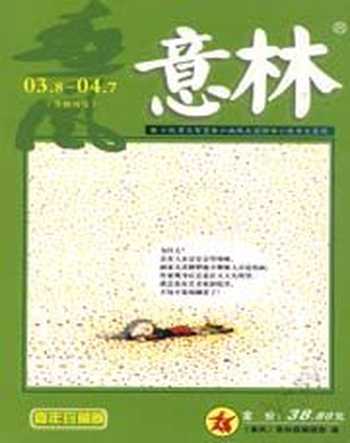水的记忆
魏 雷
有些事情会在你的脑海里潜伏很久,牢牢地蛰伏于你人生的路径上,每次想起都会让你深思,感慨万端。在我的生命里曾经流淌过一碗水,是这碗水让我懂得了绿色的珍贵和生命的意义,一滴又一滴的水珠鱼儿一样游荡在我脑海深处,它们与我亲切而贴近,时时在对我诉说着它们的存在。
暑假时,久居都市的我决定与朋友结伴西行参加社会实践。车子在高高的黄河大堤上爬行,黄河河底或龟裂或时断时续,不管往哪里看都好像是褐红而又惨白的颜色,那颜色让人想到了刚刚燃尽的一炉炭火,仿佛你触摸一下就能烫出一手燎泡,一阵微风吹过就有死灰复燃的可能。
天热得像发了狂,我们挥汗如雨。在黄河的拐弯处好不容易见到一个村子,村子因树而得名,叫“五棵树村”,据说那里前几辈的时候,全村确确实实只有这顽强生存下来的五棵树。现在环村已种下了不少小树,显然栽上没几年,虽有些弱不禁风,但多少给这黄河装点了几分生命的绿色。
在村头有个苗圃,绿阴一片,让长途跋涉的我们略感一丝凉意,一个小姑娘拿着一个特制的大瓢,瓢的下端有个长长的滴管,在每一棵小树苗根上小心地滴上一点点水,那动作好像是轻抚睡梦中的婴儿。
“小姑娘,能不能给点水?”我一边问一边不停地用毛巾擦着好像永远也擦不干的汗,渴望能洗一把被汗水渍疼的脸。小姑娘迟疑了一下,转身走向苗圃后面的屋子,屋子里的椅子上坐着一位老妇人,脸上带着世事洞明的安祥,小姑娘轻轻对她说了些什么,老妇人点点头,从腰间“哗啦”一声摸出一串钥匙,这时我才看见在屋子和苗圃之间有一眼水窖,水窖设有坚固的木盖,木盖上牢牢地锁着一把大铁锁。我曾听说水窖是这里人的财富,如果谁家的儿子想让人介绍对象,准会夸张地说自己家里有几眼水窖,因为这里的水比油珍贵。
只见小姑娘轻盈地走到水窖前,熟练地打开大铁锁,用一个小木桶小心地汲出一点水,倒在一个干净的白瓷碗里,然后小心地用双手捧着那碗水,走到我面前说:“走远路渴了吧,快用吧!”我看了一眼,那水竟漂浮着一些细小的杂物,在白瓷碗里更显得浑浊。其实我只是想要一点水洗把脸凉爽一下,饮用的水我独自带了许多瓶装的纯净水,况且这不干净的水似乎根本不能喝。等小姑娘转过身来继续汲水给我的其他同学,这时我则让同伴把那碗水倾倒在我手上,开始洗脸。
听到水落地的声音,老妇人和小姑娘都不约而同地转过来愤怒的看着我,老妇人“腾”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开双臂大喊“作孽呀!”随后竟然一个趔趄又摔倒在地上。小姑娘却没有去搀扶老妇人,而是惊叫着跑到我的身边,迅速地抢过我的同伴正在倾倒水的白瓷碗,然后竟然跪在我的脚下,伸开双手用力去挖我脚下那一点被水浸湿的土,直到她挖到见了干土后,才把手中的湿土捏成一个湿泥团,又跑到苗圃旁新栽的小树边,深深地挖了一个坑,把湿泥团贴着树根埋下。做完这些,小姑娘这才急切地叫着“奶奶”向老妇人扑过去,慢慢把老妇人搀扶到椅子上。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惊呆了,一时间戳在那里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这时我才发现老妇人瘸了一条腿,刚才摔着的正是那条瘸腿,老妇人抚着那条伤腿痛苦地呻吟,我和同伴慌忙跑过去赔罪,老妇人铁青着脸不理,小姑娘不住地抹着眼泪。
老妇人默然的愤怒深深刺痛了我,如果做些什么能补偿我的过失,我一定不遗余力地去做,但老妇人只是愤然盯着刚才被小姑娘挖的小坑,表情怆灰而悲痛。良久,我们才从小姑娘口中知道,老妇人是这村里原来的妇女干部,上了年纪后主动要求来到村头培育苗圃,这村周围和黄河大堤旁的小树苗都是她老人家培育出来又一棵棵栽上去的,由于连年缺水,老妇人便挖了这个储水窖,前年遭遇大旱,水窖里也难存住水了,为了刚栽上的小树苗能够成活,老妇人翻山越岭徒步二十余里的山路去挑水,不料在一次途中一脚踏空摔下山坡,瘸了一条腿……老妇人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不是我小气,这样热的天,我的苗圃一天才用我自制的那一瓢水,你们不知道吃水的苦,可这样糟践水我心疼呀!……”
我愣愣地立在那里,眼里竟充满了泪水,因为我知道这世上不仅有繁华的都市,还有饥渴难耐的黄河乡村。
文/曲意波摘自《辽宁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