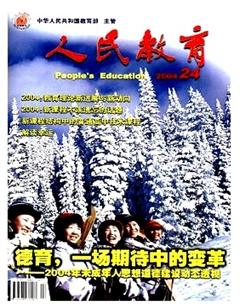回到文本,回到语文的地面
赖配根
语文界曾经很流行一句话:语文的外延与生活相等。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语文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并通过与鲜活的生活实际相联赋予语文教学以灵气和生動,那么,这样的“大语文教育观”是值得赞许的,《语文课程标准》不就提出要“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吗?而且,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由于许多语文老师把生活的“活水”引入课堂,同时努力为学生创设语文活动实践的机会,把语文学习延伸到课外,语文教育因而变得生动有趣。
然而,有些语文老师的课堂开放之后,出现了教学目标迷失的现象。新课程强调探究,进行探究性学习应该是语文教学走向开放的重要途径。那么语文该如何探究呢?我们知道,科学课的探究是要遵循一定规则的,一般要有“发现问题一提出假设(或猜想)一验证假设一检验结论”等大体的过程(当然,并不是所有科学课的探究都要严格遵循这样的模式)。语文课的探究不可能照搬这样的模式,但是不是也要遵守一些基本规则呢?比如探究要从具体的文本而不是凭空出发,最后回归而不是远离文本。可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是,老师要求学生收集大量信息并在课堂上交流,而这些信息并没有与理解课文联系起来;老师极力鼓励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课堂因而变成与文本毫无关联的众声喧哗;老师让学生进行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语文研究性学习,而这些活动与平常的语文学习无关,成了脱离日常教学、仅供参观的展品。这样的开放性语文教学,就像被放飞而断了线的风筝,与真实的语文教育大地渐行渐远。
语文是一刻也离不开文本的。不管语文是向生活开放还是向活生生的人开放,教学目标的制订与完成、教育意义的产生和丰富都只有通过师生与文本尤其是文本的细节的深入对话来实现。刘老师对此一定是有深刻体会的。他的这篇教学案例,定位于探究性阅读的探索,走的是语文研究性学习活动的路子。粗略浏览,看到的也就是人云亦云的大语文教育而己。如果你真的是这种感觉,那么我建议你再回过头去细读一次:读他的怎么让学生探究感悟,读他的怎样引领学生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诗歌。这时候你也许会猛然发现:他的教学原来是如此地扎根于文本的土地,从而催生了真实而丰盈的教育意义。
毛主席的《七律·长征》,气势磅礴,胸襟开阔,既有革命的浪漫情怀,又见历史的岁月峥嵘。但是,自幼生长在和平时代的小学生,又如何能体认这样的意境呢?从解释学出发,我们必须让学生形成一定的“前见”,即要让学生对长征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甚至较为深刻的理解,以提供走进文本的必要经验和心理结构,否则,学生对《七律·长征》就难以形成有意义的理解。因此,教学向历史开放,向各种课程资源开放,甚至组织研究性学习,就成了许多老师的选择。但是,“前见”的形成是为走进文本服务的,信息的收集、课外的大量阅读和调查,最终要与解读、丰富文本的意义有机地联系起来,而有些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环节走了岔路,他们或者过分惊喜于学生带来的“意外精彩”而抛弃文本走向海阔天空,或者对教学目标没有明确认识而任由教学朝着远离文本的方向行进。
刘老师的可贵就是在这样的关键环节及时地回归了文本—他引导学生利用收集来的大量课外资料讨论解决诗歌阅读中碰到的难题;不是解决一般的难题,而是解决关系到诗歌意义阐释的关键字眼(“暖”与“寒”)的理解难题。因为熟悉了长征历史,学生已经能够自觉地“移情”于诗人创作时的心境,对描写自然气候的“暖”与“寒”的理解就自然地上升到情感、精神的层面;有了这一层面,学生对文本的把握就扎实了,对诗意的体验就丰富了。毫无疑问,没有“前见”的形成和在此基础上对文本的亲近甚至“纠缠”,学生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可惜的是,当学生已经能如此用诗意的眼光来阅读诗歌的时候,刘老师没有进一步引导,比如让学生用类似的方法来观照、解读整首诗歌,体会诗境的阔大;甚至还可以拓展开去,例举诗词名句如“红杏枝头春意闹”、“战地黄花分外香”等,让学生体会诗歌的妙处—没有对文学艺术本身的欣赏,对作品思想主旨和意义的归纳、抽象就容易变成无病呻吟。
回到文本,回到文本的细节,回到文本的血脉,回到文本的意义场,语文才能获得力量,这是我阅读刘老师的这篇案例时获得的最大的启示。凑巧的是,不久前,新课程专家方智范撰文呼吁,语文教师要“尽可能正确、到位地理解和把握文本”,“成为文本作者的‘知音”。这样看来,回到文本,回到语文的地面,应是日渐浮躁的语文教育界要重新拾起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