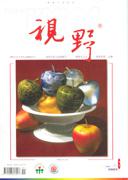一秒钟32步
施国安
一秒钟32步—一这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水平。击打根本无法区分,只听到阵阵类似蜜蜂发出的嗡嗡声。这只蜜蜂叫迈克·弗莱利。他是当今吐界上最著名的踢踏舞王。
他的两条腿的保险费为4000万美元。
弗莱利可称作是一块跳舞的料。他创建的舞蹈团Lord of the Dance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节目一一舞蹈、艳丽的服装、戏剧性音乐和现代烟火技术。照弗莱利先生的说法,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多少都是舞者。
记者:弗莱利先生,你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一种舞蹈,或者你还是把职业和生活加以区分?
弗莱利:我在舞台上跳的时候,与其说我在从事某种工作,不如说我进入了一种非常惬意、非常合我本性的状态,我以此为生。每次演出结束的时候,我总是很难从我的“那个”生活中摆脱出来,回到地面,回到大家认可的生活中来……事实上,现实和舞蹈还是不同的东西。对我来说,舞蹈就是我的生活,是第一位的。
记者:不过,如果尝试一下的话,是否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和某个舞蹈作比较?
弗莱利,当然可以。不过,我想说的是,生活恐怕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最不可思议的舞蹈的汇合……但是除此之外,对我们的演出还有着某种整体的感受,它能使观众脑海中浮现出某个整体的,以某种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的舞蹈……这就是对世界的最准确的反映。华尔兹在1 9世纪某种程度上正是这样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最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和谐和平稳。20世纪初出现了探戈,一种更具活力、更强烈、更具摧毁力的东西,而它也是世纪之初的准确反映。20世纪下半叶当然是摇滚,节奏开始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现在我们大家的生活节奏快得发了疯,主要任务就是赶、赶、赶……容我斗胆期望,我们的演出是最准确反映21世纪节奏的尝试。
记者:知道吗,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现在不兴跳双人舞,要不独舞,要不一人群人在舞场上群舞……另外,如今年轻人不叫跳舞,而叫……怎么说呢……跳几步……
弗莱利:是的,世界在变化,我们大家在变。你注意到没有,人们现在去迪斯科舞厅不是为跳舞,是吧?舞蹈不是目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人们去舞厅出于其他目的……要感觉自己是完整的,要自我表现,要充电……我不是心理学家,不打算解释大众跳舞的现象……但是,我能理解独舞者。这是现代人用来表现绝对自由、完全个性化的形式。这不是和世界的对话,而是独白,一个有关自己完全独立的声明:“这就是我,请接纳这个原本的我。”现代艺术有个新概念“新解剖学”,其实质是:生理、遗传和文化空间已经变化,与之适应的应该是另一种动作。我们看到的正是如此。
記者:你在某次访淡中说过,除了自己著名的踢踏舞,其他舞你都不精通。为什么?
弗莱利:确实如此,华尔兹我就跳得很笨拙。如果我要想跳各种舞都能取得成就,我就没法更多关注自己喜欢的。你知道,人是多才多艺的,但是在某个阶段他得选择某样他做得更好的东西。只有成为某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一个人才会取得成就。我把踢踏舞称作舞蹈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舞蹈。我跳的是快速度的爱尔兰传统舞蹈,但同时我配合了上体和上肢动作。这是某种我用一些细节做成的东西,没法下什么定义。换句话说,某种大杂烩……
记者:甚至著名的艺术家现在也陷入非常复杂的境地。他们被迫考虑的不是创作,而是有没有市场,能刁;能赚钱……
弗莱利:确实,如今艺术家不仅要考虑出新作品,还得考虑怎么推出、保存自己的作品,同时还要尽力不去关注多余的东西。今天艺术家的生存形式与其说在于了解新事物,不如说是要把自己和一切不需要的东西隔开。现在的世界、现在的艺术中影响我们的荒谬东西实在太多,艺术家首先必须学会区分什么是真正的东西,什么是假冒伪劣。比如说我,已经1 5年不看电视,我根本没有电视机。我禁止自己看电视,而且一点不为此惋惜。(罗大友摘自《世界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