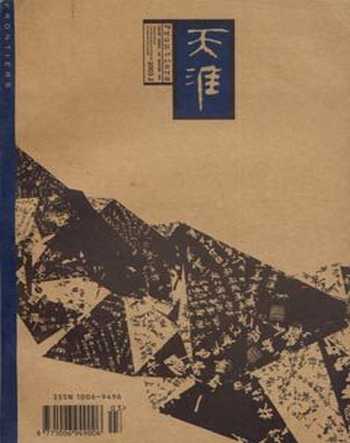媚俗的改写
刘再复 林 岗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虽然距离今天并不遥远,但是它的版本复杂和由此造成的困扰并不亚于古典的研究,两者所不同的是古典文献的版本困扰多数是因流传过程中后人的传抄、删改、修订而造成的,而二十世纪文学的版本困扰多因作者本人在不同时期的重编、改写而造成的。许多现代重要的作家都曾经重编、改写过自己的有代表性的旧作,例如胡适重订《尝试集》;郭沫若屡次重编自己的新诗集,修订《女神》;曹禺改写《雷雨》;老舍删改《骆驼祥子》等等。现代作家似乎普遍不满意自己的旧作,虽然悔自己的少作也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但是现代作家修改自己的旧作却不是那么简单。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真正不满意自己当初的幼稚,要尽量将好东西留下,不满意的删去,胡适之于《尝试集》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自己在《尝试集》增订第四版的序文中有详细的说明,旧作的存废以自己的趣味和满意程度为标准。另一种是迫于时局的变化和压力,改写自己的旧作。郭沫若、曹禺和老舍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作家其实并没有不满意自己的旧作,但是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要继续作为一个作家,要继续出版自己的作品,条件便是主动的修改。这种迫于意识形态压力的改写在作家内心世界最终造成的屈辱感和挫败感是可想而知的。它表示了意识形态在这个世纪对作家写作最粗暴的干涉,也表示了作家的屈服和无可奈何。本文不打算讨论自悔少作式的改写现象,而讨论遭受强大的时局和意识形态压力下的现代改写现象。因为这并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现象,也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纪文学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它会引起我们值得深思的疑问:作家为什么那么媚俗?为什么那么无奈又那么痛苦?
新诗作家诗作的版本杂乱当首推郭沫若的诗集的版本,他一生多次重订、增删、修改自己的诗集和诗作,几令细心的读者无所适从。那些被认为代表郭沫若思想和艺术的诗作其实都曾经被他在不同的时期修改过;同样的一首诗,在这个集子出现,在下一个集子就不见了,但又在下一个集子重现。作者简直就像变戏法一样,通过重订和改写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读者只看见他一次现身的面目。可是,郭沫若也许没有想到,当读者追踪他一系列的变戏法的时候,将他多次的假面演出串连起来,就能够看见他的真实面目,看见他的媚俗,看见他的投机,也看见他的恐惧。
郭沫若新诗的集子最值得讨论的版本有1921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的《女神》初版本、1928年由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印行的《沫若诗集》、1944年由重庆明天出版社印行的《凤凰》和195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女神》。郭沫若在自己的诗集重订、改写中,并非完全没有从艺术出发的修改。可以举出的例子是1928年《沫若诗集》本对初版的《凤凰涅!酚兄卮笮薷摹3な最后部分“凤凰更生歌”中的“凤凰和鸡”由初版本中的十四节缩减为四节,应该说这种修改是基于艺术考虑的。因为初版的写法太过重复累赘,每节仅主题词“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等十六个词的不同,其余完全一样,其重复的程度真有如裹脚布一样长而不雅,但《沫若诗集》本将四个词合成一节,修正了初版太过注重节奏而带来的累赘的毛病。但是,除此以外,郭沫若对自己诗集的重订和诗作的修改就不敢恭维了。
郭沫若似乎特别重视《匪徒颂》,这首诗对当年的文坛的确造成很大的震动。他在《创造十年》中谈到这首诗,以为它是对于祖国的恋歌和对日本新闻界污蔑五四运动后中国学生的抗议。茅盾晚年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旧事:“我记得最早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1919年底发表的长诗《匪徒颂》,诗的开头有一小引,说‘匪徒有真有假,然后引用《庄子》脚箧篇盗跖之徒问盗亦有道乎一段文字,最后作出结论。”可见这首诗在那个年代的大胆妄为,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是引人注目的。可是这首诗也有不同年代隐秘的修改,颇耐人寻味。《匪徒颂》的初版本第二节是: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东南来去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1928年的《沫若诗集》本,郭沫若将这一节改写为:
发现阶级斗争的谬论,穷而无赖的马克斯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尔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西北东南来去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诗句改动很大,当然表明这时的郭沫若思想倾向左翼,罗素、哥尔栋等人已经不是社会的时髦,经过了大革命,国共的合作和分裂,在思想界、文坛,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是更响亮的名字,所以,在开列的“匪徒”名单中,罗素、哥尔栋被除名而马克思、恩格斯荣列其中。但是,1953年版的《女神》本中,“穷而无赖的马克思呀!”一句,又修改成“饿不死的马克思呀!”这一句的改动,违反了全诗正话反说的修辞风格,而作者甘冒修辞不协调的风险,内中当然有缘故。推测起来,不外是时局氛围的改变。1953年全国解放,马克思已经由革命的号召者转变为新政权的思想和理论的宗师,这时候诗句说他老人家“穷而无赖”,作者已经感到内心的不安,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二十多年前的诗句,即使照旧说“穷而无赖的马克思”,也不见得在新社会下会因此而得到什么罪名,谁都能看出这不过是反话,是修辞,但也许会被认为不礼貌。有意思的是旧作的“不慎”引起了作者的不安,非要把它改成“饿不死的马克思”不可。这一修改,不伦不类。马克思活着的时候,虽然不能说富裕,但恩格斯是开工厂的资本家,在恩格斯的支援下,马克思的生活总是在中等的水平上,说马克思“饿不死”,无论站在崇拜还是站在反对马克思的立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诚然马克思不是很饱,但他也没有饿过。马克思一生反对资本,但他也曾经从资本市场上赢过英镑。但说马克思“饿不死”,则完全不着边际。博学多闻的郭沫若犯如此低能的过失,唯一的解释是他要迎合社会的氛围,他要媚他不可抗拒的俗。1953年版的《女神》作者删去早年他自己喜爱的《夜》、《死》、《死的诱惑》三首,原因也是一样的。作者在开国建政的大变局中,深觉要迎合社会,迎合宣传的气氛,早年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旧作就觉得不合时宜了。这是郭沫若的善变,也是郭沫若的渺小。他从1921年《女神》出版得到文名开始,就不断因应社会的气氛、潮流,重订、改写自己的旧作。1944年版的诗集《凤凰》,固然没有收入《序诗》、《巨炮之教训》、《匪徒颂》等有明显左翼色彩的诗,也没有收入其实寫得不错的《上海印象》。原因当然是国共再次合作,他本人也在重庆国民政府任事,他以为他的左倾旧作会得罪政府。否则,为什么会在解放后的集子中将这些诗又收进去呢?作者显然并没有认为这些诗作在艺术上有什么不妥,只是诗作里的愤怒和抗议令政府难堪,在合作的气氛下,他宁愿让自己的面目显得温和一点。上海曾经是令他心碎和怨恨的地方,但也是令民国政府骄傲的地方。郭沫若在解放后愿意让读者知道他在《上海印象》中表达得还不错的心碎和怨恨:
游闲的尸,
淫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床,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所以,在除了1944年重庆版《凤凰》以外,这首诗都在他的诗集里。他的感受是真实的,郭沫若这样谈到他在上海上岸后的感觉:“到了上海了。这儿我虽然是再度刘郎,但等于是到了外国。那时候,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长大的毛线披肩,披在肩头像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极长的袖管,长得快要Ч膝头。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一个营养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头窜来窜去。我在‘行尸走肉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感觉。街上跑着的汽车、电车、黄包车、货车,怎么也好像是一些灵柩。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时候索性又以不同的意义流出来了。”到了抗战国共合作,郭沫若背叛了他的感觉,他不想让民国政府难堪,删去了这首旧作。因为他期待他的背叛会得到更大的收益。
综观郭沫若修订诗集、改写旧作的历史,他像一个眼观六路的机警的兔子,随时窥测环境的变化,决定逃走的方向和时间。他透过作品的改变来适应新的社会情势,其敏感和多变的程度超出了实际需要的程度,应该说意识形态的压力和他本人的投机性格共同塑造了他诗集的修订史。郭沫若对自己诗集的修订、改写基本上是投机性的修订和改写。郭沫若新诗的修订、改写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背叛他自己的历史,他通过对自己的背叛来适应时代,通过背叛来不断确立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1937年周扬发表了批评曹禺《雷雨》的文章,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肯定它是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可是,他也认为曹禺的现实主义不够彻底,比如剧本的“序幕”和“尾声”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搬到了十年以前,仿佛《雷雨》的故事不是当下现实的故事而是一个遥远而离奇的故事;周朴园和鲁大海的亲子关系削弱了这两个性格所具有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剧中的宿命论色彩使人看不到反抗的出路。周扬是当时上海左联的主要负责人,他的赞扬对曹禺当然是很重要的,意味着左翼文坛的肯定。可是曹禺有自己对戏剧艺术的看法,而且在当时的文坛作者还是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曹禺对周扬的批评意见并非非照办不可。自周扬的文章发表到解放,十余年的时间,曹禺并没有任何回应。可是,全国解放后,周扬是党在文艺界的负责人,地位不同对作家的压力也不同。他的言论也具有了霸权话语的色彩,对作家来说,不仅仅是来自批评领域的意见,而且也是关于写作的指示,他所说的一切有作者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到的逼人的力量。它的力量来自权威话语的滔滔之势,作者甚至根本不熟悉这个权威话语的实际内容,或者它和自己的美学趣味相去很远,但也要作出顺从的表示。改写旧作就是一种顺从的姿态。曹禺五十年代后期修改了他自己最喜欢也是写得最好的《雷雨》和《日出》,其中《雷雨》修改尤大。对照初版和修改版,我们发现曹禺基本上是按照当年周扬的意见改写的。他本人在晚年与田本相的谈话录里也坦率承认,解放后他对周扬的话佩服得不得了,两个剧本就是照周扬的文章改的。修改是失败的,不过,曹禺毕竟还有一点幸运,他还来得及在晚年审订自己文集的时候弃修改本而不取。这样,修改本留下来唯一的价值就是见证作家在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压力下写作的痛苦了。
一个批评家的意见十几年以后才对作家发生实际的作用,而且这作用的发生事后看来完全是多余的,这件事本身就很耐人寻味。我们今天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曹禺的修改是出于艺术圆满的考虑,也不相信曹禺对自己的得意之作缺乏艺术的自信。1936年曹禺写了《〈雷雨〉序》,谈到他对《雷雨》的喜爱,他说,“我爱着《雷雨》如欢喜在溶冰后的春天,看一个活泼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跃,或如在粼粼的野塘边偶然听得一声青蛙那样的欣悦。我会呼出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灵感,给与我若何的兴奋。”文学家用谦逊的言辞或者用谦逊的言辞包裹着傲慢来谈到自己的作品,读者就见得多了,但像曹禺那样用如此亲切的口吻谈到自己的作品是罕见的。《雷雨》不仅是曹禺第一部剧作,也是他青春的生命和激情的凝聚和见证。曹禺也写其他一些剧本,例如解放后写的奉命之作、应景之作,如《明朗的天》、《王昭君》等,他不愿意谈及,就好像这些剧本记在曹禺的名下是作者耻辱的印记一样。事情是做了,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也想通过遗忘洗清这耻辱。但是,曹禺对《雷雨》却是百谈不厌,从青年谈到老年。因为《雷雨》是曹禺生命里的一首诗,一首完美的诗。这样一部完美的作品在它得到赞誉和成功之后再由作者动手改写,在作者一定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1977年,改写过的剧本重印,曹禺写了一篇无奈夹杂着悲哀的《后记》,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这本选集,并要我写个后记。我感到为难。面对自己三十年代的这些旧作,该说些什么呢?我想,把它们拿到今天来看,必然有许多的缺陷和谬误,因为它们都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重印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安”,他没有提到五十年代修改的事。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修改后的第一版,曹禺一言未置,好像改写的事情没有发生一样。重读《雷雨》不同的版本,我们能够感受到曹禺内心的隐痛。重印产生的“不安”,写后记的“为难”,除了担心满口革命言辞的当代读者不能理解剧作复杂的意蕴之外,似乎还有修改本带来的尴尬。因为在曹禺的内心深处,修改是被强加的,是不属于他真正的内心自我的。
《雷雨》最大的修改有两处地方:删除“序幕”和“尾声”;尽量突出人物关系的阶级特征而消除血缘混乱带来的神秘性。修改符合周扬当年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它努力吻合革命的文学理论关于“现实主义”的说教。《雷雨》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它的过人之处是它的神秘,没有神秘,就没有《雷雨》。可是,《雷雨》的神秘在现实主义的理解框架下成了宿命论。神秘是人物关系的结果,而宿命是人物的主观认定。《雷雨》被革命的批评戴上了宿命论的帽子,作者的修改只好尽量抹去它诗意的一面,而突出阶级的对立。所以,两处的修改其实是有关联的。改写的总体想法就是尽量让《雷雨》可以纳入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之内。
文学剧本有两种作用,既提供演出用的底本,也可以提供阅读。曹禺当年写《雷雨》很明显照顾到两方面的需要。作为供阅读的剧本,长度不是问题;可是作为纯粹的舞台演出本,《雷雨》是长了一点,这曹禺也意识到了。他在初版的序里就把问题寄希望于日后聪明的导演解决,他不愿意承认“序幕”和“尾声”是多余的。相反,他写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解释需要“序幕”和“尾声”的用意。他说,“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来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着,念着这些在热情、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死亡,惨痛如一只钳子似的夹住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我不愿意这样嘎然而止,我要流荡在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序幕与‘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合唱队——引者注)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曹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由于“序幕”和“尾声”的现在时态,使观众的期待和故事的发生拉开了一段心理的距离;即使观众把故事看作现在时态,“序幕”和“尾声”的奇妙的背景,例如已经改作修道院的周家旧宅,巴赫的弥撒曲,修女的形象,已经发疯的周家女人等等,都有助于把悲剧诗化的气氛。初版的写法是从悲剧中升华出诗意的写法,而不是在悲剧里撒下愤怒的种子的写法。流淌在悲剧故事中的感情是哀伤和沉思,而不是愤怒和仇恨。这种有如画外音的“序幕”和“尾声”引导观众沉思:贪婪、叛逆、乱伦、粗暴犯下的罪孽需要得到超度和拯救,这种超度和拯救不是世俗的超度和拯救,而是神圣的超度和拯救。“序幕”和“尾声”对《雷雨》悲剧故事品味的纯正必不可少。可以想见,这种品味纯正的对悲剧的理解,已经不能适应解放后甚囂尘上的阶级斗争的社会氛围,当年周扬的批评在解放后已经由一种左翼批评界的意见转变成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胆小的曹禺亦要趋时才能生存。所以我们才能在文学史上看到难得一见的现象:一种不顾艺术的批评意见居然经过二十年的发酵终于成为失败的文学实践。修改本的《雷雨》删除了“序幕”和“尾声”,大大减弱了全剧的诗意,修改后《雷雨》的故事,纯粹就是一场噩梦,一场由贪婪、乱伦造成的毁灭。修改后的《雷雨》当然向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靠拢了,可是作者还是为它产生在“没有太阳的日子”而内疚,这是比《雷雨》修改的悲哀更大的悲哀,因为前者是艺术的悲哀,而后者是人的悲哀;前者是虚构的悲哀,后者是现实的悲哀。
为了迎合现实主义的理论,曹禺在修改本中还尽量改变人物之间的关系,让其中的阶级色彩更加鲜明。例如,第一幕周繁漪出场,有一处问四凤老爷见客,见的是什么人;另一处问四凤这么多天没见老爷,老爷在干什么。初版四凤的问答是:“刚才是盖房的工程师,现在不知道是谁。”“这两天老爷天天忙着跟矿上的董事们开会,到晚上才上楼见您。可是您又把门锁上了。”修改本这两处改为:“刚才是警察局长,现在不知道是谁。”“这两天老爷天天到省政府开会,到晚上才上楼看您。可是您又把门锁上了。”第四幕临末,真相大白,周萍终于知道鲁侍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初版中一段父子的对话是这样的:
周朴园(沉痛地)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周萍(半狂地)不是她!爸,您告诉我,不是她!
周朴园(严厉地)混帐!萍儿,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周萍(痛苦万分)哦,爸!
周朴园(尊重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鲁四凤(向母)哦,妈!(痛苦地)
周朴园(沉重地)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我万没有想到她今天还在,今天找到这儿。我想这只能说是天命。(向鲁妈叹了口气)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很后悔,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想萍儿是个孝顺孩子,他會好好侍奉你。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修改本这段对话改写为:
周朴园(沉痛地)萍儿,你过来。你的生母并没有死,她还在世上。
周萍(半狂地)不是她!爸,不是她!
周朴园(严厉地)混帐!不许胡说!她没有什么好身世,也是你的母亲。
周萍(痛苦万分)哦,爸!
周朴园(尊重地)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向侍萍)我预备寄给你两万块钱,现在你既然来了,——
鲁侍萍不——四凤,我们走!
周朴园(暴怒地,对周萍)跪下,认她!这是你的生母。
初版中的周朴园虽然是个资本家,但并不是个政客;对工人手段狠毒,但并没有策划于密室。修改本写他去省政府开会,会见警察局长,无非是表明他是和官僚一体的“阶级敌人”。初版的周朴园对自己当年不负责任的偷情,有相当的悔意,他向孩子当面认错,用金钱弥补被伤害的鲁妈。这些都是有人性也合乎剧情的表现。但是这样的写法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如此的一个“阶级敌人”怎么可以有人性?当年的偷情就不是偷情而是“阶级压迫”,所以修改版的给钱并不是悔意而是虚伪的打发,而这种肤浅的收买伎俩为鲁侍萍断然拒绝。还有,修改本中周朴园让周萍认生母不再是初版里的大家长的诚恳和悔意,而是不近情理的暴君的虚伪而暴怒的表演。他让周萍跪下认生母,并不是要周萍认这个女人作生母,而是要借机表现自己的权力。修改者的用意是清楚的,可是读者要问,除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要求之外,除了贴“阶级敌人”的标签的需要之外,周朴园有什么必要在这种场合伸张自己的权威?这修改让读者感觉到人物的行为和他所处的情景是完全乖离的。
如此的修改也贯穿在其他人物身上,初版第三幕写鲁大海与养父鲁贵争吵,拔出从矿上带来的枪,还说要用枪为自己和矿上流的血报仇,鲁侍萍闻见大惊,劝说鲁大海把枪交给自己。其中有一句说明天报告警察,把枪交给他。修改本把这句删去了。初版也是第三幕鲁侍萍担心四凤跟周家的人有染,重蹈自己的不幸,说了一段悔恨交加的话给四凤听:
鲁侍萍(落眼泪)凤儿,可怜的孩子,不是我不相信你,我太爱你,我生怕外人欺负了你,(沉痛地)我太不敢相信世界上的人了。傻孩子,你不懂妈的心,妈的苦多少年是说不出来的,你妈就是在年青的时候没有人来提醒,——可怜,妈就是一步走错,就步步走错了。孩子,我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的女儿不能再像她妈似的。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容易变了。孩子,你是我的,你是我唯一的宝贝,你永远疼我!你要是再骗我,那就是杀了我了,我的苦命的孩子。
修改本中的这段话是这样的:
鲁侍萍(落眼泪)可怜的孩子,不是我不相信你,(沉痛地)我是太不相信这个世道上的人了。傻孩子,你不懂,妈的苦多少年是说不出来的,你妈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人来提醒,——可怜,妈就是一步走错,就步步走错了。孩子,我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我的女儿不能再像她妈似的。 孩子,你疼我!你要是再骗我,那就是杀了我了,我的苦命的孩子。
把枪交给警察当然有“良民”的嫌疑,对于写一个身体和精神都备受摧残的底层劳动人民来说,是“政治不正确”的写法。而鲁侍萍的这段话,经过了修改,感情的基调从悔恨变成了怨恨,突出了她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消除了其中人性论的色彩。还有第三幕周冲与四凤的长段对话,表现周冲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作者也都尽量删除,以免让这些有“小资”色彩的浪漫幻想冲淡现实悲剧的气氛。初版第四幕中周朴园经过侍萍的到来,周繁漪的反抗,预感到有事情要来。不详的神秘悲剧气氛既通过角色关系传递,也通过人物感受传递出来。这本来就是非常圆熟的戏剧手法,大概曹禺被《雷雨》宿命论的批评所震慑,在修改本里有意识地回避,将神秘写成了阴谋。修改本周朴园对周萍说的一段话:
周朴园(畏缩地)不,不,有些事情简直是想不到的。世界上的事真是奇怪。今天我忽然悟到做人不容易,太不容易。(疲倦地)你肯到矿上去磨练一下,我很高兴。有一样东西,你可以带去。(领周萍到方桌前,拉开抽屉给他看)但是,只为着保护自己,不要拿它来闯祸。(把抽屉锁上)拿着钥匙!走的时候,不要忘了带着。(把抽屉的钥匙交给周萍。)
感叹做人不容易是一件世俗经验的事情,勤加历练也许就可以收放自如了,怎么就跟感叹世事莫测连在一起呢?还有,周朴园感叹做人不容易,又怎么跳跃到劝儿子拿一枝枪防身呢?曹禺似乎很欣赏剧情和角色带来的神秘气氛,但又不得不注入阶级斗争的成分,所以就有了如此的修改。就像一道汤,本来味道已经很纯正了,可是美食批评家嫌不够辣,曹禺就只好放辣椒,结果把味道调得不伦不类。初版本周朴园的话是这样的:
周朴园(畏缩地)不,不,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点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冒险,太——荒唐,(疲倦地)我累得很。(如释重负)今天大概是过去了。(自慰地)我想以后——不该,再有什么风波。(不寒而栗地)不,不该!
看了初版才知道修改本周朴园的话为什么那么自己不咬弦,前后对不上。原来初版中并没有“阶级斗争”的现实威胁,周朴园只有对天意的恐惧,对神秘的恐惧。但是,修改本把周朴园的恐惧写成对工人斗争的恐惧,也就是一个资本家末日的恐惧。
曹禺的晚年是在苦恼中度过的。自己作品的好与坏,他是一清二楚的。除了那篇写于1977年的修改本《后记》,曹禺晚年对修改本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相反对初版的《雷雨》却说了很多。他一生剧作少,好的剧作就更少,连最好的剧作都由自己动手不由衷地删改一番,这真是令人惋惜的一件事。这种自我的创伤,我们有理由相信也构成了他晚年苦恼的根源。他小心翼翼地生活,想写出好作品来,也清楚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但就是做不到,就是写不出来。他的苦恼也是那个年代作家普遍的苦恼,可是,这种苦恼不是艺术的苦恼,而是艺术家落在世俗的苦恼。他谨小慎微的形象也是那个年代艺术家的形象,透过他的渺小和失败,可以认识那个年代。
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一批当年的名作,和曹禺的剧作一样,老舍的《骆驼祥子》也在当中。重印后的《骆驼祥子》经过了老舍关键的删改。老舍在《后记》中轻描淡写地说,“现在重印,删去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看似文句技术上的修改,其实并不尽然。新本几乎没有增加字句,但删掉的却不是不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新本删节共有四处:第六章虎妞勾引到了祥子之后的一段写景约二百七十余字删掉了;第十二章交代曹先生被捕原因约七百字删掉了;第二十一章分析议论祥子经受不起夏太太诱惑的心理七百余字删掉了;删掉第二十三章最后二千余字和全部的第二十四章。老舍写东西本来就没有色情描写的内容,所以,“不洁净”云云,如果不是无可奈何的搪塞就是另有所指。至于“枝冗的叙述”,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还表示结局收得太匆忙,只是因为报章连载的关系,不得不划一整齐二十四段,其实“应该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地杀住。”本来就已经太简单了,怎么到了解放后就变得太冗长了呢?其实,对比初版本和修改本,答案是不难找到的。
重读初版本和修改本我们发现老舍的删除集中在两点内容上:第一,涉及祥子堕落自身原因的分析议论;第二,涉及对当年革命者的描写。老舍要删除第一方面的内容当然因为祥子毕竟是劳动人民,过多强调劳动者的阴暗不但违背现实主义理论,也违背新社会的时代氛围。第二方面的内容要删除是因为老舍当年用了漫画化的手法写革命者,其中不无讽刺挖苦,如果原文照登,很可能得到“大不敬”的嫌疑。
《骆驼祥子》讲述的是一个堕落的故事,不过它不是养尊处优式的腐朽的堕落,而是一个底层人为了生存而要强的堕落。老舍赋予这个故事不同凡响的意义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过分强调社会性的苦难在祥子堕落过程中的作用,而是写了性的诱惑如何把自尊、健康、要强的祥子引向了堕落的深渊。性的诱惑摧毁了他的自尊,也就摧毁了他的人格。例如,他从乡下来到城里,没有自己的车,他可以凭力气租车拉,挣下钱再买属于自己的车;被军队拉夫,他逃跑,拐来骆驼卖掉再重新开始。但他过不了虎妞这一关,性的诱惑是他命运的分界线。对人生堕落的这种见解本来是老舍独到的地方。可是,解放后,社会氛围改变了,老舍也要趋时。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把劳动人民写得如此消极和阴暗,显然是不妥的。老舍在修改本中小心翼翼地掩盖祥子堕落的关节。堕落故事的基本格局是改变不了的,于是老舍采取回避祥子堕落自身原因的方法,通过突出社会环境的压力,使故事向现实主义靠拢。第六章删去的那段写景其实写得非常好。屋内灭了灯,天上漆黑,不时有几颗流星划入夜空,带着发白的光尾,给了天上一些光热的动荡,过后天空又恢复了原样。“余光散尽,黑暗似晃动了几下,又包合起来,静静懒懒的群星又复了原位,在秋风上微笑。地上飞着些寻求情侣的秋萤,也作着星样的游戏。”写景含蓄地暗示祥子这时如同寻求情侣的秋萤,虽然他像拿猫似的把虎妞拿在手里,但是,一个他不爱的女人,正是他迈向人生地狱的门槛。
性的诱惑并不能等同于女人的引诱,既然是一本写堕落的故事,祥子自身阴暗的心理是不能不涉及的。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初版本对祥子这方面的分析议论越来越多。在帮助读者理解这个堕落故事的意义上,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修改本却越删越多。二十一章写原本是暗娼的夏太太在做出支走女仆穿性感衣服喷了香水的种种诱惑暗示以后,祥子在盘算是不是要占点便宜:
这要搁在二年前,祥子决不敢看她这么两眼。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一来是经过妇女引诱过的,没法再管束自己。二来是他已经渐渐入了“车夫”的辙:一般车夫所认为对的,他现在也看着对;自己的努力与克己既然失败,大家的行为一定是有道理的,他非做个“车夫”不可,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与众不同是行不开的。那么,拾个便宜是一般的苦人认为正当的,祥子干吗见便宜不捡着呢?——生命有种热力逼着他承认自己没出息,而在这没出息的事里藏着最大的快乐——也许上最大的苦恼,谁管它!
这段话修改本删节了,因为它伤害了祥子这个受旧社会迫害的劳动者的形象。其实,这段话对人性很有洞见,是老舍精彩之笔。二十三章后半部分和二十四章写祥子行骗、嫖赌,出卖革命者阮明得了几十块钞票,彻底变成了“人渣”。老舍这部分的删节使得本来完整的故事变得不完整,不但使一个堕落的故事没有彻底的完结,而且使这个堕落故事的意义大大削弱了。它没有写出性诱惑本身的复杂性,没有全面揭示性诱惑对人格的伤害。看来,老舍是在现实主义理论的框架面前却步了,不惜胡乱删改自己的作品迎合时代的社会气氛。
老舍喜欢用讽刺的笔调写东西,《骆驼祥子》算是比较克制的了,没有《二马》、《老张的哲学》那样幽默得有点油滑。写祥子的时候就没有用讽刺的手法,但他还是禁不住要挖苦一番,这在小说里主要见于写革命者阮明的形象。但这在三十年代不成问题,解放后可是不够恭敬。幽默的笔法带来了麻烦,推测起来,这也是老舍为什么要删掉整个二十四章的原因。小说有两个地方涉及革命者的形象,一是十二章,另外就是最后二十四章,修改本把涉及到革命者的地方都删除了。在老舍笔下,阮明是一个品行不端,以革命来讨口饭吃的人物。就像前清末年的时候有人吃洋教,现在有人吃革命。这种看法似乎是当年城市中产阶级的眼光,写在小说里本不是什么问题。那位阮明读书的时候功课就不好,得了不及格,怪罪正直的曹先生报复他,就到党部告发,害得曹先生被拘捕。后来祥子为了糊口,又出卖了以游行为职业的阮明。这一切都是在喜剧的气氛下叙述出来的,看看老舍怎样写阮明被抓去杀头的情形:
阮明是个小矮个,倒捆着手,在车上坐着,像个害病的小猴子;低着头,背后插着二尺多长的白招子。人声就像海潮般的前浪催着后浪,大家都撇着点嘴批评,都有些失望:就是这么个小猴子呀!就这么稀松没劲呀!低着头,脸煞白,就这么一声不响呀!有的人想起主意,要逗他一逗:“哥儿们,给他喊个好儿呀!”紧跟着,四面八方全喊了“好!”像给戏台上的坤伶喝彩似的,轻蔑的,恶意的,讨人嫌的,喊着。——大家越看越没劲,也越舍不得走开;万一他忽然说出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呢?万一他要向酒店索要两壶白干,一碟酱肉呢?
老舍的笔法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写阿Q。可是,阿Q毕竟是辛亥年间的事,这位阮明分明就是三十年代的人;阿Q是个乡间的人物,这位阮明读过大学,组织游行,宣传社会主义。他的死法居然有点像阿Q,真是不可思议。这样的笔法不合时宜是肯定的,而且也不能明讲出删除的原因,只好委诸“枝冗的叙述”。老舍没有正面谈过他的删改,在1954年的《后记》里有暗示性的解释。他说:“在书里,虽然我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我可是没有给他们找到出路;他们痛苦地活着,委屈地死去。这是因为我只看见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革命的光明,不认识革命的真理。当时的图书审查制度的厉害,也使我不得不小心,不敢说穷人应该造反。”人生的出路从来就不是小说能够指明的,一个作家不认识革命的真理也算不了什么过错。重要的是老舍在这里表明了一个顺从的姿态,一个愿意承认自己不够高明的姿态。他删改小说就是一个实际的行动。删改使得他的小说避免了在新时代新社会的尴尬,如果说中国的书写传统一直存在避讳的做法,从前是避皇上的名讳,现在则要避革命讳。可是,他的避讳却伤害了他的艺术。
意识形态是一种权力话语,它对作家的压力既是非字面的,也是字面的。所谓非字面是指它的势力。因为它挟持的是政治力量,不表示顺从的或者没有机会表示顺从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领教了它的力量。所谓字面的,是指它是一个陈述,一个关于世界、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究竟所以然的陈述,它提供了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模式和路径。因此,这样的模式和路径落实到文学中来自然就形成了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这个标准给出了什么虚构故事是允许的,什么虚构故事是不允许的;什么文学形象是应该如此这般的,什么文学形象是不应该如此这般的。透过这套“政治正确”的标准,意识形态控制了文学的每一个细微要素:故事、情节、人物、冲突、意象等等。作家在这套“政治正确”标准下写作。旧作所以要修改,就是因为它们违背了新时代的“政治正确”的标准,意识形态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作家改写自己的旧作,透过作家自己的手把旧作修改成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
刘再复,学者,现居香港。主要著作有《人论二十五种》、《性格组合论》等。
林岗,学者,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明清之际》、《罪与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