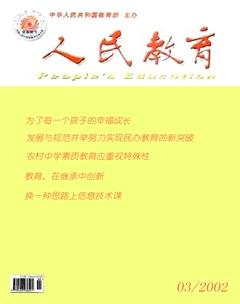与书为伴的岁月
童年时对读书的渴望
1970年,6岁的我进了村里的棋盘小学。学校只有两间教室,没院墙。教我们的只有一个老师,叫王成厚,20多岁。一块大木板,用墨涂黑了挂在墙上,就算是黑板了。课桌椅是几条长凳,一溜儿摆在那儿,学生一个挨一个。后来,学生多了,长凳不够用,王老师就从山上扛来了一些石板,用石头撑起来当桌子。40多个孩子叽叽喳喳地挤在屋里念书识字,很是热闹。
那时不学汉语拼音,学习生字全靠硬记。教生字的时候,王老师就在生字旁用小括号标上一个学过的同音字,这样字音记得快,也不易忘掉。那时的课本薄、内容少,一学期的课本3个月就学完了。接下来,王老师就找来《烈火金钢》、《金光大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给我们读,读到好的词就抄在黑板上,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怎么记,怎么用。不知不觉中,我们比邻村同年级孩子多学了不少字。上学不到一年,竟能囫囵吞枣地读一些简单文章了。
我那时最羡慕闫明,他爹在公社水利站工作,家里有好多书。有一次,闫明领我们到他家,很神气地抱出一个纸箱子。哇,里面全是书!上面一层是小画册,《烽火少年》、《鸡毛信》、《红灯记》等,大家呼啦一阵疯抢;下面一层是《公产党宣言》之类的书。我再往下翻,闫明捉住我的手不让了。一定还有好书!老坤像抱小鸡似的把闫明抱在一边,我乘机揭开一看,底下竟是一层棉花。装不满就装不满,何必拿棉花垫底儿呀?伙伴们一阵喧闹,老坤的嘴巴快咧到耳朵边儿了,手指弹着闫明的头说:你这叫满一满一半一箱一书?闫明的小脸憋得通红,反驳说:你连半本书也没有呢,神气什么?过不了多久,我让那层棉花全变成书。
闫明说得不错,没几天,他又约我们去他家,啪地把纸箱子翻扣在地上,下边的棉花真的变成了书。有好几本是以前没有的,像《养蜂技术》、《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不用说,是他爹帮他充实起来的。从此,闫明家成了伙伴们最向往的地方。每次去他家看小画书,他母亲总是准备好一大堆活儿,扒玉米皮,扒棉花,推磨,扫院子,大家都忙不迭地干完活儿,再看那些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小画册。
老坤对此愤愤不平,他发誓不看闫明的书,还招呼大家也不要去给地主打短工——这是他对去闫明家干活换书看的说法。可招呼归招呼,大家还是照去。老坤很难过,和我商量:怎么才能盖过闫明这小子呢?去书店买,光那些小画册也得20几块钱,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上哪儿去弄钱呢?老坤日思夜想。有一天下午,我俩去猪鼻子崮上放羊。羊儿满山遍野撒欢,我和他头枕破布鞋、手扳脚丫,躺在地上看天上的流云。突然间,老坤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大喊一声:有了!
老坤家养了9只羊,我家养了5只,我俩常合群放羊。我们这样合计:老坤把自己家的一只羊绑起嘴巴捆在山上,回家后谎称羊丢了一只。次日是石汪峪逢大集,我俩星夜牵羊去集上卖掉,然后买书。说干就干,虽然老坤挨了他爹一顿穷揍,但这计划却实施得出奇地顺。第二天,太阳还没爬上东山,我俩就怀揣着34块8毛钱,蹦蹦跳跳地回到了棋盘村。
那天下午,我和老坤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进了公社的图书门市部,他先让我回忆闫明有哪些书,然后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连《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也要买。我说,别要这个,咱看不懂。他双眼瞪得溜圆:看不懂慢慢看,买!我说,你裤子都露腚了,少买点书去买条裤子吧。老坤不干,34块8毛钱一分不剩地买成了书。当我们一人背一包、气喘嘘嘘地回到村子时,已是满天星斗。为了不让大人们怀疑,我们一人一包藏在家里,先看完自己的一包后,再交换看。
以后,我和老坤经常把书借给同学们看。王老师为此专门把结婚的衣柜拿到学校,设了个图书柜。没到一个月,我们的两包书都陆陆续续合拢在图书柜里了。闫明的小画书再也没人借了,尽管他反复央求,发誓再不让同学干活,也没有人去。
那时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校长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叫刘忠,头顶有块疤,大人们叫他灯泡,我们背后叫他电棒子,尊称为老电。王老师说,你除了当校长,还得兼图书管理员。老电很乐意,把书柜的钥匙挂在腰里,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地响,一下课同学们便跟在身后让他开锁拿书。课余时间,他也翻看我们的小画书,一页一页地让我们给他读。老电当校长不用出工,翻翻小画书就能挣10个工分。
上四年级时,我曾以偷羊买书之事为题材,写了3首十六字令:
书,闫明有书老坤怒,偷卖羊,买回两嘟噜;
书,免费借给伙伴读,同学们,再不找地主;
书,保管老电大老粗,老坤懒,人读他不读。
老坤看后连连点头,说写得很有味道,但再三叮嘱我不要外传。
塑料大曲与《三国演义》
初中的学校设在棋盘村南边两里路远的石汪峪村,由周围十几个村子联办,称石汪峪联中。学校前边有一个深潭,潭底和潭四围都是岩石,河水泻进潭里,激起一片雪白的浪花。当地人称这个潭为任,石汪峪村因此而得名。石汪上边50来米处的山崖上有一眼山泉,泉眼似张开的龙口,人称咙口泉。
我们的语文教师叫章松,当时不到20岁。他对学生读课外书很有偏见,多次在班里强调:任何人不得把课本以外的闲书带到学校来,否则一律没收!这可怎么办?正当我不知所措时,一次下课后,闫明约我来到了龙口泉边,他抓住泉边的一条山葡萄藤,麻利地爬上去,從葡萄秧底下摸出一本书扔给我。我接过一看,竟是我一直没借到的《苦菜花》。闫明说:我外婆家在这个村子,我小时候常来捉山雀,山葡萄下面的石洞就是那时发现的,能蹲下三四个人呢。以后咱们把课外书、饭、茶缸都藏在这里,中午就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了。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以后,班里几个爱读书的好朋友,中午放学就都来到这里,一边喝着清冽的泉水、嚼着煎饼卷大葱,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闲书,真是无比惬意。
一天中午,正当我们看得出神,章松老师突然出现在洞口,我们全吓呆了。出乎意料的是,章老师竟然没有呵斥我们,而是搂着我的肩膀说:你们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千万别再喝凉水了。以后你们的开水钱,我包了。这件事使我明白了,章老师还是很爱学生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坤告诉我,他同桌赵永庆的三舅家藏有一本《三国演义》,不过谁也借不出来。我急问赵永庆:你舅舅有什么爱好吗?赵永庆说:他爱喝酒,喝上几盅酒,杀剐全由你。我们当即商量好,想法搞到—瓶酒去碰碰运气。老坤自告奋勇地说:俺爹前天刚用瓜干换了一桶塑料大曲,我去偷一瓶来。那时酒奇缺,想喝酒要到城里去换,把酒装在塑料桶里,人们戏称为塑料大曲)我说:行,你速去速回。不到一节课功夫,老坤回来了,兴奋地说酒已弄到,放在山葡萄洞里了。
赵永庆的三舅是石汪峪大队的林管员,常年都吃住在锥子崮上。我们仨提着酒爬上锥子崮,三舅正在杏树底下编牛笼嘴。他高兴地接过外甥的酒,抿了一口,连声说道:好酒,好酒哇,亏你爹还想着我。赵永庆趁机提出了借书的要求。三舅立即摇头:你们还没书高呢,俗话说老不看西游,少不看三国。这书也是你们看的?
老坤眨眨眼,摸起扫帚去扫天井,我也赶紧着去给三舅抱荆条,赵永庆拿着酒瓶一个劲地劝三舅喝。当老头就着咸辣椒,喝下小半斤酒后,终于摇摇晃晃地拿出包了3层布的《三国演义》。赵永庆伸手去接,三舅马上缩在怀里:你们只准在这儿看,不准拿下山去。就这样,以后的日子,我们每天下午爬一趟锥子崮。用了月余时间,啃完了那本少头没尾的《三国演义》。这期间,我们几个先后想法儿为三舅孝敬了五六斤酒。
没书看的日子显得特别的漫长。暑假里,我一边為生产队放牛,一边翻看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几本书,没几天功夫就看完了。棋盘村70来户,谁家藏几本什么书我都很有数,早已看多少遍了。那天路过大队门口,老电叫住了我。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结束后,老电到大队当了门卫。老电说,爷们儿知道你打小爱看闲书闲报,咱村里订的报纸我都攒起来了,你拿去看完了再给我。我如获至宝,把老电用铁丝订起的一摞摞报纸抱回家,钻进我那间小屋,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报纸只有3种:《参考消息》、《大众日报》、《农村大众》。两年多的报纸,足有十几斤。我翻了翻,《农村大众》上面居然完整地连载了《大海作证》和《星星作证》这两部在当时引起轰动的爱情小说。这以后,我枯燥的放牛生活就多了几分乐趣。两部小说看完后,报上又连载了一篇名叫《奇怪的四脚蛇》的侦探小说,但在老电的报纸中还没有连载完。到底谁是隐藏在我党内部的四角蛇?我急于知道下文,偏偏老电有病住进了公社医院,邮递员把报纸透过门洞投进老电的房中。这可急坏了我,去找老坤想办法。老坤说这有何难?他找来几根高梁秸,上头劈了叉,然后一人站岗,一人从门洞里往外夹报纸,报纸一张张被夹了出来。读完了那几天的报纸,小说还没连载完,我又是魂牵梦绕,心神不安。以后的几天,放牛地点改在邮递员常走的路边。那时最盼望见到的人就是邮递员,那町铃铃的自行车铃声,简直成了世界上最美的音乐。一见到邮递员去了大队,我马上让老坤去夹报纸……
让山里娃也能读上书
1978年9月,我考入了泉庄中学读高中。学校离我们棋盘村有30多里山路,村里同年级的同学中,只考上了我一个。
学校图书室藏书3000多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我欣喜若狂了好几天。班主任张志宝是一位教学经验十分丰富的教师,个子不高,为人随和。第一次见面,张老师做完自我介绍后说:我教语文,咱班同学升高中的试卷我都看了,明显存在三大不足:一是汉语拼音,10分的题80%的同学是零分;二是阅读,20分的题平均竟不到5分;三是作文,30分的题平均得了10分多一点,25分以上的只有1人。从现在起,你们不仅要补学拼音,还要扩大阅读量,提高作文水平。这以后,我们这些几近成年的高中生,便尖着嗓子,瞪着眼,开始了b,p,m,f的学习。
开学的第二周,张老师就为全班学生办了图书借阅证。当时全校3个年级共有9个班,每班每周只能借一次书。我们班有58名学生,每周可借58本书。那几年,我几乎每周都能看完班里学生借的新书,多则30几本,少则10几本。恰巧,图书管理员赵老师是我们数学老师的妻子,她知道我爱读书,就特许我每周借两次书,这让我很感动。每到周末,我就去找赵老师。一边帮她修补破书,一边找没读过的好书,像《战争与和平》、《林海雪原》等都是那时看的。
毕业时,我以几分之差高考落榜了。得知落榜的那天下午,老坤、闫明等童年的伙伴杀了鸡,打了散酒来为我打气。明年再考,必定胜利,干!几只酒杯碰出了串串滚烫的热泪。几天后,一个严峻的选择摆在了我面前。也正是这次选择,成了我一生的转折点。
村小还是那所小学,教师却几经更换。当年的王成厚老师早已当了乡长,接替他的女教师出嫁到了外村。村小因缺教师已停课多日,满山遍野都是拔草放羊的孩子。村支书找我说:我知道你是个考大学的料,可眼下咱村的娃娃没人教,你就给他们当教师吧。当时,我正全身心投入复习,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父亲坚决不同意:你看周围村里这些民办老师,头发都白了,转正也没指望,家里穷得叮当响,你要干了这个,这辈子肯定打光棍儿。母亲也说:这些年省吃俭用供你念书,就指望你能跳出这穷山沟,你要是当个孩子王,俺的心不白操了?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爬起来到外面散心。月光下,一群20几岁的小伙子正在玩儿老鹰叼小鸡。老坤家吵声不断,老坤、闫明几个人正围着桌子喝酒,每人一大碗,边喝边甩扑克。昏暗的煤油灯下晃动着我同龄伙伴的影子……
这年正逢大旱,老人们商量着用沿袭多年的求雨仪式,每家派一人参加。父亲说,你已经16岁,是大人了,你去吧。我跟随着求雨的队伍缓缓前行。没有大人般的虔诚,也没有孩子般的天真。在跪下来等待长者焚香燃纸的一瞬间,我感受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悲凉。
这一切深深触动了我:我的父辈,我的兄弟,他们世世代代就是这样生活!没有文化,是赶不走贫困的。我对父亲说,娶不到媳妇我认了,这孩子王,我干!当夜,我敲响了老支书家的门。
从棋盘小学到沂蒙书屋
我站在了当年王老师站过的讲台上。小学就我一个教师,3个年级共17名学生。村支书从大队加工房扛来了一个粉碎机钢磨头,绑在院子里的柿子树上,棋盘小学的钟声又响了。
第一次给五年级的7名学生上作文课,我给他们出的作文题是《记一件事》。一个小时过去了,收上卷子一看,写百字以上的2人,写50字左右的2人,交白卷的3人,这就是即将小学毕业的学生的作文水平!怎么办?我心急如焚。
从此,我每天早起晚睡,有时一天要上8节课。半年过去,我瘦了,孩子们也瘦了。年底,全乡考试,我教的学生考了倒数第二。出了这么大的力,怎么换来这个结果?我去请教县教研室的老师,他们说,违背教学规律的硬拼,出力不讨好。我这才意识到,只凭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很难当一名称职的教师。
我又开始读书了。每个周六,我都骑自行车去县教研室借书。饿了啃几口煎饼,渴了喝几口山泉。从棋盘村到县城的路上,哪一处有山泉,我都十分清楚。直到有一天,教研室的赵宝记老师对我说,你把咱资料室里的存书全看完了,再没有了。就这样十几年来,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中等师范及大学中文古汉语的课程,阅读了上千册文学、哲学、教育理论书籍,记录了几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在棋盘小学一干就是近20年,辛勤的汗水换来了金子般的收获。我的学生先后在《中国少年报》、《当代小学生》等报刊发表作文150余篇,有40余篇在全国各类征文比赛中获奖,县教委专门编印了优秀作文集《张在军和他的山芽芽》。我本人也在教书之余,潜心写出了4本教学著作,撰写了百余篇教研文章。棋盘村,这个只有200多人的穷山窝,成了远近闻名的文明村。
20世纪80年代初,有这样一件事:乡里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派技术员到各村讲授。技术员一走,村民就把地膜收起来。他们不相信这薄薄的一层塑料能带来好收成,不把种子捂烂才怪呢。可见,农村的现代化,首先应该是农民思想的现代化,要使农民摆脱几千年延续的陈规陋习,必须更新观念,崇尚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
为从根本上实现共同致富,我开始探索农民素质教育的课题。利用晚上时间,我在村里辦了扫盲班。1992年冬天,在领导支持下,我又开始筹建忻蒙书屋。社会各界对此非常关注,纷纷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
1993年春节前后,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科技书刊云集到了乡邮电局。仓库装不下了,我和多病的父亲、老坤、闫明他们踏着积雪,往返于近50里的山路上,用手推车一趟一趟地往家运。晚上,老电帮我分拣书刊,闫明帮我登记,老坤替我写感谢信。一边写着一边嘀咕:这可比咱当年偷羊买的书多多了。
沂蒙书屋把青年们从扑克
场、棋局上吸引过来,为他们打开了一个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读书,使村民的观念有了改变,生活质量也在提高。青年农民张彬以前养猪不懂技术,猪长得慢,病死多。他从忻蒙书屋借了一套饲养丛书认真学习,现在已成为年收入过万元的养猪专业户。石汪峪村的阎方亮,高考落榜后一度心灰意冷,后来在听蒙书屋潜心研究实用养殖技术,如今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星火带头人。村民王秀臻读了高效农业》这本书后大受启发,利用塑料大棚种植珍珠番茄,年收入两万多元……
教育是明天的经济,更应成为今天的经济。作为一个农村教师,引导乡亲们读书看报、走上致富道路,我责无旁贷。
读书,教书,筹书,著书。书如同生命中的挚友一样伴随着我。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将继续与书为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