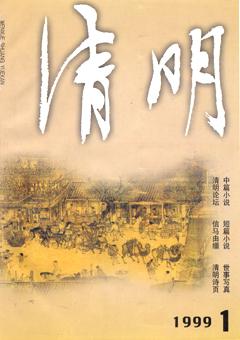重返小岗
温跃渊
1
可以说,在安徽作家中,我是写凤阳农业改革写得较多的一个。而写小岗村搞单干按手印,我却是写得最早的一个。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小岗人的红手印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居然会产生那样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按照中央一位领导同志的话说,凤阳是“两次统一了中国”:第一次是朱元璋,“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但他统一了中国;另一次,就是凤阳的“大包干”,也统一了中国。“大包干”使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奇迹,短短的几年时间,把面临崩溃边缘的中国农村挽救了过来。
而“大包干”的发源地,就是那个连年讨饭的小岗村。
今年6月6日,我再次随安徽省作家、艺术家采风团,来到小岗村。
久违了,小岗!
昔日破败的村舍已荡然无存。
村口有个牌楼,上面书写着六个行书大字:凤阳县小岗村。
一条一公里长的水泥大道通往村里,这是张家港人援建的“友谊大道”,大道两边有绿化带,有慢车道。
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古铜色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如今,他的四儿子严德友当了村支书。爷俩在新盖的村中唯一的一幢二层楼上接待我们采风团,专程从县里赶来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怀仁,当年曾数次陪同我来采访。
他介绍了小岗的变迁。
我这次带来了我17年前与江柏圣(江深)兄合写的《风雨小岗村》。我找到了我们写的主人公严宏昌和他的妻子段永霞家,他家也大变样了,提起当年讨饭的往事,段永霞眼红红的。因为采风团要到别的地方去,只和他俩聊了一小会,车队便走了。
小岗现在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了,作为当年最早来采写小岗的,我应该早些来再访她。
我第一次去小岗,是1981年的2月。
江苏的《钟山》主编刘坪,曾在滁县地区当过政委(王郁昭兼第一政委),所以他对凤阳大包干很有感情。当时江苏在连着滁县地界的地方都插着牌子,上书大字标语:坚决抵制单干风!作为一个刊物的主编,刘坪很想能在自己的刊物上有一两篇作品反映安徽的大包干,来推动一下江苏的改革开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既要有胆识,也要有胆略。
后来,我和江深兄合作采写的报告文学《风雨小岗村》,经过一番风雨,终于得以发表,但谁也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在时隔十七八年之后,我才亲手交给了小岗人。
1981年3月7日那天,在从小岗村回来的路上,我和江深兄还相约,月底我们再来小岗一次,好好地再采访一下。我们一路上议论着小岗人的故事。
谁想这一拖,竟是十七年。
2
这次到小岗,小岗已经是很热闹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20周年,也是小岗人冒死犯上搞单干的20年。
20年自是要大庆一番的。
这些年来,作为“中国农业改革第一村”,来小岗参观和采访的人很多。我们这次来后,刚好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康锐也去了。《滁州日报》的摄影记者汪强兼任着小岗村的“宣传部长”,他是采访小岗最多的一位记者。他这次是来采访美国记者对小岗的采访的,当晚即要去上海,给《人民日报》华东版发特稿。
既然上面和外面要常常来人,那就要把小岗弄得像模像样一点。
于是,交通部门来了,来替小岗修路。
城建部门来了,来给小岗统一规划,盖学校,盖招待所。
水电部门来了,来帮小岗打井,埋自来水管道,盖标准化厕所。……
28岁的新支书严德友忙得不亦乐乎。
看来,小岗村的确要有一个那怕是简易的招待所,否则严德友家也吃不消。我们和县里来帮助小岗的部门以及省里为农民服务的“三下乡”大学生,一共二十多人在德友家“搭伙”,摆两桌。德友的妻子吴风雪,俊俏而贤淑,只是身材略瘦,每天早晨5点钟就得赶车去十几里远的小溪河买菜,然后汗流浃背地做菜烧饭,实在是太辛苦了。
按我原来的设想,这回来了,就写《小岗十八家》,打算把当年按手印的18位农民一个一个地访问。谁知十几年中,18人中已“走”了4位。那就访问14家吧,可是当天下午我访问了一户农家后,我对我的计划就动摇了。
小岗人是绝顶聪明的人。
小岗人是很不简单的人。
小岗村是个不平静的村。
晚饭后,德友给我们一人一张草席,要我们和安医大“三下乡”的几位同学一块睡在会议室的水泥地上。
我们欣然接受,我和诗讳都来自工厂,我俩都能吃苦。
德友原来说给我们二老弄张床,看来有困难。可为什么又不叫我俩睡在“群众”严宏昌家呢。
诗讳说,你要把小岗村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出来,那可能成为第二部《马家军调查》,那就有轰动效应了。
我说,我可不想出这个风头。
我俩都觉得,小岗村的这篇文章,不太好做了。
3
十多家访问完了,最后我们才又去严宏昌家。每次去他家,不管他本人在不在家,他家里都围了不少人。我们一去,他们就都散了。香案上有两张照片很显眼:一张是邓小平的黑白放大照片;一张是宏昌在中南海万里的家中和万里的合影。我说,你这是哪一年和万里合的影?
说到这张合影照片,宏昌没有立即回答我,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他的思绪一下拉得很远,很远。
我没有催促他。我想起了那句流传全国的民谚:“要吃米,找万里。”
万里哪来的米呢?
1977年,“四人帮”粉碎半年之后,万里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一次,他微服私访到民间,偶遇一个农民,万里问他:“你有什么要求?”
那青年解开破棉袄外面的稻草绳,拍拍光肚皮:“‘克(吃)饱肚子!”
万里听了,热泪盈眶,良久无语。当夜,他对身边的人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却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30年,连人家这么个要求都不能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
是的,这些年,我们做了多少荒唐的事啊。近20年来,那个名曰“天堂”的人民公社,实际上使八亿农民过的是地狱一般的日子:有三分之二的生活不如五十年代初期;有三分之一甚至连三十年代都不如。他们终年劳作,但却填不饱肚皮,他们平均每年只能吃到一百零五公斤粮食和若干斤麸糠。凤阳是全国出了名的讨荒要饭地方,而小岗村自从进了“天堂”以后,也成了一个讨饭村了。解放后,农民有了土地,小岗的产量一直都在20万斤左右。上一届的县委书记吴庭美当年是县里的秘书,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小岗搞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良药》,报告开头就说:56年高级社以来,小岗地荒,人穷,集体空。生产水平十分低下,集体经济已经崩溃,社员生活极其贫困,到了57年小岗就开始发粮票供应了。1960年小岗饿死了60人,凤阳全县死了50245人。到了1966年,小
岗的产量退到2万2千斤。“天堂”把小岗的粮食穷折腾得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了,老百姓怎能不讨饭!
记得我把《凤凰展翅》送给王郁昭同志审查时,他说他把这篇关于小岗村的调查报告送给万里看后,万里对他说,写得好!我像看小说一样,一口气看完了,还连看了两遍!
1980年的1月20号,万里在地委书记王郁昭、县委书记陈庭元的陪同下,来看小岗人了。他一家一户看,家家粮满屯,户户谷满仓。他来到严宏昌的小院子里,坐在一条小板凳上,听严宏昌汇报。虽然是寒冬腊月,面对从未见过的党的大干部,宏昌心里有点紧张。
万里看出来了,笑着说:“别紧张,慢慢说。我过去也是农民。”
万里这一宽慰,宏昌的情绪才稳定下来,说:“我们小岗,从前是个讨饭村,10岁以上的,个个讨过饭。78年冬,我们偷偷摸摸地搞了包产到户,一年下来,家家户户有余粮。”
万里听了,十分高兴地说:“嘿,你们一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真了不起!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小茅屋里了!”尔后又问:“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想头呢?”不论到哪里,这位体察民情的共产党的高官,都想知道农民心里在想些什么。
宏昌说:“我们只希望能让我们这样干下去,至少能再干三五年,不要变。旱不怕,涝不怕,就怕政策有变化。”
万里说:“行,我叫县里再让你们干三五年。”
宏昌说:“只要能再干三五年,保证家家吃陈粮,烧陈草!”
万里说:“好,一言为定!我五年以后再来看你们!”
宏昌很幸运,万里在他家的小院子里坐了一个半小时。万里的那句准他们“再干三五年”的话,不径而走,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那些年,在邮局里给京城朋友寄的稀罕物品,就是一小包花生米;能在火车上偷偷捎带给上海亲戚的宝贵礼品,就是十几斤大米了。贫穷的安徽,顿时成了一个富庶的省份。人们从心里嘣出了一句话:
“要吃米,找万里!”
就在万里答应他三五年后再来看小岗这句话说了一个月之后,万里便奉命进京,接替王任重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关键时刻,邓小平把万里推到了一个关键位置,从此,八亿农民有了盼头,有了希望:
“要吃米,找万里!”
但是,从那以后,万里便没有再来过小岗。
1986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来到阔别六年的安徽,他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想到小岗去看看,但后来却未能成行。原来他在合肥突然病倒了,不得已乘飞机回了北京。
小岗人想念万里他老人家。
1994年,万里在北京托有关方面传来口信,希望见一见小岗人。当年小岗之行,给万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直接促成了,他农村改革思路的成熟。5月19日,一辆小轿车载着小岗村的省人民代表严宏昌来到了中南海,在毛泽东曾住过的丰泽园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严宏昌在《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的陪同下,代表小岗人来看望能使他们“吃陈粮、烧陈草”的万里委员长。
满头白发的万里仍然保持着平易近人的作风,热情地招呼着严宏昌:
“来,坐拢一点,我耳朵不好!”
严宏昌用他粗糙的双手握着万里的手说:
“万老,我代表小岗人民感谢您!……”
万里亲切地拍了拍严宏昌的手背,说:“请你回去代我向乡亲们问好!你们小岗现在生活还好吗?”
于是,严宏昌便据实一一回答万里的问话,琢在小岗家家都盖了新房,家家都有了电视机,只是彩电只有两家有;人均有三亩地,只是一亩地的收入才只有两百多块。
万里听到这里,沉思着说:“才两百多块,光靠种地富不起来啊。农村也要搞企业啊,要办好乡镇企业。……”
严宏昌点了点头。
最后,万里和严宏昌、张广友二人合影留念。这张彩色照片如今就摆在宏昌家的香案上,万里老人天天在小岗村。
严宏昌现在出任“小岗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他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把小岗的村办企业搞起来。他和小溪河养殖大户高明珍联营,给村上办了个饲料厂,专门供应小岗村头十家养鸭户的饲料,保证每一只鸭子可尽得一块钱的纯利。宏昌干得似乎有点吃力,他既不是村里的领导成员,也不是中共党员。他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儿有力无处使。
但是有一点给我印象很深:他既没有抱怨谁,也没有说谁的不是。他的心胸宽广,不像村里有的人家,斗争的弦还是崩得很紧的。
4
我这次给宏昌带去了一份6月12日的《南方周末》,第18版是“解密新闻专版,”上面有位叫曹俊的,写了一篇“翻案文章”:《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
我反反复复地看了这篇文章。
我不住地揣摩着、掂量着它所质疑的分量。
我不知道这位作者是哪里人。但有两处使我对它产生了质疑:
陈奎元,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学昭,当时的滁州地区地委书记,都是支持小岗的领导人,他们俩都不知道捺手印的事。
我的质疑不在于这两位书记知不知道,也不在于曹先生把滁县地区写成了“滁州地区”。而在于他竟把这两位书记的名字都弄错了。把“陈庭元”错写成“陈奎元”,只错了一个字,还情有可原;那么作者把时任滁县地委书记、后任安徽省省长的王郁昭,竟错成了“陈学昭”,我则是觉得不可思议了。这位曹先生肯定是位外乡人啦,不然何以会把咱省长的名字都会错的一塌糊涂呢。
我问宏昌:“人家那文章说,捺手印的纸那样新,也没怎么皱,按理说让社员们摸来摸去的,也不早就脏了、旧了吗?”
宏昌说:“捺了手印后,谁也没有摸过,碰过,先叫严立学保存的,后来他家要翻修房子了,这才叫我给保存的。就放在当时房梁的毛竹里头。”
我说:“当年叫你给我们看看,你怎么不给看呢?”
他说:“我谁也没给看过。它涉及我们全家性命,万一弄丢了可怎么办?再说,当时思想上也还有点顾虑。所以就什么人也不给看了。”
我说:“后来怎么又给了电影厂了呢?”
他说:“大约在198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来了两位拍电影的同志,要拍大包干的纪录片,说要拍这个手印。听说他是上海电影厂的,叫王影东,他多次向我要当年的这份合同,我不肯给。我小哥严俊昌说,宏昌你给人家拍个镜头怕什么?后来我说我要去买化肥,那姓王的摄影师说,我给你们买吧。那时化肥紧张,后来还给他真的从小溪河买着了。这不就处出感情来了吗?后来我小哥又叫我拿出来给人家,我就从屋梁竹筒里拿出来给他了。”
我还有一个迷团解不开:“那合同书上写的是12月,后来在一些书报上怎么又把那个日期写成11月24日呢?”
他说:“农村只记阴历,记不住阳历。那天开过会后,一天我到小溪河去买墨水,在人家的日历上一查对,才算出那天开会的日期该是24号。”
严宏昌于1992—1997年当选省第八届
人大代表,年年要到合肥开头十天的会。
我说:“宏昌,你年年到合肥开会,也不和我联系一下子。”话一出口,我又自我解嘲道:“这要先怪我。你看,我们写了你的稿子,不也17年了也没和你联系?”
5
凤阳有些着急。小岗村这些年变化不大,赶不上市场经济大潮,有点不大好向全国人民交待似的。
其实,小岗这些年的变化也还不小。
那个七弯八扭的泥泞小路没有了。那个矮矮的、低低的、可怜兮兮的趴在岗头上的破草屋没有了。只有严宏昌的二弟仍然留着三间破草屋,二弟叫富昌,可惜既未富强,又未昌盛。富昌过去也是一直讨饭,30岁了还是光棍一条。大包干的第一年的冬季,他和三弟盛昌就都娶上了媳妇,成了小岗村的一大新闻。富昌娶了个18岁的模样俊俏的四川女子张长淑。后来又把老岳父接过来,又把妻弟接过来,还花钱帮着妻弟娶妻成家……我们就坐在他的三间破草屋里,和几位乡亲叙着话。靠东北面的一堵土墙倒塌了,他们正在修补。我笑着说,将来盖新房了这破屋也不要拆,留着做小岗的博物馆。他憨厚的老岳父在一旁操着浓重的四川腔说,富昌是叫我们给拖累了。
虽然没有一溜新房,富昌家却也让村里统一盖了院墙、门楼,门里也新盖了两间新房,自来水管也接到家了,一条宽宽的水泥路面也由县交通部门从大街铺到草屋门口。
原来的大队会计严国品家也留着五间草屋,但只有两间是从前的,大包干后又盖了3间。重要的是,他家另盖了10间大瓦房!他有4个儿,前两个结婚,一人3间;后两个儿成家,却只有一人两间了。只是儿们都不在家了,闯世界去了。
其余各家各户,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当年的三个队干之一、会计严立学的儿子,现在当了小岗的副村长。严立学和老伴养了两千只鸭子,光这一项,尽收入两千元;他家的院子里,摆着拖拉机、收割机;堂屋里,摆着两部摩托车:一部“野马”牌,是女儿骑的;一部“雄风”牌,则是他副村长儿子的专车。
青年人骑摩托车,潇洒走一回本不稀奇。令小溪河镇上人啧啧称奇的是,过去和大伙一起爬“老黑皮”(炭车)出去讨饭的严学昌家,有两个轮的摩托车,也有三个轮的拖拉机,还有四个轮的“东风”牌大客车。学昌三个儿子,老二德根在县里的中都商城工作,老三德书开客车,老大德奎骑一部“野马”摩托,家里还有一部“钱江”牌摩托车,则是学昌自己的“坐骑”。他常骑着串串亲戚,到小溪河镇上赶集,屁股后面冒着烟,在镇上驰来驰去,甚是自得。前些年,学昌感到家里劳力多,田地少,就把老大、老三送去学开车,跑运输。一方面当然是为了致富,但另一方面,他也为乡亲们做了不少好人好事。他的车,对去梨园中学读书的附近学生一律免费;对老年人赶集、乡亲们急事用车也从不收钱。严学昌数年如一日学雷锋,做好事,被评为县里和滁州市运输系统的“十佳”人物,县汽车公司还把他“农转非”,培养他入了党。
小岗村里最早走出这片土地而致富的,是小青年关正金。他的母亲徐善珍,是我在《凤凰展翅》里写到的一位“女社员”。陈庭元当时到小岗时,发现她只带着十来岁的小儿子关正银在地里干活,便问她:队上的劳力呢?她一下吱吱唔晤答不上来,陈庭元心里便有数了:这个小岗,得寸进尺,单干了!关正金十多年前就到了小溪河镇上做屠宰生意,还在镇上盖了楼房。他告诉我,光他这些年上缴给国家的税收,就有20多万!
今年五月的一家报纸说,凤阳县委书记吴庭美,是小岗村出来的第一位大学生。按现在小岗村的“建制”来说,这话也对。但当年小岗十八户按红手印的人家,并没有一户姓吴的。吴庭美的家,在小岗东边百多米的大严村,和现在的小岗也连成一片了。小岗村出了名以后,就把大严村也划过来,统称小岗村了。真正从小岗十八家里诞生的一个大学生,是关友江的小儿子关正标,现在正在合肥工大的财经学院读书。关友江从房里拿出了一个红本本给我看,原来是这孩子在学院里学习党的十五大演讲比赛的得奖证书!
我觉着,这些都挺好的。
不一定就非要小岗村也成为第二个大邱庄、华西村。当然,她若依靠自身的力量能够走向富裕,走向富足,那也是我们共同的祝愿。
小岗村就是小岗村。他们在20年前所写下的以自己的生死为赌注的那张单干的契约,实际上是在打破一种桎梏生产力的旧体制,是射向人民公社的一篇檄文,使在中国维持20年的名曰“天堂”的人民公社一朝瓦解!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张普通的契约合同会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流浪。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去乞讨。
他们只是为了不再被饿死。
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制,创造了农村承包责任制,从而一举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这里起步!
今天,我们说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开路先锋,毫不为过。
说他们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十八根擎天柱,也不为过。
小岗人对往日的辉煌有一颗平常心,这就好。
小岗村在支书严德友的带领下,已经于去年11月间和富庶的张家港长江村结成“东西联动、振兴经济友好村”。小岗向长江村每年供应10万公斤大米,长江村将努力带动小岗经济启动。小岗村由于没有村办企业,人均收入才只有2500元;而长江村则拥有4个亿的资产,人均收入9000元。今年3月,长江村还出资66.8万元,援助小岗村修建一条宽18米、长1公里的友谊大道,栽花木1.3万株,一下子把小岗村打扮得好漂亮。长江村还安置了小岗村25个农民在那里做工,双方还洽谈了一些联合开发项目。
小岗人知道怎么过好日子,他们会一天天更加好起来的。
带着这样的祝愿,我离开了小岗。
骄阳似火。上车时,只有严德友和严宏昌站在车的两边送行。
我心里一动:村里要是这两位领导人,又会如何呢?我只是觉得,严宏昌是不该被排斥在村领导之外的。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已。
我只是从感情上,觉得宏昌好像应该是个村干才是,而且应该早就“在党”了。
6
1998年的七、八月间,中国的长江、黑龙江流域发生震惊世界的洪水。中国人民在江泽民总书记的亲自指挥和率领下,万众一心,决战决胜,终于夺取了这场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
9月,洪水刚刚退去,江总书记又风尘扑扑地来到了江淮大地。
22号上午,县委李书记来到了严宏昌家,对他妻子段永霞说:“段永霞呀,今个中央领导要到你家做客,你可得炒点花生呀。”
段永霞一听,又高兴又紧张,说:“李书记,你可得跟我说个谱,不然到时候来不及可就糟了。”
李书记宽慰她,不要紧,下午来。
1998年9月22日下午3时30分,一辆
面包车徐徐驶进了小岗村。
小岗村以又一个丰收年,迎接着总书记的到来。小岗村的粮食产量由20年前的不足1.5万公斤增至60万公斤,人均年收入由22元增至2500元。金色的阳光把沉甸甸的稻谷、玉米抹上一层金黄,接收电视信号的抛物面天线在高空中闪闪发光,村民们个个面带笑容,喜气洋洋。
总书记在省委书记回良玉、副书记王太华、方兆祥的陪同下,来到了小岗村的村史展橱前,问:“这就是你们那份字据吗?”接着,他一字一句地念了出来: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剁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严宏昌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富、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总书记念了一遍后连声称赞:“好,好,可贵精神,难得勇气。”
随后,总书记一行又来到了严宏昌家。一进院门,严宏昌和段永霞一人一边挽着江泽民的胳膊,把总书记请进了家门。总书记把严宏昌的6间房子都看了看,看了他和万里在一起的合影,询问了他家的生活,还叮嘱严宏昌的儿子严德锦“好好读书,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奋斗。”
总书记接着又到了宏昌家的院子里,和当年在字据上签字的十几位小岗人围坐在一起,回顾小岗村不平凡的过去,展望中国农村更加美好的未来。段永霞把她炒好的香喷喷的花生端到总书记面前,请他品尝。
总书记说,“我过去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一直想来看看乡亲们。”省委书记回良玉说:“总书记来安徽视察的第一站就是小岗;看望的第一户人家就是小岗人。”大家听了,又一次热烈鼓掌!
最后,回良玉提议,请总书记同当年参与发起大包干的农民们合个影。江泽民欣然答应,并诙谐地说:“好啊,不胜荣幸。”
当年的十八个红手印,已经“走”了四位,还剩下14人。合影时,摄影师一点数,只有13个人,还有一个严美昌,上小溪河赶集去了,没能赶回来。
随着快门的一声按动,一幅非同寻常的画面在这里定格,深深地烙印在小岗人的心中,永远,永远!……
7
我和诗讳又三次结伴到了小岗。
我们直接到了宏昌家里,他不在。他带着儿子严德锦到小溪河医院去忙征兵体检去了。就这样,他家里依然围了不少人。
他们在谈论选举的事。
哦,小岗村要进行第四届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要选村长了。
听说贴在严宏昌家西山墙上的选民榜,不知叫什么人给涂上了一大块黑墨水。在严宏昌家里,我碰到了严俊昌的二弟严美昌。
我笑着和他开玩笑,“美昌,和江总书记照像,你怎么溜号了呢?”
美昌蹲在墙拐拐,搔了搔头皮:“嘿,不能提了!那天,我到小溪河银行去‘起钱,谁知道总书记会到咱小岗来呢?不能提,不能提!越想越后悔!”
在村口,我到俊昌、富昌家里看了看,他们家新近都装了电话。县里电信部门给十八个按红手印的仍然健在的14户免费装了电话。已经过世的4户人的后代提出也要装,对他们四家象征性地收了点初装费,也给装了。
尔后,我和诗讳去了原来的支书严德友家。
他爱人吴风雪问我:“老温,我家德友调走了?”
“我听说了,”我宽慰她:“不是升了吗。”
“你说,像我家德友的调动,江总书记可知道?”
“这我搞不清,”我愣了一下:“江总书记恐怕不会管这许多。”
吴风雪说:“县里、市里要调我家德友走,德友不走。问:我可是犯了错误了?上面说:你没有错误。……”
走出德友家,我的心里很沉。
我隐隐地感到了小岗村的矛盾依然是很深的。
车过小溪河镇时,我们到镇医院里看了看严宏昌。问问他儿子德锦的体检情况,他说基本正常。
嗣后,我一直关注小岗村的这场选举。
11月18日,预选。要选出两名村委会主任的后选人。
19日,诗讳得到信息,打电话告诉我,说是严宏昌选上了,220个选民,他比另一位候选人多了51票,肯定没问题了。不过,26日才算正式选举。
这两场预选和直选,《安徽日报》的摄影记者冯骏都及时做了报导。11月22日和27日的头版都在显要位置发了消息和4幅照片。冯骏告诉我,直选前,不赞成严宏昌的人,把小岗村在张家港做工的30多人派代表回来参加了选举,这样,严宏昌的支持票锐减。
11月26日上午10时许,小岗村具有选举资格的259名村民,聚到新落成的希望小学里,进行了紧张的长达近4个小时的选举,严宏昌以137票的微弱多数,当选为小岗村的第四届村委会主任,也就是村长吧。小溪河镇镇政府当场给他颁发了当选证书。
当晚,我给严宏昌打了电话。问了他们的选举情况,问了他的儿子参军情况。
他说,当选也当选了;儿子参军也征上了。
我说,你这是双喜临门,我祝贺你。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并不轻松。
以一支铮铮钢笔,20年前亲手写下了大包干“生死契约”的严宏昌,在经历了20年零2天后,才被选为小岗村的村长,这个时间也是太迟了点。
就是这样,也还有那么多的人反对。
宏昌,你将怎样善待这些不赞成你当村长的村民?
宏昌,你会怎样团结好这些不支持你的父老乡亲?
宏昌,宏昌,相信你能带领小岗人一展你的宏图,但愿,但愿……
责任编辑红杏
——以安徽部分地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