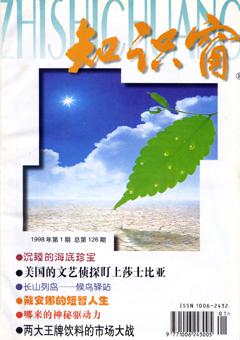文学名家三人戒烟记
蒋诗波
酒与诗歌一直关系密切。酒后不能驾车,却是写诗的最佳时机。杜甫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很显然,他把诗与酒的关系进行了极富夸张性的量化分析。与此相关,烟与文章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在许多人心目中,烟似乎可以诱发、刺激出能构成文章的无形原素。那些挑灯熬夜的文士作家,早晨清点好一页一页的文稿后,还得清理书案旁边堆得像座小山似的烟灰缸。文人队伍里的嗜烟者往往私下里佩服这样一种人:他们既写得出一手锦绣文章,又能不口吐烟雾。因而,文人作家的戒烟注定是一桩非同寻常的大事情。这一点在许多年前的三位赫赫有名的作家那里得到了某些具体的印证。
这三人指的是吴组缃、林语堂、梁实秋,他们的戒烟行动发生在四十年代。毕竟他们都是注重独特性的作家,三人戒烟的缘由、过程、结局都不尽相同。
1
吴组缃的戒烟念头缘于当时物价飞涨、家庭经济拮据。一日三餐,孩子们端起饭碗向桌上一瞪眼就撅起了小嘴巴,因为他们发现没有肉吃。吴组缃感觉到孩子们乌溜溜的眼睛分明是在抱怨自己:“爸爸每天一包烟,一包烟就是一斤肉!”他决计要戒烟,但是屡戒屡败。他的体会是:十天半个月不吸烟倒也容易,可是易戒难守,若想从此戒绝,便比旧时代妇女守节还难。于是别出蹊径,改吸劣等烟卷。吸一口喉咙便辣得不停地咳呛,脸色发红,鼻子冒火,每天被折磨得心烦气躁,无缘无故发脾气。
一天,妻子上街回来,送给他一把整洁美观的烟袋,一包上等的水烟丝。吴先生当初在乡下吸过并且导致上瘾的正是这水烟。在劣等卷烟折磨下,重睹旧物,吴先生既感慨又欣慰。可是,很快他就遇到了种种不便。原来,吸水烟是旧式的富足闲逸生活的象征。整套烟具的料理极其讲究、烦琐。假若一位老者手托一把整洁的烟袋,便说明他婢仆不懈惰,儿女媳妇勤快、孝顺,他是个有福气有家教的人。当他擎着烟袋,架着腿安祥自若地坐着,慢条斯里地装着烟丝,从容舒缓地吸个一口半口,这就把他的闲逸之乐发挥到了极处。而吴先生的日常生活与吸水烟的情调已不甚合拍,他到教室上课、外出散步、伏案写作、读书看报,都不便托着个水烟袋。而且,他家没有婢妾,妻子儿女都各忙自己的事情,他必须自己洗刷料理烟具。原本是为了享受,却变成了苦役。想到这些,他便丢开了水烟袋,又抽起烟卷,并且不要劣等的。吴组缃的戒烟从起点出发,兜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先的出发点。
2
林语堂形容自己的戒烟举动是“一时糊涂”“步入歧途”,是莫名其妙地戒起烟来的。因而,他非但无法进一步解释自己戒烟举动的理由,还由此推导出一个奇异的结论:人有时故意要做做不该做的事,故意要降大任于自己,饿其体肤,苦其筋骨,预备做大丈夫。林语堂是个具有名士风度的人,事事都追求凡人世俗的相对一面,对自己戒烟的动机说明便是如此。但是,这些并不重要,我们关注的是他的戒烟过程。
起戒的头三天里,林先生体会到从喉咙口到气管上部都有一种似痒非痒的难堪感觉,他便一个劲地吃薄荷糖,喝铁观音,含法国的补喉糖片,这种难耐的感觉也就渐渐消除了。这是他戒烟的第一个阶段。在林语堂看来,吸烟分为两类:一类人吸烟只是生理上的需要,仅仅是肢体的一种机械举动,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可以刷可以洗,也可以不刷和不洗。也就是说,他们想不吸就可以不吸,其戒烟行动经过第一个阶段的努力便告结束。另一类人吸烟还有心灵上的需求,比如欣赏辛弃疾的词、王维的诗、贝多芬的音乐,神游其间,兴会淋漓。在这种心境中,伸手拿起一枝烟是最合理的举动,要是把一块牛皮糖塞入口中便觉俗不可耐。林先生自己正属于后一类,因而他的戒烟除了生理的搏斗之外,还得进入灵魂的战斗。
进了第二阶段以后,林语堂的戒烟不但显得不怎么理直气壮,而且简直有些煞风景。有位三年不见的朋友从北京到上海来与他会面,两人原先在北京过从甚密,尤其是晚上时常会聚在一起一边吸烟,一边谈论着文学、哲学、现代美术等种种问题。这回两人围在炉旁叙旧,谈到高兴处,林先生总想伸手取出烟来抽,但都是站起来又坐下,或者简单地换换坐姿。因为他预先已把自己戒烟的事告诉了朋友,不好意思当场破戒。因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一口接一口地吞云吐雾。没有了烟的助兴,林语堂内心一直怅然若失,很难配合朋友的高谈阔沦,以致于这位朋友几天后来信说他的谈吐大不如前了,也没有先前的兴致与爽快,而且还想当然地以为是上海的空气太恶浊造成的。
又有一天,林语堂参加文人间每星期例行的沙龙。聚餐之后,由某先生宣读题为《宗教与革命》的论文,以作为讨论的引子。这种讨论通常总是一种吸烟大会,在豪谈闲聊之间,室内的人一齐吸烟,烟雾一层迭一层不断增浓加厚。林语堂觉得这正是暗香浮动奇想泉涌的关口,可独有他一人没有吸烟,这时戒烟越看越没意思了。于是在此后的一个下午,林先生去拜访一位洋女士,只见她坐在桌旁,一手吸烟,一手靠在膝上,身体微微向外倾,姿态十分优雅。当她拿起烟盒让烟时,林语堂便缓慢而又镇静地拿出了一枝。很自然,他历经三星期的戒烟行动便以失败告终了。
3
梁实秋似乎注定了是要学会吸烟的,他出身于吸烟世家。祖父抽旱烟,像当时不少人一样,用的是翡翠的烟嘴,白铜的烟袋,烟杆一尺多长,与别人三四尺的标准相比,还是算短的。祖母抽的是水烟,父亲主要以雪茄为主,但随时要补充纸烟。他有个习惯,每当打开纸烟的铁罐,就在里面的纸笺上写好启用的日期,以备测算每日的平均消耗量。
梁实秋自己吸烟始于二十年代赴美留学时期。当初他并不太乐意出国,觉得在清华大学有读不完的书,住不厌的环境,国内还有舍不得离开的亲朋好友。为此,他还与大他两岁的闻一多商议说:“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对于我们有无必要?会不会到那里被汽车撞死贻笑天下人?”真的抵达美国,梁实秋并没有感受到汽车的威胁,倒是流寓异城,独在他乡为异客,整天神思不宁,心绪如麻。看见别人吞云吐雾,便就跟着学会了吸烟。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吸烟的水平进展神速,由一日一包而一日两包,直至一日一听。后来的某一天,梁实秋心血来潮,想试验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克制能力,并且毫不含糊地选择从戒烟开始。于是,他既没有挑拣黄道吉日,也没有与家人商量,便闷声不响地把剩余的纸烟丢进了垃圾堆,留下烟嘴、烟斗、打火机送人。一开始,这种被称作“冷火鸡”的戒烟方式使他手足无措,六神无主。他就以繁忙的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实在熬不住就吃一块巧克力。一盒巧克力还未吃完,就感到腻味了。于是,戒烟连带把巧克力也戒掉了。梁实秋是英美文学的研究专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时常被人称道。很自然,他很熟悉马克·吐温如下的一句名言:“戒烟是很容易的事,我一年戒过好几十次了。”因而,他也跟着幽默地说:“说来惭愧,我戒烟只此一遭,以后一再没有再戒过。”
现今的作家文人也有不少立志戒烟的,而且梁实秋他们的戒烟故事说不定还会原封不动地发生在其中的某些人身上。当然,变化肯定是有的。根据最近公布在报上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人戒烟是为了避免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这与梁实秋三人的戒烟动机完全不同,时代毕竟已经相隔了五六十年。
(责任编辑/陈信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