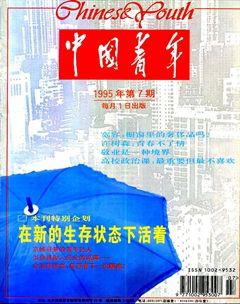橙红色的太阳
梁粱
卢晓月,女,1970年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同年分配到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从事聋儿教育工作至今。
殷会利,男,32岁,北京市“五四奖章”获得者。现为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讲师。
卢晓月
我喜欢孩子,喜欢和孩子在一起。孩子们清澈的目光和真纯的语言能让人的心灵瞬间得到净化而变得美好。所以,考入北师大算是遂了我的心愿。读书时我就常会想像着某一天我成为一名幼儿教师、和一群天使般的孩子在一起的情景。这么想着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分配到聋儿康复中心倒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无法想像,当我面对一群耳不能听、口不能言的孩子,我怎样才能与他们交流,又该怎样去教育他们。
但我还是上任去了,虽然心里忐忑着。当我走进教室,看到那些因为耳聋而比正常孩子显得木讷、神情僵硬的学生时,我的心里涌起一丝叹息,一份感慨。他们本来也应该和别的孩子一样快乐、活泼、无忧无虑的呀!我曾经看过一份材料,是1987年所作的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当时有0~14岁聋儿171万,每年还在以2~4万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聋儿群体1如果我们能不失时机地发挥他们的残余听力,对他们进行听力和语言训练,使他们得到有效的听力补偿,那么,他们必将可以得到最终的康复,从而回归主流社会,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来。这该是一项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啊!那一刻,我感到一股神圣的责任感在我心里慢慢滋长、升华。
与教正常孩子相比,教育聋儿要困难得多。光“点名答到”这一关就花了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也有忍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可一想到他们生理上的暂时缺陷,再大的气也消了。最后,终于可以不让他们看我的口形就能通过“点名”关了。不让看口形,是怕孩子们据此猜测我在点谁的名,更是为了诱导和发挥他们剩余的最后那点听力。这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是大有益处的。
聋儿因为缺少了一个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较之正常孩子会显得更为执拗。我班上有个叫张大伟的,性格就怪怪的,好像总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中。每次我走近他,他的眼神里都有一股明确无误的排斥和敌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急于逃避我,不留任何余地地拒绝我的接近。后来我了解到他的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家中常年只有一个老人。我理解了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和特殊的情感需求。于是,在课堂上我对他的行为总是表现出最真切的关注,并毫不气馁地一次次走近他,用各种方式与他交流。渐渐地,他眼神里那股强烈的拒绝意味淡化了;他最终接纳了我。而此后他表现出的想与我交流、与我友好的真诚和热切,令我感动。他母亲回北京见到我时,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哭。
现在,张大伟已调入正常幼儿园上学。每次想到他,我都在心里深深地为他祝福,为他明天的美好祝福。
首先必须付出,然后才能赢得一个聋儿的心。这是我两年多工作的体会和总结。吴桐,一个来自江西的4岁聋儿。他父亲在北京找了个工作,因远离康复中心无法接送。我承担起了吴桐的一切。白天上完课,我就将他带回家,吃、睡都在一起。那段时间,我是在紧张和极度的疲惫中度过的。妈妈看我实在累得不行,便常常帮着我照看吴桐。以前,由于父母的迁就,吴桐固执而任性,同他讲道理是件很困难的事。我带他一个月,他变得懂事多了。而且,他已将我视作最亲近的人,每天都须臾不离地跟着我。甚至,见了他父亲,也远没有对我亲热……
我想说说那些孩子的父母。他们都是些最了不起、最具爱心的父母。他们中有很多是从偏远省份千里迢迢赶来北京,将孩子送到康复中心。他们都曾拥有很好的工作,但为了孩子,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北京,他们找临时工做,租住最简陋的民房,冬天没有暖气,夏天蚊叮虫咬……我常想,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如果不用心教好他们的孩子,在他们面前,我们都将罪无可恕!
所以,虽然我每月的工资、奖金加起来也超不过400元,干的是最操心劳神的工作;别人下班了,自己还得经常留下来给个别孩子加小灶——但我还是要说,我喜欢我的工作,发自内心地喜欢我教的这些孩子。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
是的。我今天用爱心浇灌的这些小苗苗,总有一天会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的。我坚信这一点。
殷会利
1983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装潢系。在那之前,我在家乡鹤岗岭北矿区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师。我曾经打着格子为人家画巨幅毛主席像,还常常爬上脚手架,画各种会议的宣传和招贴。时间长了,就有人“慕名”邀我去作画。当时的那种自得和兴奋,是难与外人道的。毕竟,对于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来说,能拥有社会的承认和瞩目,便足可令他傲视阔步、睥睨同类了。当然,今天想来,是不免要惶然的。
但如果我就那样安于现状,陶醉于那份微不足道的成就感,或许直到今天我还只是边陲小城里一个技术娴熟的画匠,艺术上永远也走不出沾沾自喜、墨守成规的窠臼。我的机缘来自那次心血来潮般的冲动:想去北京,去看看故宫、琉璃厂,看看中国美术馆里每天都有的中国最高层次的画展——那是无数画界新人都急欲一瞻其风采的艺术圣殿啊!
于是,我参加了高考,并如愿以偿。登上赴京的列车时,我满怀着朝圣者的心情。
在北京,除了经常性地光顾美术馆之外,我成了班上最用功的学生。外出随吴冠中教授写生,大师常常把最高分奖给我。似乎顺理成章地,我成了班上唯一在院内举办个人画展的学生。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教育出版社美编室,先后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1990年底,我离开出版社,到民族学院任教。我教过素描、色彩、风景、工业设计等专业课,还兼任班主任。因为工作勤奋、努力,我曾被学校评为优秀青年教师。但使我的名字走向社会、为人们所熟知,却是由于一方方小小的邮票。
1988年,中国邮票总公司就《麋鹿》邮票的发行公开向社会征稿。我参加了,却名落孙山。现在想来,那完全是由于我对邮票认识上的浅陋和偏颇所致。我觉得邮票设计纯粹是一门雕虫小技,难登大雅之堂的。后来,再比较自己的设计稿与中选的作品,我立刻为其间的差异所震动。我终于意识到,要画好一枚邮票,就必须调动我平生所掌握的所有绘画技巧。或许,仅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开始将邮票作为一门真正的艺术去对待,开始从设计思想、构图、色彩等不同角度去研读、揣摩。1990年,我设计的《野羊》一举中的。1992年,《鹳》《昆虫》《奥运系列》三套邮票也顺利发行。这一年,全国共发行18套邮票,而我一人独占三套。我为此也付出了许多。仅为《奥运系列》一套,我不仅费尽心机,还差点跑细了腿。我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去体育学院观看运动员训练,希望可以发现我应在画稿中展现出的精彩瞬间。我姐姐殷秀梅是位歌唱演员,和许多运动员都有联系,她书房里有不少体育画报,我也统统抱了回去,当然有用。《奥运系列》里那枚体操票的设计,就是从体操王子李宁送给我姐姐的一本画册里获得的灵感。那段时间,北京正在搞“卓别林电影周”。我平素最喜卓别林的片子,特意让人搞了一套。但直到电影周结束,那套票还完整地揣在我口袋里……
1993年,我接受了《野骆驼》的设计任务。在大学读书时,我曾利用暑假去过一趟陕北。在榆林地区,我第一次看‘到了沙漠,那茫茫大漠,绵延起伏,一望无际,予人无限遐思。但激动过后,我忽然觉得眼前还缺少点什么。后来才发现,这种感觉是因为没有看见骆驼,哪怕是远远的,沙漠与天际交接处有几点骆驼的影子也好。在我的印象里,沙漠总是和骆驼连在一起的。现在,当我着手设计《野骆驼》的形式和总体风格时,我的直觉引导我向有关沙漠的范畴去思考,如沙漠的色彩、沙漠流动的节奏感和沙漠作为背景与主体野骆驼的关系。《野骆驼》的构思可以说自始至终都是围绕这一基点来发展和完善的……在这一年举办的最佳邮票评选中,《野骆驼》获专家奖。在中国,我是迄今为止第二个获得此项殊荣的邮票设计者。
常有习画多年尚未成功的朋友向我诉说他们的烦恼,并问我在邮票设计上何以会如此一帆风顺。我举了一个例子给他们听。我曾画过一套2枚《张闻天》纪念邮票,从时间、空间上看,我都与张闻天相距甚远,仅凭几张存留下来的照片,最多也就凑合个形似。我没有对着照片贸然下笔,而是翻阅了大量史料;张闻天夫人写的回忆录我至少看了5遍。每读一遍我都会深深地感动一次。渐渐地,我明了了他的经历,走进了他的思想。拿起笔来,他的形容、情态历历如在眼前。在2枚小小的邮票里深刻地反映出张闻天同志革命、战斗的一生,在我便不再成为难事……常说“功夫在诗外”,对于作画,也是一样的道理。希望我的这点小小的感受对朋友们能够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