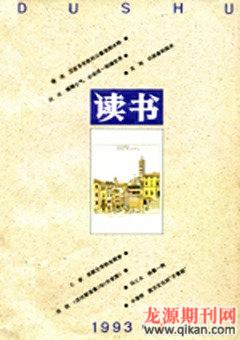西方文化的“不育症”
申慧辉
二战前后的几十年,诺贝尔文学奖曾对美国作家宠爱有加。刘易斯、赛珍珠、奥尼尔、斯坦贝克、海明威、福克纳、辛格、贝娄,以及入了美国籍的俄国诗人布洛茨基等人,均成为此间的幸运儿。近几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倾向性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一九八八年,埃及小说家马哈福兹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人,引起一阵喧哗。一九八九年,西班牙作家塞拉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紧接着,一九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授予另一位西班牙语诗人、墨西哥作家帕斯,再度引起舆论界的哗然,如果说马哈福兹获奖是因为他“开创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的叙述艺术”(瑞典学院颁奖评语),那么,塞拉和帕斯的获奖则是对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主调的当代西班牙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而表示的承认。此后,新的浪潮又从另一方向卷来。一九九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南非反种族主义的著名女作家纳丁·戈迪默,以表彰她“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并“因其壮丽如史诗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的成就。然后便是去年年底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是一九七九年方获独立的岛国圣卢西亚的黑人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瑞典学院对沃尔科特的评语更带有象征意义,直称其诗作“是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
从一九八八年到现在,已经是整整五年了。在这期间,诺贝尔文学奖将传统的文学大国的作家统统排斥在外,独独褒奖那些所谓的边缘作家(西班牙的塞拉有些例外),不能不说是一种颇引人注意的新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实际上显露了一种对世界文坛乃至整个世界新格局的认同,因而具有文化的甚至政治的意义。
七十年代末以来,国外学术界开始流行后殖民主义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门理论现已成为一批知识分子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武器。其代表人物萨伊德,就是一位来自巴勒斯坦国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尤其在人文科学领域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理论的运用者们证明了,在西方国家里,一个文化是如何按照其模式生产出有关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些“一厢情愿”的知识去实行文化霸权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创始者们也许十分欣慰,因为在其理论兴起之后的十几年间,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相互不甚关联的事实从不同侧面证明,二十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和下一个世纪,世界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要角色将是一批新人。例如,政治上,苏联的解体打破了以往两霸对峙的冷战局面;经济上,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复兴意识和亚洲崛起的势头,已经在重新绘制世界经济的大地图。文化上,欧美作家已不再可能继续统治文坛。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的成熟宣布了世界文坛的主角已经易人。
以这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为例,传统的主流文学之外的作家连连榜上有名,已经说明世界文坛新动向的实际含意与指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了注释。首先,这些作家都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突出的文学个性。他们不仅在题材的选择和语言的运用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而且在主题的倾向性和情节的切入点上,也有着明显的新特色。马哈福兹、塞拉和帕斯,及至戈迪默,都善于将世界文坛的新思潮、新技法创造性地运用到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学创作中去。马哈福兹对阿拉伯民间故事、传奇和游记等文学形式作出了创造性的发展。塞拉的实验性创作使其成为西班牙战后“文学之车”的启动者。帕斯得以运用其现代的多元文化意识,用代表着自然与人类历史的“太阳石”去表述现代人的生活真谛与现实困惑。对于充满责任感的戈迪默来说,文学创作则不仅仅是艺术地反映现实,更是直接介入现实,对现实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当戈迪默获奖时,迎接她的不仅有文学界同仁的祝贺,还有着南非黑人的欢呼。整个世界文坛,整个世界的各民族人民,则通过这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及其创作,聆听到了地球上另一些人群的心声,体会到了发展中国家所潜在的巨大活力,以及世界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其次,上述作家的创作活动及其在世界文坛上日益重要的地位,都明确地证实:“后殖民地文学”已经成熟。近几年不敢公开露面的拉什迪,曾写下充满激进色彩的语言和富有创意的形象的优秀作品,并因此而成为后殖民地文学的开拓者与教父。他的名著《午夜的孩子》,被欧美书评界称为“后殖民地文学独立的呼声”。这一评价不仅是指《午夜的孩子》以印度独立日前夜作为小说富有寓意的开头,更为本质的是,拉什迪通过对印度社会细致入微的描写,带给世界文坛崭新的文学语言,独到的作品结构和新鲜的意象比喻,有力地震撼了封闭的、了无生气的传统主流文学体系。从此,已经悄然发展了数年的后殖民地文学脱颖而出,走上前台,正式加入世界主流文学,形成与传统主流文学并存、且日益显示出压倒优势的文坛新局面。
拉什迪的巨大成功令世人瞩目,他的戏剧性灾难又象征性地暗示了后殖民地文学发展之艰难。自从霍梅尼宣布了对拉什迪的判决,不仅拉什迪本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就连翻译其作品的译者也连遭暗算。后殖民地文学本身似乎也有类似的遭遇。作品被误读、误解乃至被禁的现象均有发生。这些作家的成功,往往凝聚着更多的辛劳甚至血泪,他们的作品也因此而更凝重、更深刻,更贴近时代的脉搏。
后殖民地文学的又一典型代表,就是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沃尔科特。沃尔科特是典型的多元文化的产物。他生长在位于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中的圣卢西亚。他的血管里流着英国、非洲和荷兰祖先的血液。这位血统复杂且又生活在多种文化交叉的岛国里的黑人诗人,从开始创作起,就深切地感受到“分裂”之痛。他不仅要为自己的肤色“不够黑”,不足以使黑人同胞们“骄傲”而受到感情上的伤害(见《飞翔号纵帆船》一诗),更要面对白人把持的主流文学的殿堂,承受“批评界不愿承认这位伟大的英语诗人是一个黑人”(布洛茨基语)的巨大压力。他不能不面对这一现实而发生慨叹:“可我如何/在这个非洲与我所爱的英语之间作出选择?/出卖两者,还是奉还它们给予的?/面对这样的屠杀我怎能冷静?/背弃非洲我又怎能生活?”(诗中的“屠杀”系指肯尼亚吉库尤族人举行“茅茅”起义时的遭遇)独特的体验化作传神的比喻,赋予沃尔科特的诗作一种特殊的魅力,并终于将诗人推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使这位黑人诗人最终受到世界的公认。
沃尔科特的诗作技巧娴熟,语言鲜活,标志了后殖民地文学的成熟。更有代表性并具阐释功能的,还要算他于去年十二月七日获奖时发表的演说。且不说演说题目《安的列斯群岛:史诗记忆的片断》已经包含的丰富暗示,演说的行文用辞更是处处显示了诗人强烈的后殖民地时期的文学意识。文中的比喻乃至提到的人名地名,无一不表明诗人鲜明的政治立场与话语倾向。这一篇长达十五页的讲演稿中遍布前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的名称,相比之下,前殖民国家与殖民者却很少提及。讲演提到了欧洲,美洲,以及维多利亚,哥伦布,还有作家特罗洛普和诗人雪莱等等。不过很显然,这些字眼只是被用来衬托演说的主题,演说的主导意象则是由那些反复出现的词汇所构成的,即那些曾经遭受殖民者压迫的各民族的强大生命力。沃尔科特在斯德哥尔摩挤满社会名流的大厅里,向全世界发出对新文学的热烈欢呼:“能注视一种文学——使用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等数种帝国主义语言的一个文学——在一种文化的形成初期,在一个岛屿又一个岛屿上,含苞并开放,这令人多么欢欣,多么荣幸……这绝非好战的吹嘘,而是对必然的朴素庆祝:花季终于算临。”这番话公开而清楚地宣布,由少数人统治世界的历史已经结束,世界已经进入后殖民地时期。后殖民地文学的成熟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标志。
近二三十年来,西方的“性解放”导致了不育人口的急剧增加。结果他们只好依靠从发展中国家领养婴孩来维持人口数量和家庭关系。后殖民地文学的兴起及其取替传统主流文学的强劲之势,是否暗示了西方文化迟早也要出现“不育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