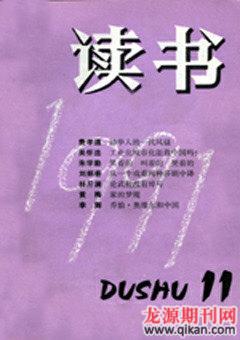“夜深闻私语”
大 东
读书不该有先入之见。
偏偏已有了先入之见——读张爱玲的《私语》,心中总还记着几年前读过的一本什么书,一种虽不清晰、却很执拗的印象:“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即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不过,一卷读罢,闭目沉思,虽然从文字间已俨然见出一位十足的女性,却又决不是男性、特别是怀了欣赏与爱慕之情的男性眼中的女性。张爱玲也讨论女性,但有着清醒的意识,尤其不是站定了女性至上的立场,一味回护女人的种种“不是”。其实这也是不必回护的。说起来,女人的许多“不是”,与男人的也并无怎样大的不同,无非女人把它用在治家,男人则施于平天下——大世界中的是是非非,除了较之小世界更热闹、或更残酷外,难道还有什么相异。可那不都是男人闹出的纠纷么?但这已是旧话。如今,在一切统一的趋势下,女性在为求解放而不断向男性认同的过程中,已失去了部分或大部分“自我”,自然也包括了那许多“不是”。这样看来,那种种充满个性的“不是”,实在是不很讨厌的;倒是连这“不是”也变得和男人的“不是”一般无二的时候,才真是令人嗟叹了。张爱玲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毋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这已算得通透之见。不过也还不妨补充一句,就取悦于人来说,男人与女人,真正也没有多大分别,只是男人在这后面隐藏了更多的内容罢了。
谈画,谈音乐,说跳舞,论写作,张爱玲总给人一种意外的惊喜——是么?竟是这样的么?虽然未必循着她的思路走,但至少被她从一种习惯了的崇拜中“拯救”出来,也想大了胆子用自己的眼光去看那早有定评的东西。至于能否像她那样妙语惊人,自然又是另一回事。
谈穿戴,谈服饰,我却只能万分惭愧自己的无知,而无法“投入”了。但仍然喜爱——便是喜爱那字词字句的拼接,甚至不要去想它的意义,就像《红楼梦》中的这一类文字。似乎这种不经意(也许是经意)的字词组接,就已经满溢着一种很可悦的情调,又似乎这种与众不同的造句方法,就显示着一种迥出众流的聪明与灵气,也正显示着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最令我感动的,却是这样一节不止一次被人引用过的文字:“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抉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若总是处在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境地,大约也不见得是怎样的快活。没有另一面,这一面也便无多意义。一种没有任何管束的自由,也许还会给人飘泊无依之感,觉得失去了栖居地,没有了归宿。故要只在那人生的一撒手——在经常的紧张中,突然有了那一刻的轻松,自己和自己开玩笑,和人生开玩笑,和周围熟识的与不熟识的面孔开玩笑。这是什么样的快活!
于是记起儿时常玩的“过家家”的游戏。玩的时候,是那样认真,那样“投入”,一切又都做得那样逼真。而一旦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只消说一句:“不跟你好了”,就可以轻松自然地结束游戏,而且丝毫不影响再次相遇时的欢好如前。
我觉得,张爱玲就是那个“过家家”的小女孩。至少是,她虽然长大了,成熟了,聪明了,但只要她愿意,就随时可以回到游戏中去。
但也许我的感觉不对——她本来很深刻,却被我理解得肤浅了。不过,做那样一个小女孩,不是人生中的一个诱惑么?
(《私语——张爱玲散文集》,刘川鄂编,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年五月版,4.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