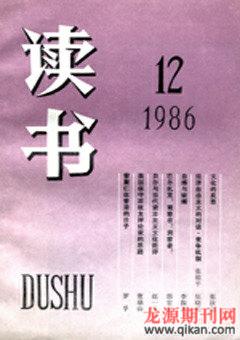唐代文史资料的拓荒者
朱金城 丁 聪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中,以史学名世而又对唐代文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应首推陈寅恪、岑仲勉二先生,其间岑仲勉先生以考据见长。他以大量精确而令人信服的资料为隋唐史及唐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开拓了新的天地。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而仲勉先生本人也受到同辈和后辈学者、研究工作者的敬重。陈寅恪先生对岑仲勉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推崇的,其晚年所著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曾多次引用了仲勉先生的学术成果。我很同意傅璇琮在他的《唐代诗人丛考》一书前言中的话:“从资料考据的角度说,岑仲勉先生的书对我尤有帮助。这真是一位勤勉的学者,他的著作中的材料的丰富是使人获益不浅的。”这确实是治学的甘苦之言。仲勉先生某些方面的学术成就,并不在寅恪先生之下。最近有一位薄负时誉的中年学者对我说:“今后有可能再出一个岑仲勉,但不可能再出一个陈寅恪。”言下颇有低估仲勉先生之意,但鄙见则不敢苟同。可是,仲勉先生身后的寂寞也是无可讳言的,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我想他教学时间短(他晚年始任中山大学教授)和优秀桃李门墙少大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从五十年代起,我因整理笺注《白居易集》,比较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各种有关唐代历史及文学的研究著作,开始接触到陈寅恪与岑仲勉先生研究白居易及其作品的学术著作,当我读到了岑仲勉先生有关《白氏长庆集》的文章,立刻为他学识的渊博和考证方法的精密所征服。仲勉先生研究、论证《白氏长庆集》的文章有《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白氏长庆集伪文》、《补白集源流事证数则》、《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从文苑英华辩证校白集诗文附按》、《从金泽图录白集影页中所见》等七篇,共十万字之多。这些文章对《白氏长庆集》流传的版本、白居易诗文的真伪作了详细精博的研究和考证,对我的笺注工作帮助极大。现存《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共有诗文三千六百多篇,数量浩繁为唐人之冠,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唐代文学、历史第一手资料。此书虽然亡佚了极小一部分,但由于是白居易生前亲自编撰,首尾最为完全,是流传到现在最可靠的文学编年资料。可是历来流传的版本情况极为复杂,仅以编排顺序为例,就有以宋绍兴本、明马元调本为代表的先诗后笔本及以日本那波道园本为代表的前后续集本,加之白集编成后,屡遭战祸流散,后来补入文字,羼入不少伪作,从而产生了白集的许多校刊和辨伪问题。仲勉先生根据传世的唐代碑志、正史、类书,互相核校,比较宋代以来白集传世刻本的异同,认为白居易的诗文,大致分为六类:其中第一类,是可以相信的白氏作品;第二第三类,虽然有可疑的地方,但没有确凿的强证能断定是伪作;第四至第六类,各本出入极大,肯定不是白氏所作。他还仔细校定白集诸刻各有所善,指出明马元调本优于日本的那波道园本,并论断白集东林真本早在唐末或五代已经消亡。这样,仲勉先生以其多年治唐史的广博精湛的学识,通过大量细致详尽的校证和考释,解决了白氏作品研究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白居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日人花房英树曾经发表过《关于岑仲勉先生的白氏长庆集研究》一文,对仲勉先生的研究推崇备至。花房英树著有《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及《白居易研究》两书,虽然其中颇有舛误疏漏之处,但也吸收了不少仲勉先生的研究成果,这说明仲勉先生对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仲勉先生对白居易的研究,不仅在资料方面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他的考据方法和谨严的治学精神同样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仲勉先生的考据方法是乾嘉学派和现代科学方法的结合,继承了乾嘉学派而又有所发展和提高。他十分注意资料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他的考据旁征博引,材料过硬,从不根据推测妄下断语。他的许多考据结果,可以说是超越前人的新发现,又是经得起验证的独到见解。如王之焕,新旧《唐书》都无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也都载而不详,闻一多《唐诗大系》也弄错了他的生卒年,岑仲勉《续贞石证史》据唐靳能所作《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知道王之涣卒于天宝元年(七四二年),年五十五,则其生年就可以推知为武后垂拱四年(六八八年)。又如白居易有一首酬令狐楚的《奉和汴州令狐令公二十二韵》诗题中称“令狐令公”,然令狐楚未尝官中书令,颇不得其解。历来研究者也从未有过正确的解释,如冯浩《玉溪生诗详注》卷一《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诗注引证了白氏诗云:“按《旧日唐书·志》,中书有中书令,唐之宰相曰同中书,固以此也。令狐虽未实进中书令,而《香山集》中亦称令狐令公矣。”仲勉先生在《唐史余
一九三七年初至一九四八年,仲勉先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这十一年是他致力于唐代文献整理成就最辉煌的时期。除以上所提到的关于《白氏长庆集》的研究外,他还写了许多传世之作,如《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元和姓纂所见唐左司郎官及三院御史》、《唐方镇年表正补》、《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元和姓纂四校记》、《唐史余
一九六二年,仲勉先生刚去世不久,他的另一部巨著《唐人行第录》出版,这是一部考订唐人行第的专业工具书。当时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凡是搞考据和资料研究的,都要受到批判和指摘,这部书受到冷遇正是意料中事。我偏偏不识时务,写了一篇《从唐代文学的人名工具书谈到岑著<唐人行第录>》,文中特别强调工具书在唐代文学、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对人物的辈行、宫职、经历等的探索和考证,是研究唐代文学、历史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一方面的工具书非常稀少,过去除了两《唐书》中的表传和有关的年谱碑志之外,主要只有林宝《元和姓纂》、丁居晦《承旨学士壁记》、徐松《唐登科记考》、劳格赵钺合著《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和《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等,而仲勉先生为这项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整理和编纂的,不仅仅是《元和姓纂四校记》和《唐人行第录》,而是一系列,是继承清代学者徐松、劳格等的研究成果,全面、深入、系统探索而获得很高成就中最杰出的一部分,每一个有关的研究者,都应当珍视他的贡献和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这篇文章写成后,当时很多地方不愿登载,最后还是靠了陈翔鹤先生的赞赏帮助才得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
凡是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学的都知道,唐朝人在诗文里经常喜欢用行第相称呼,或者以官职和行第连称,这种习惯,盛唐以后格外风行。以行第相称在当时很平常,可对后世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要弄清这些以行第称呼者的人名却非常困难。因为本来是史传中有名的人物,一经使用行第,失去了主名,便使人产生了茫然之感。如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白居易为白二十二等;况且由于传刻之误,一个人可能出现几种行第,或行第的数字讹误,如庾三十二(敬休)误作庾三十三,李六(景俭)误作李十一等;至于同姓同行第的人,那就更容易混淆不清了,如李十一建与李十一景信,又如元和时代有三个李三作宰相,元稹、白居易集中有四个李六等等。仲勉先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穷数十年精力,广搜博采,除两《唐书》、《全唐诗》、《全唐文》、《太平广记》及唐人笔记、诸家别集外,复采集唐以后的总集和选本、敦煌抄本、新近出土的墓志等,按笔划排比行第,并在每条之下作出详细的征引和考证。唐人的姓名、行第、官历有时互相串合,常常给考证工作带来许多麻烦,如由于仕宦的升沉不定,称呼也随时变换。岑参诗中称王季友为“王七季友”、“王七录事”、“王录事”,元稹、白居易集中称李绅为“李二十助教”、“李侍郎公垂”、“李二十侍郎”、“李二十尚书”,要把这些称呼搞清楚,需要极大的耐心,做大量的资料排比工作,仲勉先生就是这样,用力勤勉地编纂了学术价值很高的《唐人行第录》。通过他的努力,研究者可以很快查找到自己需要的唐人姓名或行第,手置一册,即可窥得整个唐代文学作品中行第的全貌,所得到的益处,实在是同类书不能比拟的。《唐人行第录》出版后,在唐代文史研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有关的唐诗选本,把白居易《问刘十九》诗中的“刘十九”误注成为刘禹锡(刘禹锡行第为刘二十八)了。
仲勉先生涉及的学术领域是极为广阔的,他研究过我国西北边陲地史学和中外交通史,精通多种外文和突厥文等少数民族的古文字,还写过佛教研究专著。解放后,先生任教于中山大学,写成《黄河变迁史》,共六十万字,这些精博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他的《金石论丛》与《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隋唐史》也由中华书局重印。其中《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是先生逝世前最后完成的未刊稿。唐郎官石柱著录唐代诸曹郎官四千六百五十人之多,为唐代史学、文学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残碑漫漶,
除了资料性的研究工作之外,仲勉先生也从事理论研究,他撰写的《隋唐史》是同类教科书中独树一帜的,此书以资料详赅、考证精博见长,每一结论都有详尽的资料摘引和注释,而资料必注明出处。同时,他又十分重视对史实的总结和概括,有鲜明的独到见解。
仲勉先生是近代著名学者中自学成材的典范,但他之所以有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与陈援庵(垣)先生当年的识拔也是分不开的。仲勉先生原籍广东顺德县,一八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生于一个普通商人家庭。童年入私塾,受过严格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他博闻强记,聪明超人,执笔为骈文,往往冠其曹辈。及长,自行点读《通鉴纲目》,学习金石之学,逐步对历史及金石之学发生兴趣。以后,他先后就读于两广大学堂、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广泛地研读了经史及宋人理学,深受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响,特别对王念孙、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和考据成果感兴趣。由于他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史学基础和在税务学校学习时打下的现代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基础,因此,他在因家庭生活所迫,不得不谋生于财政、税务、邮政等机关时,仍然以工余之暇,潜心治学,并在国内学术刊物如《金陵学报》、《东方杂志》、《中山大学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文章,引起当时史学界的关注,因此受到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赏识,约他为《辅仁学志》撰稿,并于一九三七年初,推荐他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在这以前,仲勉先生已发表了四五十篇质量很高的学术论文。入中央研究院后,由于战乱和其他种种原因,仲勉先生仍无安定的学术研究条件,但他却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做出了最辉煌的成绩。他曾经自谦地说过,他是半途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五十二岁到六十二岁,则是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好正是仲勉先生入中央研究院后的一段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取得了这样丰硕的成果,这需要何等的努力,何等的拼搏精神!据统计,仲勉先生治史四十载,著书十七种,论文近二百篇,共有一千多万言,这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中是非常突出的。先生卒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享年七十六岁。可以说,全国解放时,他已进晚年,但犹勤勉治学而不辍,晚年的许多著作都是在健康状况渐趋恶化的情况下完成的。可是,他的研究工作却从中年时的高峰攀向另一个高峰,尤其是主要的研究工作——唐代史料的整理,工具书的编纂,出现了系列性的成果。毋庸讳言,仲勉先生的工作并非没有错误和疏漏,他的研究方法也并非十全十美,但是,这与他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相比,是不足道的。现在看来,仲勉先生所从事的资料研究工作,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为广大研究者所承认,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建设,要建造起中国文化研究的大厦,是不可能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上海双白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三月新一版,1.60元;《金石论丛》,岑仲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1.80元:《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岑仲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版,2.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