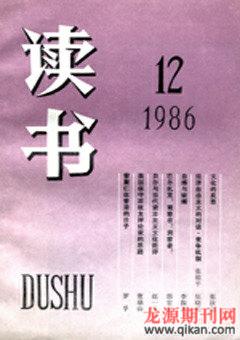长安文化与现代化
黄新亚
近代哲人黑格尔在研究、比较了世界各个文明古国之后,终于得出了结论:“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于是,许多学者都在探讨,是什么神秘的力量,使得这一文明古国能够永葆青春的活力,多次在历史长河中掀起复兴的波涛。经过长期求索,人们终于承认,中华民族得以持久存在,并不因为她远离欧洲,也不因为她地富人众,更不因为她善于在饥饿状态下生存;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的能力,能适应千百年时代的变迁,不断将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调节,将各种营养消化于自己的肌体中,并且抗衡企图改变民族基本精神的外来影响,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处于一种相当稳定的气氛中。随着现代化世界历史潮流产生,东西方文化狭路相逢,各种碰撞、渗透和冲突迫使中华民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就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过程。即使我们直到今天,实际仍是在整个传统中反对一部分传统;即使我们已经发现:从近代就开始批判、抨击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连续数千年仍然以新的形式,制约着许多非常清醒与先进的思想家;但是我们仍然要按照时代提出的要求去重新研究、把握我们的传统文化,以求在这个思想认识的“反复圈”中跃向更高的层次,找到那些代表时代气息的内容。
一、长安文化的基础
人类认识发展史中最基本的内容是概念与范畴发展的历史,长安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想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因为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历史的心理积淀,不可能用一种简单的直觉来测试。然而文化又不等于历史,它仅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所显示的趋向,联系着哲学、科技、思想、文艺、伦理、社会风尚等各个侧面,表现出一种主体意识。所谓长安文化①,是指公元九○○年以前,中华民族以长安为首都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公元九○○年以前中华民族的精神。要理解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千年古都长安
古都长安,就是今日西安,地处渭河冲积而成的关中平原,东临滚滚的黄河,周围拱卫着群山,内部沃野千里,物产丰富,因此这里自古以来就有以农为“本”的概念,就有闭关自守的要求。西安半坡与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都有保护原始人聚落的深沟,《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如果说城市的意义是保护住在城中的人而修筑的城墙沟壑,那么,半坡和姜寨的环护沟已预示了长安城的诞生,而且体现出中华民族作为古老的农业民族,极其重视家园的观念。人们探讨这里成为千年古都的原因,往往着眼于“险要的天然屏障保护着内部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这一现象,其实,在中国,符合“地险、国富”标准的地方并不少,长安之所以被封建王朝长期建都,还因为它位于中国的东西大道上。这样,中国的各部族在东西迁移的过程中,有可能在这里达到文化交融,从而找到共同的安居之所。
从历史传说上看,以半坡、姜寨文化为基础的炎帝、黄帝部落东迁黄河下游地区,构成了华夏文化的主干。但从可信的历史文献记载看,长安文化的成型,与大约四千年前西部的周部落迁入关中有关。周原出土的青铜器与殷墟青铜器极为近似,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与殷墟甲骨内容也大同小异,那些载着“甲辰,帝其令雨?”“王封建邑,帝若?”等内容的甲骨,说明与巫术紧密结合的宗教迷信既统治商人也统治周人,“帝”作为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神,曾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过无限的权威。这种权威因周人东进而发生动摇,周人联合各被压迫部族的人民共同消灭了强大的商朝,于是,以丰镐为都城(即长安城前身)的周人一方面宣扬过去尊奉过的“帝”,称之为“天”,说“天命廓常”(《诗·大雅·文王》),“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尚书·多士》)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力量,周公说:“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构成古代长安文化的核心内容,统治者一方面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另一方面也要讲“制天命而用之”。这样一来,对于神的无条件服从已被否定,人的地位,人与自然的统一开始得到肯定,自然不但不再处处被看作是一种支配威胁人的神秘力量,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成为人的意志的体现。例如我们看到的周代青铜器,造型笨重,体现统治者对权力的重视与自信;大篆书法铭文,体现着执法者的庄重,而那些饕餮、夔龙、窍曲、云、雷、火纹饰,不是凶猛的动物就是神秘的自然,它们对异族,是威吓的符号,对本族,则是庇护的神力,人对其他人的征服欲望就这样与原始宗教自然观巧妙结合。那些笨重的青铜器,那种种神秘而恐怖的艺术风格,实际是指示我们:自然的伟力,神的概念,很早就与古代中国人的要求相协调统一。周代社会与氏族血缘关系密切,人与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与服从,而且还有一种与氏族血缘相联系的伦理道德情感。这样一来,个体与社会整体应当而且必须高度统一,人与人之间有亲疏贵贱,然而却有一个共同尊奉的原则:即相亲相爱。阶级对抗使得这种“爱”充满了虚伪,但却不失为统治者协调其内部关系的重要武器。正因为有此思想基础,平王东迁、礼崩乐坏之际,才有崇尚周礼的孔子出来大声疾呼:“仁者爱人。”“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家思想才能逐渐得到被肯定的地位,成为协调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由此看来,长安早期的周代文化,已莫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正因为国家与氏族血缘、天人关系得到统一,所以,伦理道德有着极高的地位,基于氏族血缘观念,个体与社会整体不但不是互不相容,而且认为本质上就是统一的,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和谐的力量,又由荀子、孟子等人为代表的晚周民本思想而得到极大的加强。
孟子继承了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路线,但他痛感西周制度无法恢复,又为土地私有制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而苦恼,于是借用西周伦理道德,提出了协调“君”与“民”关系的主张。孟子的主张总起来一句话:“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说统治者要想成为统治者,必须庇护民众。与孟子的思想相辉映,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种协调“君”与“民”关系的思想,是长安早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就是长安文化的基础。
二、长安文化的形成
长安文化的形成,基本是在秦汉时期。秦人殷商时期“在西戎,保西垂”(《史记》卷五《秦本纪》);其先祖曾“俱以材力事殷纣”,“以善御幸于周穆王。”本属甘肃南部的羌族。直到公元六七七年才将其都城迁到“雍城大郑宫”,在这“
秦文化相较周文化多了一些新因素,氏族血缘关系稍有降低,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道德观念面临考验,君主集权政治日益强化。秦朝所信奉的思想,是韩非所提倡的法家理论:“君上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用其力。”(《韩非子·六反》)“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子·忠孝》)这就把周文化中的“君”与“民”的关系作了重大修正,早期的民本思想被赶出了正统思想圈;君权至上,成了一时的社会风尚。这样一来,长安文化便充满了危机,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子·五蠹》)这种唯吾为尊的专制主义文化论随着秦王朝的土崩瓦解而不得不改头换面。虽然我们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丛葬坑内的军队前,曾万分感慨那不可阻挡的扩张气势;我们在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上,曾不断感受到那无数智慧生力所酿就的民族精神;可是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伟大的奇观,是强迫苦役的结果,是无数苦难和血泪的结晶。所以,曾使人至今无限向往的秦都咸阳和阿房宫,随“戌卒叫,函谷举”而“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是那样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自然本质”。秦文化是长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失败的尝试,为长安文化的形成带来了无限生机。
继承秦王朝的西汉王朝,是来自长江流域的楚人所建立的封建政权,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汉文化获得全面交融的天机。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已证明:长江流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起源,虽然中原各国人视楚国为“南蛮”、“荆蛮”,但楚国的强盛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于是,楚人文化得以相对独立地发展。长江流域不象关中地区那样有四塞之固,有群山拱卫;江水一泻千里,为楚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于是,宗法制等级观念稍显薄弱,原始的自发性自由精神显得生气勃勃。楚人习惯于想象,尤其喜欢幻想,《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楚辞》中的诗歌,更充满了神话色彩。“内崇楚国之美”的屈原,尽管也向往三代之美政,尽管也宣传儒家的理性思辨结论,但他却始终保持与巫术神话相联系的想象,以及热烈的自由情感,显示其个体的精神。以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面貌,表现出与社会群体稍有差别的个体特性。现在,这种富于生气的文化来到了西汉长安,与周秦文化一起,充实长安文化的内容。正如邓以蛰先生所说:“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辛巳病余录》)正因为如此,汉代长安文化才可能有那雄伟的气势,扩张的精神,大胆的想象,以及文化创作者个人的情感与思辨。
汉代长安文化作为周、秦、楚人文化的交汇,在汉武帝时达到激烈交锋的程度。一派以董仲舒为代表,他看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实,想到了秦末农民“伐无道,诛暴秦”的后果,又要为汉武帝建立统一帝国的目的献策,于是再度运用早期长安文化的“和谐”手段,改造儒法二家。他剔除了先秦民本思想,保留了儒家“仁”的提法,他又摒弃了法家君权至上的主张,改为“天人感应”即“君权神授”的概念。这样一来,“天”或多或少对君主的权力有所制约。既然天具有道德和人格意志属性,那么,天人关系就不能不是一个被认真对待的问题,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相互渗透性,逐渐形成长安文化的重要特征。另一派以司马迁为代表,这位坚信历史可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的哲人,与唯我独尊的汉武帝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受宫刑是封建制度对他的肉体摧残,然而又使他的思想得以升华。他感到“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思想的主体,是周代文化后期的民本意识,他对孔子怀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情,推崇智、仁、义、勇、行等儒家准则,但他又不赞成儒家的“中庸之道”,向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充满爱憎分明的斗争精神。《史记》以人物为历史活动的中心,描写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尤其是一大批敢于与强暴抗争的下层人物形象,体现出尊重个性自由的趋向。建功立业与个性自由的要求交织在一起,使得《史记》代表的西汉长安文化充满了豪迈的气度,这时的人们一方面充满了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又不忘个人的地位,可以说周秦文化的协调能力与楚文化的自由精神在《史记》中得到了巧妙的结合。司马迁并没有向汉武帝低头,在《史记》中有大量切中时弊的篇章,但司马迁并不以修史为目的,而是以修史作为个人的一种自我精神解脱。他自己知道这部书只能“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但他并不因此而不负责任,而是全力以赴,反复推敲,写成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将它作为人的理想性与现实冲突的最后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汉长安文化虽然可以看到大一统封建帝国对人的压抑,但更多的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因此,其主流是那振奋人心的宏伟气魄和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由此看来,楚人文化与周秦文化交融获得了成功。中国的东西南北、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大融合,终于促使长安文化形成,这就是千古不衰的汉民族传统意识与心理结构。
三、长安文化的确立
三——九世纪,即所谓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长安文化大放异彩的时代。古今中外各民族文化的大交融、大吸收,终于确定了长安文化的特定内涵。
东汉时期,长安一度失去国都地位,左右政局的世家大族,一般也不在长安,于是秦汉时期形成的长安文化,开始因大量西北游牧民族的内迁而发生变化。李催郭汜兵
佛教在长安立足,是古今中外文化大吸收、大融合、大提高的重要标志,通过对佛教在长安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长安文化的确立过程。最早做出贡献的是玄奘,他为了解决“纷纭争论,凡数百年”(《全唐文》卷九○七)的佛性问题西行求法,取回那烂陀寺真经,并将译经、讲学、授业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佛教研究中心。只是玄奘所创“法相宗”,强调因明辨识,“万法唯识,心外无法”,体现了印度后期佛教大乘有宗的哲学体系,并不能适应中国的现实。于是虽然显赫一时,但三四十年后逐渐消失。曾参加玄奘主持译经工作的法藏在“因笔受、证义、润文见识不同而出译场”(《宋高僧传》卷五)后,认为“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迎合武则天的政治需要创华严宗,以“一真法界”的本体论,“法界缘起”的认识论,在长安城获得极高的地位。而只要口念“阿弥陀佛”即可“延年转寿,长命安乐”的净土宗,又将佛教普及入民间。最后,与士大夫修身养性观念最为相似的禅宗风靡长安,标志佛教的中国化完成。这种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佛教,宣传佛性在心,只要心外无物,即可“顿悟成佛”,与封建士大夫修身养性、治国治心的要求相适应,成为长安文化的重要内容。正因为各国、各地、各民族都能在长安最后趋同一致,所以,隋唐时期长安文化获得确立。秦汉时代那种雄伟、强劲的征服精神,这时又加上了奔放的情调与“和谐”气氛,这就是长安文化的主要特征。
四、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现代化,本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运动。它产生于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大进军时代,当着资本主义列强利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建立起强大的物质文明体系,并开始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时,所有落后与不发达的国家,面临痛苦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情愿的条件下展开的历史运动,因此形成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传统文化与代表先进方向的西方文化相逢而出现“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使非常明智的思想家,也很难作出清醒的判断。尽管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火花一次次在近代史上闪烁,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总是限制着中国前进的步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民族精英,深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弊,他们认为不用极端的反传统办法——即拆屋顶以求开天窗的办法,将不可能对中国社会有所触动;以至于今天又有学者提出:应该以传统为攻击目标,进行一次超过五四时代的大清算。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海外学者杜维明先生的一个命题值得我们重视(尽管对于杜先生的第三期儒家文化论,特别是对于杜先生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特别寄予厚望的从宋到明的第二期儒学,笔者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到底能否跳出五四时代以来那种简单的二分模式?”(见《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十期,第125页)
即使仅仅通过我们对长安文化的粗略勾画也不难看出,文化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都要根据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对文化传统进行选择、批判和改造,并按照时代的需要重新作出解释。当历史的紧迫感又一次把对文化传统的反思提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勇气跳出旧有的二分模式,选择不同于五四时代的新的起点,努力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要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就要在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营养的同时,对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进行认真清理,大胆扬弃那些不适应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内容——这些内容在杜维明先生所欣赏的第二期儒家文化中存在得最多;同时,要努力发掘可资运用的优秀文化遗产,以保持中华民族不断自我革新的进取精神。当我们研究长安文化时,总感到那活跃的生力,奋进的气势,大胆的吸取,与我们今天追求的目标,并非完全相悖,而且颇有发扬光大的意义。例如当我们在乾陵石刻群中发现,守陵的狮子,领路的天马、驼鸟、原本是“蕃族”、“夷人”时,难道不能为这伟大的气魄所鼓舞?当我们看到昭陵六骏飞奔的战马身上带着被敌人射中的箭矢时,难道不能意识到唐太宗告诫子孙“创业难,守业亦难”的苦心?即使那些充满内心自我平衡的诗词文赋,或多或少表现着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促使后人进一步思考,进一步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如果我们能作这样的理解,传统文化也许就不是一种包袱,相反,可以成为新时代的动力,鼓励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自我革新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前进。这就是说:我们既不应当作因循守旧的懦夫,因为停滞就意味着衰亡,我们也不必为因袭的重负而焦虑。如能正确地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由之取得前进的动力。中华民族毕竟有过在极端不平衡条件下取得伟大成就的长安文化时代,在那引人注目的两千年中,中华民族经受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吸收了古今中外各种营养成分,创造了至今使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汉唐文化,从而雄据东方。继承与发扬这一传统,中华民族将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开创更为伟大的前程。这是我们重新估价长安文化后所得到的启示。
①根据此概念相对而言,还可以指出中华民族的汴梁—临安文化和北京文化。长安文化,是一种古今中外各民族大交融、大吸收的混合型、开放型、进取型文化,汴梁—临安文化,是一种内聚型、思辨型、收敛型文化,北京文化,是一种由封闭型、保守型而不情愿地走向吸收型的文化。这种分类法,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公元九百年以前,公元九百年——公元一四○○年,公元一四○○年——公元一九四九年三个时期。本文主要讨论长安文化,其余两类文化,另有文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