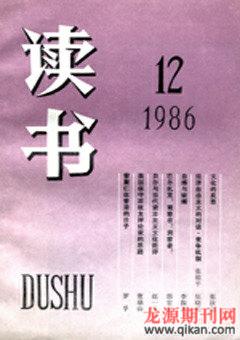音乐王国的西西弗斯
赵鑫珊 丁 聪
“哲学的目标是寻求基本原理的基础;头脑是需要借助于哲学才能达到崇高境界的。”
——贝多芬同女友贝蒂
娜的谈话
被当代美国小提琴大师斯特恩(Stern)誉为当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马友友(美籍华裔)拉了二十几年的巴赫组曲,如今对巴赫的音乐依然不时有新的发现,赋予新的理解。
为什么会如此呢?对巴赫的一首曲子难道也会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理解吗?要知道,天地人间只有少数几样东西才需要人类对它们不断作新的发现,赋予新的理解。德国古典音乐正在这几样东西之列。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灵魂的披露和人类本身的再现;德国古典音乐是旋律化了的德国古典文学和德国古典哲学总的汇合和交融。我们对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音乐的新发现、新理解,就是对人类本身,对我们自己灵魂的广度和深度的新发现、新理解和新的惊异。
在整个西方音乐史上,贝多芬大概是谈论哲学最多的一位作曲家。当然,他所谈论的哲学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哲学,即对人、社会和大自然以及这三者的内在关系的紧张而深沉的思索。
当贝多芬用德语陈述自己的哲学见解的时候,他充其量是一个三流(甚至还不能入流)的哲学家;可是,当他一旦改用旋律(音响)语言在钢琴、提琴和铜管乐器上陈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的时候,全世界都要毕恭毕敬地倾听他那雷鸣闪电般的英雄绝唱。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有外在的生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有的人(如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除了外在的生活,还有波澜壮阔的内在生活。然而正是这看不见的内在生活,正是他们的思想感情,正是他们的灵魂、胸臆和意志,才造就了他们,使他们形骸不存而精神不朽,使他们“其人虽已段,千载有余情”。
贝多芬当在这万古不朽者的名单之首。
“贝多芬的一生算得上是幸福的吗?”——近年来,当我听完他的乐曲,看完他的书信和有关传记,我就常常会这样问自己。
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回答。因为它涉及到人生哲学的最微妙处。而哲学问题的答案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也许,哲学只有不断提出问题而没有最后的答案。
论外在生活,贝多芬的一生当然算不上幸福。耳聋、经常处在孤独之中、多次失恋(终生没有点燃起家室的炉火)和其他种种的疾病、烦恼、痛苦缠身,还有经济拮据,生活上的窘迫,哪有幸福可言?
那末,论他的内在(精神)生活呢?
我想起了古希腊有关西西弗斯的神话。
西西弗斯被众神判决推运一块巨石至山顶。由于巨石本身的重量,到了山顶总要滚下山脚,于是西西弗斯又得把石块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永远也没有尽头。众神认为,让西西弗斯服这永恒的劳役是最严酷的惩罚。作为一种哲学比喻和象征,西西弗斯的命运仿佛就是人类的命运。贝多芬和歌德的命运,还有康德和黑格尔的命运,都是西西弗斯式的,而且都很典型。
一八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歌德对爱克曼说:
“人们通常把我看成是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的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地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象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歌德谈话录》,第20页)
歌德呕心沥血,不停创作辛劳的一生,是典型西西弗斯式的一生。但是他并不抱怨。他饱尝了创作的甘苦。
贝多芬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附在本书后面的贝多芬生平活动年表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十二岁起,贝多芬就开始服西西弗斯式的永恒劳役,推命运的“巨石”上山。一七八二——一七八四年,即从十二至十四岁,少年贝多芬便创作了三首钢琴奏鸣曲、两首钢琴回旋曲和一部钢琴协奏曲(另外还有其他许多作品)。十五岁那年,贝多芬还写了三首钢琴四重奏(即C大调、降E大调和D大调)。从一八○○至一八○一年,即从三十至三十一岁,贝多芬一口气竟创作了二十一首杰作。其中包括著名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他只活了短短的五十七个春秋,却创作了九首交响曲、五首钢琴协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十七首弦乐四重奏和五首大提琴奏鸣曲等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作品(包括从简单的歌曲到不朽的歌剧)。
用西西弗斯式的语言来说,贝多芬一生反复推运“巨石”上山总共计三百多次。每当一部作品完成,巨石滚下山脚,他又鼓起那超人的意志和压倒命运的勇气,操起那永恒的劳役,接着再往山顶上推,创作另一首乐曲。
他的一生所作所为,那一串大大小小的坚决的选择和果敢的行动,本身就是一部《英雄交响曲》,而且还是一首未完成的英雄交响曲。在他撒手离开人世的时候,留下了一大堆谁也辨认不清的手稿:《第十交响曲》、《b小调交响曲》、《D大调钢琴协奏曲》和《巴赫序曲》等。
贝多芬所留下的哪里是一堆手稿啊,那分明是留下了无限、发散的追求空间。这在我看来,便是构成幸福人生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是的,幸福的人生应死在无限的希望、追求和眷恋之中。悲哀的死是面向天边的落日;幸福的死则是朝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在这种意义上,贝多芬是幸福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幸福。它来自烦忧、孤独、悲愤和搏斗。
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贝多芬则是人类文化艺术史上的英雄。他们对自己(对人类)命运的哲学内涵都有清醒的意识,并为此感到极度的烦忧和痛苦。然而他们都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战胜命运的坚强意志面对人生沉重的十字架,正视那严峻而冷酷的石块,不断地把巨石推上山顶。
当代法国著名文学家加缪在散文《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表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见解:对自己(对人类)苦难处境的清醒意识给西西弗斯带来了痛苦,同时也造就了他的胜利,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决没有任何命运是不能被藐视并战胜的。顶顶重要的是,不要对神有任何期待,面对严酷的命运要有清醒的意识,要对它表示藐视和对抗——
“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贝多芬又何尝不是这样?应该设想,贝多芬也是幸福的。贝多芬不期待什么上帝(尽管他经常呼唤上帝)。面对严酷的命运,他深信“天助自助者”。
贝多芬的一生就是用超人的意志来满足自己,并鼓舞千百万人,去唤醒他们昏睡的头脑,点燃起他们内心世界的熊熊之火。他的音乐,就是对荒诞命运的挑战、报复和抗衡。
在推巨石上山服永恒劳役的过程中,贝多芬仿佛是借用西西弗斯的口吻说出了这样一句著名的箴言:
“……daβ Musik h
最后,若用爱因斯坦的人生观来衡量和判断,那末,贝多芬的一生也是够幸福的。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当它用来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的时候它才有意义。
贝多芬本人也持有这种幸福观:
“你可不要做那种专为自己而活着的人,你要为他人而活着:
只为自己无幸福可言,要在你的内心世界,在你的艺术中去寻找
更多的幸福……”(F.Zobeley《贝多芬传》,德文版,第50页)
今天,由于电子技术高度发达,收录机普及,地球上有多少人因为可以随时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才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充实、更高尚和更优美啊!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贝多芬之魂》并不是一部关于这位作曲家的流水帐式的外在生活传记。笔者的写作意图并不重在贝多芬的生平细节上化浓墨重笔,而仅仅是在一些关键性的事实(生平与创作)的基础上,努力揭示贝多芬的精神进展轨迹,他的心路历程,他那西西弗斯式的意志、勇气和人生的崇高使命感,以及他的音乐哲学体系同与之相对应的德国古典文化其他几条近似于平行的曲线(如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曲线和歌德、席勒的文学所划出的曲线)的相互关系。试图揭示这些内在的相互关系,正是本书副标题《德国古典“文化群落”中的贝多芬音乐》的涵义和“主旋律”。
其实,贝多芬一生的内在生活,他的心路历程所划出的曲线,本身就是一部宏伟、悲壮的“交响曲”。它也有“主题”,有“副题”,有主题之间的较量、斗争、否定、变化和发展,还有突如其来的“转调”,也有对故乡波恩、青少年时代的如烟往事的再现。
贝多芬的音乐曲线只不过是他的内在生活和心路历程曲线的回声、映象和投影。
我们这些现代人的灵魂和内心世界同贝多芬音乐发生共鸣,其实也是两条曲线的共振和大致上的重叠。或者换言之,贝多芬只不过是用千变万化的音响在一种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更优美、更深沉地表述了人类整个心胸的起伏和波动。
有两种传记:关于一个人外在生活的传记,关于一个人内在生活的传记。普朗克和爱因斯坦都写过有关自己的科学自传;那是很典型的陈述内在生活的思想传记。罗素和波普,还有卡尔纳普所写的哲学思想自传,也是属于揭示自己内在生活的传记。
在《科学自传》中,普朗克开宗明义就指出:
“我决心献身于我的科学,并且从青年时代起就使我热衷于它的,正是出于下面这一绝非不说自明的事实:我们的思维规律和我们从外部世界获得印象的过程的规律性,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人们就有可能通过纯思维去洞悉那些规律性。在这个事实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外部世界乃是一种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而去寻找那些适合于这种绝对东西的规律,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了。”(M.Planck《科学自传》,德文版,第7页)
那末,在贝多芬的心目中,什么是艺术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呢?《贝多芬之魂》这本书也将努力揭示这一点。
凡是笔者在本书中说错了或说得不够确切的地方,都将由贝多芬的乐曲一一加以纠正和补充。贝多芬音乐是第一性的原始标准,是最高裁判,是校正一切试图用普通语言文字对贝多芬及其音乐艺术世界进行界说的“标准米”原件。
普通日常语言文字的终点,恰好是旋律语言的起点。
我想起了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著名的格言: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darübermussman
schweigen.”(凡是不可以言说的,对它就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单簧管吹奏者,一生酷爱德奥古典音乐,具有非凡的音乐记忆和识谱能力。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有许多涉及到理解音乐性质的喻示。
所谓哲学思考,在他看来,就是弄清楚普通语言的界限:究竟什么东西是我们能说的,什么东西是不能(无法)用普通语言加以说清楚的。
贝多芬音乐的功能正在于超越普通语言的界限,打破人类在说普通语言时的沉默。象莫扎特一样,贝多芬总是习惯在钢琴的琴键上,通过音响和旋律,陈述人类意志本身那惊心动魄的隐蔽的故事,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或自言自语,或同别人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
例如,当贝多芬的好友(著名的女钢琴家)多罗蒂娅·冯·埃尔特曼失去了最小一个孩子的时候,起初贝多芬并没有去她府上安慰她。只是后来他才邀请她来他家作客。当她一走进来,贝多芬便坐到钢琴旁边,并且对她说:
“现在让我们通过音响彼此来进行交谈吧。”
就这样,贝多芬连续弹奏了一个多小时。
许多年后,多罗蒂娅·冯·埃尔特曼在回忆中非常激动地把这个故事告诉门德尔松:“他把一切的一切都这样告诉了我,我最后得到了安慰。”
这无疑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动人心弦的故事。将近三十年,贝多芬的音乐不也是把一切的一切都娓娓动听地告诉了我,使我得到了许多高于哲学智慧的启示和甘美的慰藉么?
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何以会有这种奇妙的功能呢?从青年时代起,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今天,我的须发已开始变白,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意识到了其中确有一些不能言说的神秘性。我想起了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拉斯金(JohnRuskin)的一段话:
“每一部伟大作品的精华部分,总是无法解释得很清楚的。因为它好,所以它好。”
是的,大自然和人生,科学、艺术和哲学,都有其内在的、不可究诘的神秘性。正是这种神秘性激起了人类历久不衰的探索热情。关于这种热情,爱因斯坦在《广义引力论》一文中写道:
“存在着求理解的热情,正象存在着对音乐的热情一样。……要是没有这种热情,就不会有数学,也不会有自然科学。”
当然也不会有贝多芬音乐,不会有力求深深地去感受、去理解贝多芬音乐艺术世界的涵义的《贝多芬之魂》这本书。
——哦,演奏不完,听不完,说不完的贝多芬音乐!
(《贝多芬之魂》,赵鑫珊著,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