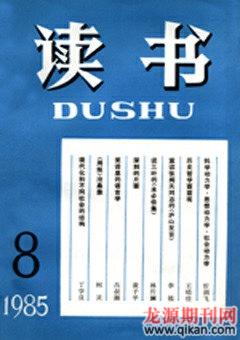真正的短篇小说艺术家
董鼎山 丁 聪
介绍安德烈·杜勃斯
约五年前,我在《读书》发表一篇《美国短篇小说的过去与现在》,其中我特别推荐一位专在非商业化的“小杂志”上发表作品的短篇小说艺术家。我称呼他为“艺术家”,因为写短篇小说对他说来是一项艺术。他的创作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他对这桩艺术的特别爱好。象一位清苦的画家一样,他的创作是为了自己的需求与发泄;他的产品不单纯追求发表。
这样一位献身于纯粹创作艺术的作家的才华已在逐渐赢得公众的赏识。此作家名安德烈·杜勃斯(André Dubus),他的成名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作一个特别介绍的必要。
杜勃斯今年已近五十岁,写了二十多年的短篇小说,还是默默无名。他共出版过四部短篇小说集与一部名叫《来自月亮的语声(VoicesFrom the Moon)的中篇小说,都是由波士顿一个小书局经手,既无广告宣传,也不受书评家的注意——直到去年,皇冠(Crown)书局突然替他出了一部书名《我们不再住这里》(We Dont Live Here Any-more)的平装本,才开始畅销起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杜勃斯原在波士顿三五十里外一个小型大学教书为生,现在已辞去教职,希望从此能靠写作度日。目前与他同居者是年纪较他轻了一半的第三任妻子与他们的两岁女儿。
杜勃斯出生于南方路易斯安那州,父亲是个土木工程师,母亲有教养,喜看书听歌剧。他在大学专攻英国文学与新闻学,毕业后却去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于一九六四年,他二十八岁时,有了两项成就:一是升为陆战队上尉,一是在著名的小杂志斯温尼评论(Sewanee Review)发表了一篇小说。稿费不过一百二十五元,但他的写作精神因此大振,靠了这一百二十五元大洋,他退了伍,辞去军官职,前往爱荷华州的作家实习深造专心学习写作。在那期间,他也结识了名作家里查德·叶茨(Richard Yates)与库特·冯尼格(Kurt Vonnegut)。
他说他并不后悔海军陆战队的生活。在军队的四年内,他每晚在军营中偷偷地学习写作。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斯温尼评论》并不是一件易事。这个小刊物销路不过四千份,却是美国一份较有声望的文学季刊。此后有一时期他接连不断地写了多篇短篇小说与一部长篇,都被退回,他曾一气而将退稿烧毁。
杜勃斯系于一九六六年开始在麻州一个小型大学教书。教书匠的低薪仅足以糊口。他的创作欲却没有终止。象一个清苦的、不能卖画换钱但仍专心绘画的美术家,不论发表与否他继续不断写作。
杜勃斯说过:“人们的生活不是一部长篇小说,而是一连串的短篇小说。”历年来,他发表过作品的刊物除了小杂志以外也包括大型杂志如《纽约人》,《哈泼斯》,《花花公子》之类。在他的小说中,主角都是我们日常所接触的普通人物。不过作者在这些常人的生活中掺入一些复杂变态、不能预测的圈套与曲折过程等成份。结果,一篇开首是平安无事、毫不奇特的叙述,会有爆炸性的结束。这种结构(必须自然、必然、平稳、适于性格、合乎逻辑)就是真正的短篇小说艺术。
杜勃斯自己正如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常遇到的普通人物。他服装随便,口中常含烟卷,他所爱好的运动是举重,他富有男子气概,外表是一个喜爱户外生活的粗人。初次与他相识,绝不能想到他是一个富含深思的创作家。
关于他对短篇创作的嗜好,他这么说:“我并不是有意识作出专写短篇的决定。我想那只是我的天然癖好。每当有人问我为何要写短篇小说时,我的答复老是自我轻视的。我说我在写作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二、三个角色而已。而人们总以为一个长篇小说作家能够创造整个的世界。”
曾有一个时期,杜勃斯确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以后不久即绝版。且听杜勃斯自己说:“有次我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农民》,读完后我印象极深。在短短三十页内,契诃夫创造了俄罗斯社会的整个缩影。我发现我必须不断学习。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写长篇小说。写短篇小说的时刻是我最快乐的时刻。一次我写了一篇名叫《胖姑娘》的短篇。在我所教的课室中有一个肥胖的少女,我就奇怪一个肥胖女子的心情感觉怎样?别人对她的看法怎样?托马斯·米尔顿(Thomas Merton1915—1968,董按:美国一位天主教修道士哲学家,著作甚多,在泰国出席宗教会议时死于车祸)说过,‘你的生活样式如是别人所期望你的那样,那末你就是生活在别人的想象中。对这名言我要加一句:‘别人如不想到你,你就不复存在。”
杜勃斯的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引线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现代生活的性格特征阻碍了男女之间互相的认识:在美国社会一般观念中,儿童自幼即受教导,长大后必须象一个男子汉,女孩子必须有女子气。杜勃斯以为这样的思路过程终于造成男女之间的隔离,而形成人们成年后深感孤寂的现象。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成长,男女间所产生的心理上的隔离,终会使他们到了老年对生活更难应付。
以一个创作家身份来观察,杜勃斯下面这句话(尤其是对我这个久居美国的人)特别有意思:“我们年纪越老,越有问题。此外,今日我们大部分人的职业都没有意义,惟一的收获是钱。钱不能给予我们满足;特别是今日的青年夫妇,男女都在工作。要他们在工作后回家过家庭生活,很是困难。”
这类对生活的看法,也许是杜勃斯二度离婚的原因。他的第三任妻子虽然较他远为年轻,但也喜爱写作,性格兴趣与他相似。在他眼中,这次婚姻将是永久性的,因他已不感到上述的“男女之间的隔阂。”
杜勃斯的作品中很多以男女关系为主题。但他否认故事中的男子角色是他本人的化身。他的中篇小说《来自月亮的语声》的角色包括一对离婚多年的父母。他们三个成年的儿女,以及离婚的大儿媳。父亲与曾经作过他儿媳的青年妇女堕入爱河,想要结婚。整篇小说的主线就是家中诸人对此事的反应,特别是尚未成年的小儿子的反应。此少年希望长大后进修为天主教神父,他对父亲的作为深感震惊与羞惭,向教堂神父去找慰藉(按,杜勃斯乃天主教徒)。同时,做母亲的却慰藉大儿子,劝他接受自己的生父与自己的前妻之间的罗曼史现实。这是一篇情节异常的小说,书中所描写充满了同情与宽恕,没有一个角色是“坏人”。杜勃斯不过借这个故事来描述了现代社会中的男女之间的复杂、隔绝的关系,而借用一个家庭的多种角色来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杜勃斯说这类故事只不过代表生活的一霎那,所以不能用长篇小说形式来表达。
杜勃斯的创作技巧是灵活的。我同意他的如下看法。由于出版界的商业观念,美国的所谓“方程式”(Formula)小说多的是。那类情节的小说能畅销,其他作家便相继效尤,制造类似的作品。杜勃斯这么说:“我在写作时从来不知故事走那个方向。你如果按预备的摘要大纲来写,你的故事就没有生气。作家的兴奋处就在这里。我写《标致的少女》时,只知道终局是一男、一女,一支手枪都在同一房间内,也知道女角色会染感冒。但我在事先不知故事如何发展。那男子会不会向那女子开枪?那女子会不会向那男子开枪?还是根本没有人会开枪?我的任务只不过是将他们的行动化为纸上的文字而已。
杜勃斯边写边改,写作速度很慢。他的写作犹如雕刻家的雕凿。在每日能写万言的有些中国作家眼中看来,他的这种缓慢小心的写法似乎太过分谨慎。且看他这么说:“过去我每天非写千字不可;现在我如能每天写百字已很满意。我想这与我近来心情较为镇静有关。过去我常如是想:‘如果我在未完成一篇故事之前死了怎么办?现在我的看法是,即使未完成一篇作品而死,那又有什么关系?”他的说法甚至使我也诧异。每天仅写百字已经使他满意,是否夸张?至少,这么写法,岂不影响了故事的连贯性?
谈到出版业对短篇小说这个形式的轻视,杜勃斯愤愤不平。他已在各种大小杂志中发表过作品,可是一想出单行本,就没有一家出版商表示兴趣。杜勃斯这么说,“他们如不喜我的作品,那倒无妨。可是有些书局却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后再来见我们。这就使我伤心沮丧。我尤记得我常因此流泪。”
皇冠书局去年的出版他的集子,给予他新的鼓励。他现在相信短篇小说的艺术已开始受了保障,前途乐观。他以为出版商已逐渐发现,短篇小说集虽不能如长篇小说一样的畅销赚钱,至少不会蚀本。
“皇冠”将一共替他出四个集子,预支版税一万五千元。在美国出版界中,此数微不足道。不过杜勃斯很高兴,他说他仍不懂“皇冠”会如此慷慨。“我一共约有五千名忠实读者,他们都已在初次发表时读过我这些作品。不过‘皇冠叫我不要担心。他们会替我找读者。”
虽然已踏上成功之途,杜勃斯仍决然不作“商业性”的写作。他喜观电影,可是他拒绝替制片商写各种报酬丰厚的电影剧本。他不愿将他所爱的艺术——短篇创作——化为一项赚钱的商业。他有艺术家的自尊心,宁愿饿肚而不愿为致富而写作。他只有两项工作条例:一、决不只为钱写一行字,二、决不在写作前饮酒。他的勃勃雄心是在临死之前在文学季刊(“小杂志”)上发表五十篇小说。他认为这类遗留后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真正的艺术,可保持他死后名誉的尊严。其实,他这种看重艺术,蔑视商业的态度已帮他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二万元奖金。
杜勃斯尚在壮年,上述那个雄心(发表五十篇文学作品的能实现,毫无问题。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