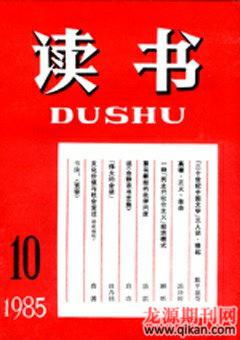披沙淘金探精微
凌 初
庞朴先生的近著《儒家辩证法研究》,是学术界关于儒家学说研究的一项新创制。作者不拘成说,在儒家学说的庞杂陈迹中寻究离析、披沙淘金,批判地清洗出一个斐然可观的“儒家辩证法”机体。这不仅在儒家学说的研究上是一种开拓性的探索,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研究,也是极为有益的尝试。
庞著《儒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在学术观点、主题论证以及创制方法上有许多独特的优点,值得称举,在此妄揆数端,以奉学林。
近些年来,关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学者多论定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折衷主义等性质,而研究的深度也略呈停滞状态。但学术的性格究非陈陈相因,而在于生生不息;学术研讨流别万殊,目的则在于探求社会、历史和文化变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性,恰如作者在另一部论著的自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庞朴:《沉思集·序》)。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作者提出了“儒家辩证法”这一命题。但如此一来,至少面临着两重困难:其一,谓儒家学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思想,是显而易见并为人所公认,但一般认为早期儒家与其他一些学派相比在哲学上创获不大,且又重言调和与平衡;其二在理论上,学者往往将辩证法学说一视为今所谓“三大规律”等。对此,作者依据列宁关于辩证法理论的正确定义指出:“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而在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研究过“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学派,不仅显见于道家、兵家等,诸如法家、名家以至“说王道、谈仁义的整个儒家学派”,“都有自己的辩证法”(第7页);唯对儒家尤须要“别具慧眼,透过儒家经典本身的种种非哲学的表达方式”,“去沙里淘金,从他们的经世之术、道德说教、日用生活去发觉贯彻其中的‘道,以还其‘庐山真貌”。这种透过事物的种种杂乱的表象以探其“真貌”的研究目的与方法,正是《研究》的独到之处,它为传统儒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作者对辩证法的有关理论作了必要阐述和辨析,认为辩证法研究矛盾,但矛盾也不是单方面的、没有任何一致性的对抗和对立;在这种意义上说,“两极对立都只有相对意义”,“任何只谈对立两极不可调和、发展只是不平衡的说法,都不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而是人们加到客观上去的一种反思,其性质,是形而上学的”(第4页)。平衡,也“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形式和条件”。因之,讲究调和、平衡的学说和学派,亦未必全无辩证法可言。这些见解,不论对于古代辩证法、或是对现代唯物辩证法学说的原理和原则的正确理解和运用,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基于上述状况,《研究》从哲学的高度着眼,对儒家学说的“仁义”、“礼乐”、“忠恕”、“圣智”等若干观念和范畴,进行了详细的阐发和论述,深入发掘其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它们“是儒家观察社会现象、处理社会问题、进行道德修养的总原则”(第79页),实现了研究的理性概括与抽象。对于儒家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精括为“中庸”与“三分”两个相近而又有不同的连动性范畴,它们旨在探求事物的一种既非过分又非不及的最佳状态,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符合辩证法的一部分法则,应予肯定。这样,儒家哲学以“仁义”、“忠恕”等若干范畴为起始,在划分世界、划分事物中“见对立而尚中,因对立、尚中而有三分法”——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儒家辩证法的体系”(当然还夹杂着不少杂质)粗具规模并与读者见面了。
作为哲学史专著,《研究》不仅对“儒家辩证法”的上述体系有一定创获,而且在若干具体观念、概念和范畴的探究上也多有覃思明见。作者根据儒家学说的特殊情况,确认“仁义”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并依《周易》等学者公认的哲学史资料证明,“阴阳”、“柔刚”、“仁义”等列并论,各“相反而皆相成”,亦即为对立同一关系,从而较准确地发掘了其哲学性范畴及涵义,并为本题的全面论证打下了坚实基础。
《研究》的这种独到和精思之处,还表现在它从一些非哲学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中,考辨和推究出一定的哲学本义来。如它在《中庸》部分,征引儒家经籍关于孙叔敖与狐丘丈人对话中的“三利”之于“三患”、官爵之于心志,“三分”部分关于“尧舜参牟子”、“禹耳参漏”等典故,加以精深辨析,谓“参牟子”应该象《管子》书中的“参表”一样,“实存的还是两眸子,第三者是虚的”,但它却是“第三只慧眼”,属于“中庸”与“三分”方法论中的一种“最佳状态”(参见第104页)。这种辨析既多神话性趣味,又富有哲学的敏感和理性,可谓独具匠心,别生慧眼。
其次,在本题研究和论证上力求纵横贯通。该书研究的范围和主题是先秦儒学及其辩证法,但它在相当程度上沟通了古代文化同现代精神文化、先秦儒学同其他学派以及古代中国同西方世界之间的内在文化联系。首先,《研究》是把主题放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和历史链条中去加以考察的。它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写道:“由孔丘开创并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不仅是中国先秦时期的显学,而且自汉武帝定之为国学之后,直至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为止,统治了中国思想界整整两千年之久,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对这样一种贯穿通代的思想学说,是没有理由不予以正视并做应有的理解、反思和批判地汲取的。先秦儒家学派,本身有其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定过程,对此作者有很好的揭示,如言孔子对于儒家学说的“开创”、孟子之于儒家学派的“中兴”(第109页),又孟、荀后于孔子而又有许多“高于孔子的地方”(第25页)等,力图从“思想史的变化史实”中,求得某种关于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此《研究》较充分地注意了先秦其他学派和学说,如“以侈求转化为目标,以守柔用弱为手段”的道家学派,“尊法术、尚功利”的法家学派,“出奇征、知彼己”的兵家学派,“辨名实、别同异”的名家学派等等,并认为它们各有其辩证法;甚至它们相互争胜,也“常有相通之处,并且恰恰以此铸成了对客观辩证法进行认识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第7页)。这得以避免那种狭隘的认识和孤立的研究途径,而将已往和过时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融于统一的真理长河之中,有助于我们今天正确地对待历史,“估价目前和规划未来的文化”。
在立足儒家哲学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打破空间和地域界限,把对儒家哲学的反思延伸到西方哲学,在联系和统一的人类精神文化总体中,比较地看待和把握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儒家哲学。书中谈到黑格尔对待古希腊哲学的宽容态度时,几举赫拉克利特的“一切都是生成”说、埃利亚学派的“反对运动”和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等诸流派古希腊哲学的特点;在论孟子的“中道”原则时,还明确指出西方学者与孟子的相似之处。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世界哲学史上的某些直接性知识,而且使《研究》建立起儒家哲学与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可能性比较,沟通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相近、相通之处。这种纵横贯通的研究与探索,对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和历史演变的规律性揭示,惠莫大焉。
再次,我们看到,在《研究》中作者采用了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这里,先是用辩证的方法研究“辩证法”。作者紧紧抓住辩证法关于“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这一理论枢机,依次探求儒家的“仁义”、“礼乐”、“忠恕”等诸基本范畴,从中揭示出“儒家辩证法”的特殊结构和面貌。作者深膺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批判精神,强调包括“三大规律为主要内容的辩证法”理论也必须进行不间断地“自我批判”,否则将“贻笑后哲”,乃至在若干年后被“贬之为朴素辩证法”——“譬诸积薪,后者居上”;“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所论并非故作惊人之谈,而应当说深切历史发展辩证法之要。因为如同马克思所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当今由现代科学技术的空前突破和巨大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浪潮,已经和正在对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理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反应,就是明证。至于作者研究儒家哲学,更是稽古而不嗜古,指“经师”之虚妄,讥“醇儒”之臆解,不去“轻信儒家自己所作的种种虚假表白”;即使“博雅如黑格尔”这样的近代哲学大师,他“瞪大了眼睛”而“未能找到儒家的哲学”,也正表明是这位思辨哲学之王的“局限”所在(第5页)。凡此都表现了作者对待学术、对待真理的不苟态度。在论证过程中,作者还大量运用了逻辑学手段和方法(详见第36页,第60页,第85—99页)。尤其对“中庸”方法论的论述,几乎通篇使用了专业化逻辑术语与符号,精简了论证过程,增强了学术效果。即把“中庸”依次化为“温而厉”→A然而B、“威而不猛”→A而不A'、“无偏无党”→不A不B、“或出或处”→亦A亦B等“四种常见的思维形式”;诸式的哲学含义及功能在于:“用A然而B以济不足,A而不A'以泄过”(第88页);不A不B“以极端的形式表示出来,然后予以否定,以见所用之中”,亦A亦B则是与不A不B紧相系连的“否命题”。这样的逻辑归结和分解,有理有力,有效地证明了“执两用中”的儒家“中道”哲学的内在结构和程式,达到了理论与方法、内容和形式的紧密结合和统一。
同时,在《研究》中,作者还分别不同情形恰当利用了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以及语言文学等论证手段和方法。前者有助于解决史实上的疑点和难点,后者使研究增加了不少特殊感染力。如对“仁义”范畴中“义”的论证,为弄清其确诂,作者几引卜辞、金文及《说文》等若干文献资料,追根溯源,博引慎取,力证“义”字本用为威杀(这有如《吕氏春秋·荡兵》中以“勇”为“凶德”),从而有力证明了与柔性之“仁”相反相成的刚性之“义”,揭示了其对立统一关系(参见第20—24页),使传统的“小学”成为哲学研究的得力工具。《研究》的语言技巧成文学手法也比比可见。它在“引论”中谈黑格尔的宽容时道:“老黑格尔”尽管“自视甚高,仿佛绝对精神全都装在他的荷包里”,但他还是有甄别地接受了古希腊哲学的家家派派(第4页);庄子“泯灭对立”之法,“好则好矣,无奈是空中楼阁,心里灵台”,乃至整个道家哲学的企望与结局,都在“自己理论形式的悲剧中凄凉实现,胜利者不是道家开山祖老子,而是历史辩证法老人,这是多少带点讽刺意味的”(第9页);最后道家的“乐土和王道,已如流水落花随春去,而无力回天了!”(第7页)在“忠恕”部分,谓儒家将“功利之心”粉饰为“与人为善”,“给取予之道套上玫瑰色的花环”……。辞间笔触,或轻盈诙谐,或淋漓洒落,寓哲理于文气,隐真知于燕谈;加之必要的历史化实证,使文笔、史法、哲思汇通交融,浑然一体,成为一种精深、信实而兼具文采的学术著作,就象有人所说的“音乐、文学和哲学”这“三颗露珠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一种新质态的高级产物一样(参见《读书》一九八四年第九期赵鑫珊文)。总之,这种综合性研究手段和方法,富有弹性的叙述方式,大大增强了《研究》的论证力和感染力,并且为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领域增添了色泽和生机,值得有关研究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庞朴先生所著《儒家辩证法研究》,是一部难得的学术专著,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儒家学说研究值得注目的新成果,但是,也由于该书的探索性质,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说一举就成为十分完备的形态。笔者以为其中有的论题或论点不无更慎重考虑的余地。在理论上,《研究》认为辩证法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理论前身的黑格尔那里叫做辩证法,通常所说的古代辩证法亦应作如是观,而不应“贬之为朴素辩证法”云。这里问题在于,一定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消逝,有无相与适应的一定历史基础以及时代性、阶段性特点呢?迄今而言的现代唯物史观的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为什么……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48页)此所谓某个特定的“世纪”无论是否就拥有那个特定的“原理”,但“每个原理”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乃是显明无疑的基础性东西;也就是说不同历史时代人们的生存条件及由此产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人们的精神素质也因之而异。在谈到自然科学的历史性分野时,恩格斯曾说:“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页)可以说,无论是观念和原理,还是自然科学等,既有其自身统一、连贯、不可分割的继承性和持续性,也有其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时代性、阶段性的“本质”差异。范畴,也不是亘古一样的不变模式,而是人类对于无限的客观世界不断认识的历史的产物。在远古“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吕氏春秋·恃君览》)的“无君”之时,也就没有什么“君道”观念和范畴可言;当人们能够用科学的辩证法则研究自然界时,以理想、幻想和臆想为能事的“自然哲学就最后被清除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2页)由此看来,辩证法是否按其自身发展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征,而相对划分为古代的、现代的,朴素的与科学的等等不同类型的理论形态,还须慎重考虑,因为没有相对稳定和可靠的理论系统,没有对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划分,也就无从进一步认识、把握事物的实质和总体。另则,具体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包括作者在内的学者大都认为它主要是在道德和政治学说等领域内展开的,作者借以研究的资料也多属“经世之术、道德说教、日用生活”之道,这就在极大程度上可以说儒家哲学是寄生于一个非哲学的圈子或干脆说是狭小天地之内的,那末就其性质和类型而言,它终究不过是一种道德哲学或伦理政治哲学,而其辩证法也主要地是关于伦理政治的辩证法罢了,尚不具有理论思维的抽象性与普遍性,这实在应该说是孔孟儒家哲学的固有弱点和局限。当然,即使如此,作者在《研究》中也力求突破儒家非哲学事务的圈子,而探求出一般、理性的哲学涵义,并确乎从儒家“种种非哲学的表达方式”中捕获到一定的辩证法思想或机质来,正可谓沙里淘金,稽探精微了。至于这儒家辩证法在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所具有的认识成就和地位,则又另当别论。此外,书中又语孔子除寓恨于仁再未另立一个表示恨的规范(第18页)、儒家恕道为“功利主义”(第54页)等,亦感有待进一步考论,在此恕不一一。谨成浅得,尚祈方家指正。
(《儒家辩证法研究》,庞朴著,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版,0.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