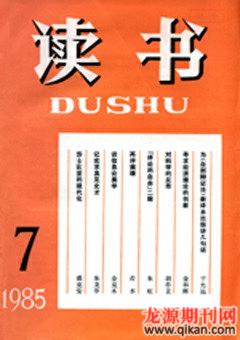文明的足下
周尚意 赵世瑜
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埃及的金字塔,从非洲丛林中的原始部落,到欧美现代的大都市,从印度恒河中迎着朝阳的沐浴,到美洲印第安人的奇风异俗……人类迄今创造的文明,林林总总,是如此千姿百态、形态各异。
我们不禁向足下望去,为什么我们一提到某一个特定地区,总是首先想到这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这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如果有,它是什么样的?文化间的差异和地域上的差异有什么关系?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意义?……
于是,文化地理学出现了。
一
要给文化地理学下个定义似乎不太容易,因为“文化”应该如何释义还众说不一。大致说来,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所谓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的狭义概念则多指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内容,如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道德观念以及其它意识形态范畴,也就是所谓精神文化。就多数文化的研究者而言,他们总是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去研究这一切对象,所以在这里,文化和文明是同一概念。许多西方学者在讲到“文化”时,也往往用civilization这个词。
上述文化概念都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当然,文化地理学是从地理环境、从区域性即不仅从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它们的。可以说,文化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事物和现象的起源、分布、变动及其同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间联系的学科。有人说的比较简单,如《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称其为“关于文化的自然和精神发展的地理学分支”;美国学者J.E.斯宾塞和威廉·L·托马斯则认为,文化地理学关心的是“被设想为文化集团的人类经一定时间在地球上的特定区域中所发展的人类技术和文化实践的方式”(《文化地理学》英文版,第4页),但都不能尽如人意。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概括:文化地理学所研究的,就是一定的人类文化和一定地理环境的关系。或是说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如何看待人类文化。
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就以家这个社会细胞为例来说吧。它既是个环境概念、地域概念,又是个文化概念。家庭是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家就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当然,文化地理学不能局限于这类“弹丸之地”,它研究无数个家庭及其所在地区,比如《水浒传》上的祝家庄在区域上自我封闭,引起的文化差异;现在遗留的“张家庄”、“李家店”是如何由张姓、李姓家庭分别使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结合在一起,尽管它们可能在地域上相邻,但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又譬如说,沙漠居民、草原居民、大陆居民以及沿海居民怎样由于居住的地域不同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这些都是文化地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但是,文化地理学往往是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接触它的对象。比如,文化地理的起源与传播这个专题,我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探究得较多,而从地理的角度考察甚少。众所周知,古文明或古文化的发源地有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长江流域,此外还有欧洲的爱琴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等。这些地区为什么成为文明发源地?自然地理环境对此有无影响?答案是可以求知的。在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比较低下的古代,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充足丰富,必然提供一地区成为文明起源地的外部条件。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上层建筑的发展,国家机构、城市(邦)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哲学宗教、风俗习惯的形成等等,成为文明发源、发展的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沿着特定的地理途径辐射传播,出现了文化融合和文化影响,形成新的文化,并进而形成文化区。
文化区或文化区域(cultural region or cultural area)的研究也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专题。法国学者埃梅·佩皮鲁在其《人文地理学》一书中提到,“流行的地理观点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多少种人类群体就有多少种文明,每一种文明是由其群体的智识活动、天然居所、从邻近群体引入的知识和物质组成的。然而向后追溯历史,人类群体无论在活动上还是在自然环境上都有差别,继而便有了地表的地理分区——文明区。”在这种文明区或文化区内,“其文化色彩应达到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台湾正中书局《地理学辞典》)。按照这种文化的一致性,有人将世界分为亚东文明、印度文明、北美文明等(同上书“文明”条);有人则将世界分为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及印度图缘、西南亚及北非、黑非洲、西欧、苏联及东欧、太平洋诸岛、澳洲、北美、拉美等十二个文化区(王煦柽文,《南京师大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分册》中的划分则将东西欧合为一区。还有的把日本划入中国文化区等。众所周知,很多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体系或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的继承、发展、吸收、丰富和传播,这一传统或体系变得日益稳定,形成了地域因素之外区别于另一地区的主要标志。如中国以及受其影响较大的日本、朝鲜、印度支那诸国乃至东南亚的另一些国家,就形成了一个由一个主要文化区和几个从属性文化区组成的东亚文化圈,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文化地理学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研究。景观,就是人们眼中望到的图景,山川河海、林海莽原等等都属自然景观,而由于人类文化的影响而在自然景观上增加的景物,如房舍、道路、耕地、色彩、服饰、村落……等等,都可转为文化景观。文化景观就是人们的劳动给大自然留下的痕迹。从飞机上俯视,我国有些地区的农田是方方正正的井字形,这样一种文化景观的形成除去自然的地貌因素提供的可能外,有没有历史上井田制的遗意?会不会是耕作方式的要求?抑或因为一家一户独立的生产生活习惯?或者与计算产量和国家制订征税标准有关联?……寻找某一文化景观形成诸因素,考察文化景观形成的过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人类的文化进化,以及逐渐独立于文化地理学的语言地理学、民族地理学、宗教地理学、艺术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所研究的内容。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文化地理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美国和德国的地理学家对其贡献较大。近年来则发展更快,分支更细、学科间渗透交叉得更深更广。而我国的文化地理学则几乎无人问津,研究者寥寥无几。因此,对文化地理学加以评述引进,推动我国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个中意义是不阐自明的。
当此之际,我们读到了陈正祥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
二
陈正祥先生自一九四二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之后,先后赴英、澳、日等国学习研究。六十年代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地理学讲座教授。在许多国际性地理学术组织中,他都是唯一的亚洲籍会员。在学术方面,到一九八○年,他已用中、英、日、德四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表过四百多种论文和专著,涉及政治地理、历史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各方面,是公认的地理学权威。《中国文化地理》一书辑成于一九八○年,其中收集了作者近年来撰写发表的十篇论文,虽然各自独立成章,不成系统,并未从理论上探讨文化地理学,但从各篇中仍可对文化地理,特别是中国文化地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故此引起我国读书界的浓厚兴趣。
诚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所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延续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它发源于黄土地带,然后向周围扩散;波及整个东亚、并向西伸入西域。在秦汉和唐宋时代,中国文化曾放发无比的光辉。……”的确,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绚烂光彩,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断丰富——尽管几遭侵扰,几濒沉沦——仍然耀眼夺目。《中国文化地理》以《中国文化中心迁移》为一类,包括对城邑(如《北京的城市发展》)、长城(其建置沿革)、大运河(其开凿修浚)等文化景观的研究,又研究了作为汉文化起源地的黄河、黄土高原,研究了汉文化中心的迁移。另一类则论述了地方志和游记的地理学价值,并通过对八蜡庙的具体研究,显示了地方志中文化地理资料的巨大价值。在利用古籍探研文化地理学方面,陈先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于汉文化中心的迁移,一直是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关心的热门问题,为什么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元代以后超过了北方?陈正祥先生认为,逼使文化中心南迁有三次波澜:一是东汉末三国时期的长期分裂战乱。东晋末年统治阶级的狂乱争斗之后,永嘉南渡、人口大量南迁,今江苏、浙江、湖北、江西一带开发繁荣;二是唐中叶的安史之乱。随着皇室南逃,人口南迁亦多,四川一带亦开发出来,成都已成为新的文化中心;三是金人入侵引起“靖康之变”,徽钦北狩,国都南迁至临安,成为“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特别是作者指出除了这三股外力之外,南方兴盛的内在条件——气候、土地等等自然因素极其重要,使这一说法更加完善了。
实际上,在几千年乃至上万年以前的文化发端之际,南方文化发展程度亦并不为低,如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距今七千年左右,属母系氏族社会阶段,遗址中发现大量已炭化了的稻谷和种植水稻的工具骨耜和木耒耜,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的遗迹。其村落遗址以干栏式建筑为特征,上层人居,下层养畜,榫铆工艺已普遍应用,并达到相当水平。仅此两端,便可说明南方文化在起源时期是和北方文化并驾齐驱的,至少是各有千秋的,这为南方文化日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陈正祥所提三次波澜不仅造成人口大量南迁,给南方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造成南方文化的繁荣发展,而且在此同时,北方却遭受着游牧民族的侵扰,如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的纷争代嬗,中晚唐时期突厥、回纥的乘机入掠,南宋时期金的统治,以及蒙元的大一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北方文化、特别是经济的发展,这些多处于氏族制末期或奴隶制时期的游牧民族的统治无疑给北方封建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相形之下,南方文化的成就就显得更为人注目了。但是,需要提出的是,宋辽金元时期以及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样也是民族大融合、新型文化复合体出现的时期,中国文化、特别是北方文化,由于北魏、辽金元和清朝的建立,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同样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况且,元明清以来,全国的政治中心固定在北京,北京也是联结全国各地的文化纽带,因此畿辅地区和江浙一带有着特点不同的重要意义。然而,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脱离,毕竟使中国文化的重点分布呈现出比较错综复杂的现象。
陈正祥研究中国文化地理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量运用中国古代地方志、游记之类文献中的地理材料。正如书中第二篇《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中所说,“中国实有更好更多的地理记录;而此项地理记录,便多数蕴藏在方志之中。所不幸的,是我们这个‘东西南北数千里,上下古今几百年的文化之矿,在近代尚未受人重视;也没有人想去发掘,更谈不到有计划的整理和研究”。
的确,我国学者对地方志的意义的认识还远远不足。尽管《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编)和《中国地理学史》(王成组著)都专章论述了地方志的地理学价值,但在实际应用上,地方志及其它古文献往往仍被束之高阁。陈正祥先生对地方志的利用是比较充分的,他利用其中自然地理方面的资料,求得全国龙卷风、台风、雹灾等发生范围、频率、编制分布地图;利用其中的人文地理资料,研究交通(如驿递)、人口、建置沿革、疾病传播及分布等。这里尤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八蜡庙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联合国有关组织请陈正祥先生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的资料,可中国不仅没有这种现成的地图,而且也没有资料来编制这种地图。但是,如果拒绝,这方面的研究报告上的中国方面势必造成空白。于是,陈先生“突然想起了八蜡庙”。中国的农村有所谓的八蜡庙、刘猛将军庙及虫王庙,这种特有的宗教迷信性的建筑均因蝗虫为害而设。八蜡庙和虫王庙是祭祀蝗虫的,刘猛将军庙是祭祀驱蝗英雄的,两者同时并存,用陈先生的话说,显然是“先礼后兵”、“软硬兼施”的办法。这些庙宇在地方志里都是有记述的,于是,作者先后在台湾和日本用了八个月的时间,翻了三千多种地方志,绘制出了一幅“中国蝗神庙的分布图”,因为蝗灾甚盛的地方才会修有这类庙宇,所以这幅图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蝗灾的分布图。研究自然灾害属于自然地理的内容,但作者却通过对某种文化景观、某种文化现象(宗教迷信)的探索,使文化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内容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
谈到制图,作者在编制文化地图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是比较突出的。仅在本书中,作者便附录了《西汉人口分布》、《西汉的三公和九卿》、《唐代的诗人》、《唐代前、后期的进士》、《北宋的词人》、《明代的三鼎甲》、《城的年龄》、《宋代之军寨堡》等三十几幅图。此外作者还出版有《中国历史与文化地理图册》以及《中国地图学史》等,其中不少是大陆学者未曾做过的工作,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
本书中还有专篇谈及游记,并论述了地理学记录的价值,这里不打算过多评述了。只是想说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未加利用的地理学资料实在是浩如烟海,且不说正史中的地理志、地方志、游记、《三通》中的地理专篇、地图等专门性的地理资料,象陈先生借以编制地图的《明代进士题名录》、《宋史宰辅表》、《全宋词》,象佛教经卷,象数不胜数的明清档案,还有神话传说、文艺作品、口碑材料等等均可为地理学家利用,特别是在明清档案中有灾荒、气象、漕运、河政等专类,对于研究清代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具有重大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发掘整理。
陈正祥先生对于台湾地名的研究也十分有趣,他将全省地名中重复的字,不重复字中的主要起首字,以大小和新旧相对区别的地名等等统计出来,又统计出各个不同时期地名的累积来判断文化层。如以鹿字为首的地名不少,说明当时台湾西部、南部多森林,野鹿成群,捕鹿为台湾先民之主要生产之一。后来榨糖业兴起,不常见的“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曾写道:“在学习过程中,我体会到文化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实难以严格划分,譬如地名,它是文化地理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却追随历史而不断改变。”的确,文化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考察它时间上的延续性就构成历史学,考察它在空间上的分布则属地理学的职责,因此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中国文化地理》一书的特色之一也在于此。就以本书第一篇《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为例,其中“汉文化的原始中心”、“逼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南北地位的转换”、“江南的开发”和“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这五个专题无一不是依靠大量史料加以证明的,而且总是按着历史发展的顺序加以描述论证的。第四篇《北京的城市发展》也是如此,除了第一节“自然环境”之外,大都谈的是北京城的历史沿革。但是,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之所以是两门不同的地理学分支,自然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如果说历史地理研究的是历史上自然地理现象和人文地理现象及其演变发展的学科,侧重其历史沿革及其变化,那么文化地理则更侧重各种文化现象与某一地理环境的关系,某一地区出现某类文化现象的原因等等。举例来说,城市可以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亦为文化地理研究的内容,但前者侧重于城市的历史演进,而后者注意城市建立的地理原因,如因地理条件不同而城的建置规模、功用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前者把城当作地理现象,而后者把城当作文化景观。或者说,文化地理学比历史地理学以及其它地理学分支更综合、更概括、更宏观一些,他们不注重“详细的人口空间分布、政治制度的空间细节,或是大聚落活动的地区分布”,而是对“地球表面经过时间活动的空间上有方向的和空间上不同的文化”的广泛研究,从而使其成为其它分支的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人类活动的手段(斯宾塞及托马斯《文化地理学》导论)。况且文化地理学不仅回溯过去,也注视现在,更展望未来,在时间上也相异于历史地理。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者往往是“大处着眼”的。
三
文化地理学回溯过去,也注视现在,更展望未来。
人是地球的主宰,未来文化的发展取决于人类。有人说,大家都没有预料到,人对文化的创造包括把握人在地球上的数量的生死平衡中的根本变化。的确,在大机器工业社会以前,人口的增长往往代表经济的增长、文化的进步,但是近一二百年以来,文化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一直如是的生死平衡性。战争和灾荒的相对减少,人们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致使死亡率大大降低,死亡速度远远低于世界人口出生的速度,使得单位面积上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反过来,又引起了人类文化的一系列变化:城市人口拥挤、市郊的胡乱延伸、人们要长途往返上班、汽车噪音、空气污染、土地价格高涨……,而在发展中国家矛盾更为尖锐,生产力低下,灾荒频仍,人口增长更快,人们的衣食之需几乎无法得到满足。这就给人们提出一个任务:必须解决人口问题,才能继续发展人类文化。
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弊端的解决者。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解决人口问题,从而减轻由此产生的文化弊端,而解决人口问题的手段,又往往是文化手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了解过去曾出现过的以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某一地区的自然界与人之间究竟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格局,才能达到人类文化相对完美的合谐。按照这一格局,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禁止乱砍滥伐,宣传刀耕火种的害处,保持土壤肥力,稳定地开发自然资源,禁止捕杀珍禽异兽和保持动物天敌平衡……以此调整生态系统,使自然景观变为文化景观的过程更加适合于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不致造成潜在的危机。按照这一格局,我们在工农业现代化的同时,要消除噪音、污染;防止城市向乡村的任意盲目地蔓延;注意保留历史遗迹、古代文化景观,……以此来保证人类的健康延续,人类文化才能得以健康延续。
人不仅是文化弊端的解决者,更重要的,还是文化的发扬光大者和建设者、发展者。人们可以研究农业文化景观。对松嫩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不同的文化类型进行类比性研究,对平原、高原山区和丘陵地带的不同类型文化进行类比研究,研究各地区的文化(人口、历史、民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对本地区农业的影响,从而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种地区性因素的影响,以更快更好地发展当地的农业,也就是所谓“不盲目引进,不盲目照搬”的意义所在。
人们可以研究某一地区精神文化、知识水平的分布情况。正象陈正祥先生在“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一节中所做的那样,研究唐宋文学家在全国的分布,研究明代进士的分布并绘制出密度分布图,还可以研究今天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分布以及密度,从而联系过去研究现状,了解地区文化发展水平及制约其发展的因素,制定有重点的文化发展规划,合理分布有识之士,实行智力支边,避免人才浪费。
人们应该注意文化区的研究。陈正祥先生说过,“我的研究考察旅行,使我深信汉文化并非单独属于中国人,而是为整个东亚人民所共有。”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埃·赖肖尔也曾写道,“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和罗马。在战前,他们喜欢用‘同文同种的说法来形容同中国的关系。”(《日本人》)如前所述,汉文化的辐射波及到整个东亚,在各个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影响颇大,我们则可通过对这一文化异同点的区域性研究,提出我们对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政策方针的可行性论证和咨询,实行有坚实基础的区域性全面合作。同样,在我们考虑东西方关系、中东问题、拉美问题……等国际战略之时,也有必要借助对文化区的研究,明确一地区与另一地区、一国家与另一国家友好或敌对关系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制定有理有据的战略方针。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参考价值都是非常大的,我们无法一一举例而论。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将系统论、控制论引入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并可以计量方法建立数学模型来论证说明文化地理的问题,这无疑会大大促进文化地理学的飞速发展。
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在欧美诸国要领先于我国,然而陈正祥先生的《中国文化地理》也不甘示弱,在这一领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我们在这里对这部书略加评述,其目的正在于期望借此引起学术界对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视,并促进我国这一学科的发展,使之能够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促进汉文化圈人民的了解和合作”,对全人类文化的健康发展,有所贡献。
(《中国文化地理》,陈正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