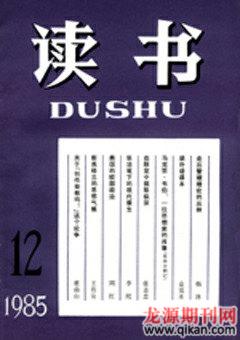是米粮川
郭 因
读完了徐寿凯同志所著的《古代文艺思想漫话》之后,我在书后的空白上写了这样几句:厚积薄发,深入浅出。不是卓异的,却是坚实的;不是天都峰,却是米粮川;不能使人惊奇,却能使人受益。
我从和作者多年的交往中知道,读者也可从他的著作中看出,他读的书是相当多的,下的钻研功夫是相当深的。一些问题,他淡淡谈来,可谁知道,那里面蕴含着多少艰辛,多少汗水,多少不眠之夜!对于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观点,作者排列出从刘勰到管同共有十几人赞同。对于嵇康“声无哀乐”的观点,排列出:赞同的有唐太宗到契嵩和尚等一批人,反对的有黄道周、尤侗等一批人。对于苏轼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观点,则排列出,宋、元、明、清共有从杨慎到何绍基等十一人就此发表过意见。关于声律论种种,关于诗格、赋格、文格、诗句图、本事诗……作者广征博引,条分缕析,扼要而系统地介绍了内容作了比较研究。如此等等,岂是一个涉猎不多、钻研不深的凑热闹的学者所能办到。
作者学风是平实的,行文是平实的,观点也是平实的。全书贯串了对种种问题的持乎之论,在论法家的文艺观时,他既指出了法家的文艺观是不要文艺的文艺观,又指出“他们否弃文艺,对于限制统治阶级的声色享受和控制人们过量的文艺生活或许多少有点积极意义”。紧接着又指出:“即使如此,也不过是因噎废食”。论六朝文学时,他指出:“文学需要的是文质彬彬的美,是统一着真、善、美的美”。在论及刘勰的偏于不变的“通变”,肖子显的忽视继承的“新变”,皎然的既重继承又重创新的“复变”时,他指出:“复变”说“确是我国文艺理论遗产的精华”。论李商隐时,他既指出李对骈体复炽起了推波助澜的不好作用,又指出李对古文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的批评并非没有积极意义。论到古文运动时,他既指出其反对形式主义文风是对的,又指出其尊古崇古思想却是错的。论到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时,他既指出梁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是对的,又指出过分夸大小说的作用则是不妥的。如此等等。没有什么观点是耸人听闻的,但每一个观点都的确是经得起推敲的。
对于寿凯的这本著作,我所最注意、最感兴趣的,是他谈论古代,常常不禁想到现代,常常笔锋那么稍稍一转,就或启发人深思,或诱使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他把“兴、观、群、怨”看作孔子诗歌理论的精华,并指出孔子认识到怨、刺可以转化为巩固统治秩序的有利因素,而杜绝怨、刺必将加速统治秩序的崩溃,这正是孔子的远见卓识。他在谈论孟子的“知人论世”这一诗歌理论时,明确提出:“看一看建国以来,一些极左的文艺批评,不知人,不论世,片面地孤立地对文艺作品无限上纲的行径,不能不使人感到孟子的知人论世这一诗论的可贵”。在论陆机的《文赋》时,指责“作品明显地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敢抒发真性情,而致力于形式美的追求”,因此认为不能“评价过高”。但对于一些古人多方责难“诗缘情而绮靡”之说,则又指出,于此可以看到“我国文艺批评中另一个有害传统: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和“再一个有害传统:栽陷”。在论及王充、葛洪的文论时,他特别肯定他们的反崇古。并特别指出,葛洪曾“具体指出象《诗经》这样的经典性作品,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顶峰”。在论及谢赫的《画品》时,又说:“世界上不会有到顶的理论”。在论《文心雕龙》时,他指出:“如果没有真谛或真谛很少,即使给作者戴上唯物主义的桂冠,也不会给作品增色”。在谈论王通时,他指出,在孔子未必是错的东西,由于时代不同,条件变异,王通的仿效,就变成了荒唐。谈到唐代的文化交流时他指出:“历史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闭关自守,不能吸收融合外来的文化,就会故步自封,难以进步”。如此等等岂是一个闭门读死书,毫不关心窗外国家大事的迂腐书生所能发出。
(《古代文艺思想漫话》,徐寿凯著,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