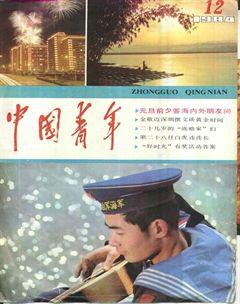大后方
杨益言 刘德彬
正在这时,忽听一声喝叫:“让开点!”林涛侧目斜视,只见几个宪兵掮着皮箱在人丛中开路,后面一群人趾高气扬,通过宪兵、别动队的警戒线进入机场,向停机坪走去。其中,有几个穿着笔挺的西装、蓄着仁丹胡子的日本人,还有几个身着黄呢军装,披着大氅的达官贵人。其中一个穿凡尔丁中山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瘦矮子,突然离开了这支特别队伍,后退两步,凝视着林涛正要招呼的来人。几个正在巡逻的宪兵突然也在这人身前身后停住了脚步。林涛要迎接的那位中年人对这突然的变化象看在了眼里,又象根本没有看见似的,还是迈着刚才那种稳健持重的步伐,默默地走着。瘦矮子挟了挟眼镜,扬了扬手杖,忽然高兴地欢叫道:“Hel1o(哈罗)Dr华(华博士)。”来人侧过头来,瞬间脸上露出了惊诧的神色,随之竟三两步迎上前去,抱住了对方瘦矮、用衬肩垫得很高的肩头:“想不到,多年不见,今日能在此相逢,真是幸会。老同学,今非昔比,荣耀高升啦!”
林涛不觉一怔。此刻,林涛和这两位久别重逢的交谈者之间,仅距数步之遥。林涛对来人和瘦矮子的谈话不仅听得十分清楚,而且,从来人向他投来的目光中清楚地看出了要他镇静、耐心等候的示意。林涛强自按捺住猛烈狂跳的心,遥望着那些优先进入机舱的当今权贵们,同时用眼睛的余光看见瘦矮子把一张雪白的名片递给了来人。来人接过名片,立刻高兴地念道:“重庆大学秘书长柏森?这就是你呀,改名了。”瘦矮子笑道:“Dr华,你可还是丰采依旧,豪情似昔哟!哈哈!”随着,又压低了声音:“前几年,听说您到华北去了……”来人笑道:“鄙人东西漂泊,一事无成,说来惭愧!所堪告慰者,不过是贱体粗健罢了。”瘦矮子立刻紧挽住来人的手臂,恳切地说道:“当兹世事多难之秋,我倒想有一言奉告:老兄何苦再在他乡飘零?何不就在此间结庐,为桑梓教育事业服务,一舒劳顿?老兄才智过人,弟所深知,略展抱负,何愁不能在此创立一番事业?请千万不要拒绝家乡人的殷切希望吧!我马上搭机去南京教育部开会,半月内准回,您回乡省亲之后,请一定光临寒舍,一定!”一名宪兵悄声伺立在瘦矮子身边,示意瘦矮子得赶快登机了。瘦矮子这才放开来人,向停机坪走去,边走边招呼道:“半月后,一定恭候大驾!”
“原来这就是重大秘书长柏森。”林涛注视着柏森钻进飞机以后,正要回头,只见来人早已走过了宪兵、别动队的警戒线,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来人坦然自若的神情,手中提着的准确无误的接头暗号,使林涛很自然地开口说道:“哎,大舅!路上可好?你不认得我了?”
“哟,长这么高了!真是,你不喊大舅,我认不出来了。”
来人的答话,更使林涛相信:他正是林胡子要找的人。林涛高兴地接过来人的皮包,就向通往河坎的浮桥走去。
他们刚走过浮桥,就听见嘹亮的军号声响了起来,一群脚登麻耳草鞋、身穿灰布军衣、腰佩盒子枪的川军正在整队集合。一名青年川军将领,身后跟着两名弁兵,微露笑容,迎面向他们走来。“这是刘副官,”林涛悄声向来人介绍了一句:“我们坐他的车进城。”军官停下脚步,向来人招了招手,说:“大舅请上车。”
话音未了,一辆黑轿车已停在跟前。几十名刚才集合的川军,早已爬上了另一辆卡车。来人和林涛、刘副官刚坐进车里,轿车立即发动起来,缓缓向山城驶去。那一辆满载川军卫队的卡车紧紧跟在后面。那些神气十足严密把守着浮桥两头的别动队员,这时才回过神来,若有所失地望着这支小小的车队,缓缓爬上河坎的陡坡,向市区开去。
在望龙门附近一处僻静的街口,司机把车停了下来,来人象完全理解林涛、刘副官的安排似的,无言地紧握了一下林涛的手。刘副官敏捷地打开车门,让林涛下了车,立刻关上门,又走开了。林涛一闪身,穿过一条有着百十层石梯的小巷,当他再次出现在大街上时,他看见他刚乘坐过的那辆黑色轿车和满载川军警卫队的敞蓬卡车,已经绕过小什字,正通过这一段繁华的市街,向上半城驶去。
林涛在人丛中站了一会儿,确信身边没有“尾巴”以后,才从另一条小巷折回下半城,准备过江到汪山去参加同学们的郊游。他到了长江渡口,心中还挂念着那不知来历的人,他为何而来?又到何处去了?……
离开繁华的市区,那小小的车队加快了车速,沿着成渝公路飞驶。但刚转过一个山湾,车队便开始减速,在一片参天大树荫蔽之下的一座大院前停了下来。卡车上的士兵,迅速下了车,隐到树林深处去了。
弁兵开了车门。来人、刘副官走下车来。车边,是一条浓荫遮盖着的光洁的三合土路。路的尽头,是一座灰色的小楼。刘副官陪着来人向楼房走去,两个弁兵在身后紧紧跟着。
绕过一处用松枝编成的屏风,便是一座经过精心布置的花园。光洁的三合土路两旁,星罗棋布地点缀着一些小小的亭榭、假山、花台。灰楼旁的几栋平房,无疑是厨房和侍从人员的住所。这些小巧玲珑的房舍,隐藏在一片葱翠欲滴的芭蕉林和竹林后面,几乎很难一眼看尽。路旁,没有一片落叶,没有一株杂草。四周静悄悄的。庭园中心,有一个雅致的喷水池,从那喷口喷出的水花,在阳光的照耀下,五彩缤纷,十分瑰丽。那喷泉口不大,喷射的水也不高,不知是由于山峰岩石和参天大树的阻拦而形成的共鸣,还是由于别的什么缘故,那水声竟似激流奔腾般嘹亮。
跨上台阶,就进入了灰楼的正厅。厅里的陈设无疑是上等的,一色的红木嵌镶黑色云母石的大椅子和茶几上摆设着精制的茶具、烟具,但这些东西上面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墙壁上的玻璃框里,嵌着一张主人的放大照片:头戴大盘圆帽,身穿陆军上将军服,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厅门,但那镜框四周却结满了蜘蛛网。
刘副官推开一间小客室,等候弁兵奉上烟茶以后,便和弁兵一起退了出去。
来人坐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缓缓地吸燃了烟。象一切谨慎而又经验丰富的人一样,他似乎对现在置身的复杂环境早就有所了解,对可能出现的一切早就有准备,一点不用担心似的。他把身子向沙发靠背上一靠,向着空中悠闲地连吐了几口烟圈。过了一会,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房门应声敞开,一个花白胡须齐胸,手持龙头拐杖的人,健步进入客室。来人缓缓地站起来,迎了上去。花白胡须的老人,丢开拐杖,一下子抱住了对方:“你来了!怎么也想不到。这里没有外人,华兴文同志,你想得到吗?说呀!”
来人摘下金丝眼镜,详细看看林胡子的面庞,说:“我当然想得到。”
“是组织上告诉你的?”
“不是。”
“那你怎么想得到会在这里相逢?”
“胡子,你还记得三年前在张家口讲过的话吗?”
林胡子自然记得三年前和华兴文分手时的事。那天夜里,抗日同盟军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发现这支队伍已经被蒋介石、日寇的阴谋彻底破坏以后,支部正在一栋小屋布置撤退的事,不料,小屋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了。大家立即拔枪在手,准备突围,可是发现特务已封锁了突围的唯一巷道,情势十分险恶,如果再延误几秒钟,特务大批涌到,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没有生还的可能。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巷道外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守在巷口的特务被迫转身还击,同志们立即乘机发起冲锋,一齐冲了出去。转过一个街口,林胡子才发现:在巷道外突然从敌特背后开枪,只身营救大家脱险的不是别人,正是同盟军作战参谋、刚从外面返回的华兴文同志!接着,他们便在漆黑的夜幕中,各自东西,分别转移了。在暗夜里告别的情景,虽然事隔三年,林胡子仍然记忆犹新。他更清楚地记得,他将转移何方,当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决不可能向华兴文讲什么。他决定到四川来,还是一年以后的事。那时,四川中共地下党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为了站稳脚跟,重建组织,上级党决定选派一个和四川党毫无关系的同志去四川,这才派了他来。因此,听到华兴文的问话,自然使他惊诧。
华兴文却盯住林胡子的眼睛问道:“你还记得,你说过:‘东方不亮西方亮,离了北方有南方吗?”
“难道这几年你走遍了全中国?”
“那倒没有。北方,我走过;南方我去过。到了这里,在你进门之前,我就听出来了,那是你特有的脚步声告诉我的。”
“原来是这样。”林胡子忙着请对方重新落坐。
华兴文一边坐下,一边却皱起了眉头,说道:“说真的,你想通了,我可还有点想不通呢!”华兴文把眼睛向客厅外扫了一眼,小声说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安排我们在这里见面?”
林胡子知道:华兴文来渝以后,只接触过林涛、刘副官。林涛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因此,不禁反问道:“刘副官给你讲过什么没有?”
“没有,在车上他什么话也没给我讲过。”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当然知道。”华兴文说道:“车子一转进这大院,我就发现了,这庭园,不是三五年能经营得起来的。中央军进川还不到二年,蒋介石立足未稳,修不起这样精美的庭院。它的主人无疑是地方军阀了。你知道,我也是在山城长大的,我当然熟悉家乡的环境。这里离闹市不远,转过山口,从树林中望出去,这庭园对面的山峰,就是虎头岩。这小客厅旁边,布满尘埃、蛛网的正厅,特别是墙上悬挂的那幅肖像,都证明了这庭院的主人,正是当今的西南王、四川第一号军阀刘湘!”
“对!就从这里说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