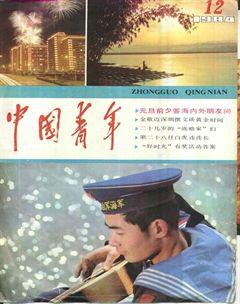来自“天堂”的挽歌
杨泉福 王燕生
一封盖着“1983.10.30”邮戳的航空信从海外寄往中国。这是一封出逃者的家信。两年来,从信封到邮票,他家里的人都熟悉了。但这封信拆开后却不同寻常:“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了。”再往下看,这分明是一封诀别的遗书。就在这封信漂洋过海的时候,发信人在异国他乡自缢身亡了。
这是一个在随团出访中私自出逃的人的悲剧。象所有的事件一样,有它真实的时间、地点、人物。这里虽然隐去人名和地名,但并不影响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思考。
机遇不能代替正确的政治方向
好的机遇都让他赶上了:
——1971年,17岁,进某外语学校。
——1973年,19岁,被选送到某大学外语系代培。
——1974年,20岁,被选送到国外学习英语。
——1976年,22岁,学习归来进某外事单位工作。
——1980年,26岁,随某歌舞团第一次出访。
—一1981年,27岁,随某京剧团第二次出访。
从1971年到1981年,也就是他从17岁到27岁的十年中,他三次进校学习,获得三次出国的机会。和他同龄的人,当年扛着行李去北大荒插队时,他已经轻松地登上了出国留学的飞机;后来许多人拉家带口,还要上夜大、奔学历的时候,他又揣着大学毕业的文凭在令人羡慕的单位里出出进进了。
在动乱的岁月里,人们常常受机遇的摆布。有时它能出人意料地推举一些人,有时它又常常无情地埋没一些人。机遇对这个年轻人的确够照顾了。
当然,条件是党和人民给他创造的。当他踏上我们国家出类拔萃者的台阶的时候,他应该更多地想到责任和义务,更多地想到创造和奉献。但恰恰相反,他的心思又用在谋划新的“机遇”上了。当他认为另一种“机遇”来临的时候,他的履历表上却填下了可悲的一页。
——1981年11月3日,在随某京剧团出访时外逃。
——1983年10月30日,从国外传来确凿的消息,他在极度苦闷中自杀。
把他的经历前前后后连贯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深思了。在人的一生中,的确会遇上各种各样的“机遇”,但“机遇”不过是提供了某种条件。在同一“机遇”上,有人可能做出可歌可泣的事,有人却可能做出遗恨千古的事。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机遇”都不能代替正确的政治方向。“机遇”毕竟不能造就一个人。过错不在于“机遇”,恶果只能由亵渎“机遇”的人承担。
他为什么由“开朗”变得“内向”了
1973年,来某大学培训的几个年轻人住在一个通铺上。夜里,两个小伙子被虱子咬醒了。这个说:“虱子是从你身上爬过来的。”那个说:“虱子还是闻着你的肉香。”嘻闹了一阵,又都呼呼入睡了。这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年轻人。可见,那时候他是个性格开朗的人。
后来,他变得“内向”了,开会或闲谈的时候,他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话也不肯多说。偶尔从别人的话中听出一点怨气,他常常借火助势地插上一两句。个别的一件事,经他一“点拨”,似乎就成普遍性的问题了。
详细观察这种性格的变化,还是可以发现内在逻辑的。几年来,国内、国外交错的生活经历,在他的头脑里逐渐产生了两种积累。
一种积累来自国外生活:摩天大楼还只是在电视里影影绰绰地出现时,他早就出出进进习以为常了;家用电器还只是在橱窗里展览时,他早就亲自享用了;“民主”和“自由”别人还只是在国内一般地谈论时,他却已经沉醉在异国那“民主”和“自由”的雾霭之中了。
另一种积累来自国内生活:想买辆名牌自行车,左转右转没有门路,他感到恼火;准备结婚了,可房子还没有着落,他埋怨“在中国要房子比找老婆还难”;“西单墙”被取缔时,他更为不满,“这又算得了什么?”……
量的积累会带来质的变化。两种“积累”就象两个电极,常常在心头碰撞起火,最后归结为两句话:“国外,如何如何……”“中国,如何如何……”。当他觉得现实和自己的想法格格不入的时候,既要发泄,又要顾到一条防线,这时,他由开朗变得“内向”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内向”,实际上是一种扭曲,性格的扭曲往往只是在一定的场合。心里的话总还要在别的机会透露。
他曾经是团员,但后来他越发觉得组织生活是一种负担了。他是他所在单位超龄团员中第一批退团的。别人退团时,对团组织还一往情深;而他呢,倒觉得从此以后,可以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了!
他也曾写过入党申请书,那是在老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下写的。但他递交申请书之后,就不知应该干什么了。也许,他以为人们的政治信仰,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示,而不是精神世界的革命。他更不知道,人们对党的信仰和追求,不仅需要言语口头的表示,尤其需要亲身的艰难的实践——这里包括,党在顺利的时候,和党同心同德;党在困难的时候,和党同舟共济;党在奋进的时候,和党一路高歌。
他也曾和女友谈过政治。他的女友——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还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当他把国内国外的对比感袒露给他的女友时,女友问他:
“你总说外国好,是一切都好吗?你老说中国不行,是什么都不行吗?”
“你又没去过外国,你当然不了解外国!”
女友叹息道:“你要是能看点辩证唯物主义的书就好了。”
他呢,满肚子的不高兴。本来,这种思想交流是有益的,有助于矫正他思想上的偏颇,但是,他渐渐把这作为一种多余的纷扰。他提出,以后见面不谈政治,离政治越远越好。
他的女友对此为他担心过,说:“你可以不搞政治工作,但不能没有政治头脑!”他的亲属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你说你要远离政治,但政治偏偏要找你;你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错误的政治观念就要侵入你的生活……”这些善意的劝导,都被他当成了“说教”,当成了耳旁风。
团组织,他退出了;入党的意愿,他逃遁了;政治生活,他远离了……理想的阳光开始消失,心灵的灯火逐渐熄灭,这个“内向”的年轻人,将走向何方?
危险的情绪在他心里升级
在国外的学习结束后,他回到原单位,被安排在图书馆。当他听说这里有机会出国选购图书时,他同意了。但后来一了解,出国要排在几年之后,他又不干了。为了调到外事部门当翻译,他左一个报告埋怨大材小用,右一个申诉强调不能丢掉口语。为了发挥他的才能,领导批准了他的要求。他一方面得意洋洋,另一方面他又耿耿于怀:“这里太不自由!”
他在婚事上也是这样。1981年他准备结婚,因为女友还在大学学习,领导希望他推迟婚期,按规定大学生学习期间不能结婚。这下他又恼了。通过其他途径,他开出了介绍信。当结婚证拿到手的时候,他不再得意,只是恨恨地骂道:“不人道!”
就这些问题来说,他也应该满足的了。可是,以怨报德的危险情绪在他的心里升级:由对一个人、一件事上升到对一个规定、一项政策;由对具体的规定和政策又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
一个成熟的青年,应该懂得怎样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对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顾大局,识大体,懂得体谅和谅解。体谅就是合作,就是支持,谅解就是调节,就是分担。个人的困难毕竟是暂时的,八十年的青年应该着眼于祖国的未来。这一切,对一个在动乱中成长,和祖国和人民共忧乐的人来说并不难理解;但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似乎一切都隔得那么遥远。十年内乱,他多少留下一些伤痕,但幸运很快给他弥补了。17岁他离家学习的时候,世界观还近乎空白;19岁一下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世界观的舞台上,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东西明显占了上风;回国之后,本应该清除掉那些腐朽的东西,但他却以“内向”的方式把这些掩盖起来了。
牢骚和不满一次又一次上升,“美梦”一次又一次闪现,防线快要不攻自破了。
希望寄托在“天堂”
一个忠于祖国的人,即使长期生活在海外,他也会觉得自己始终踏着祖国这片土地;一个拿定主意外逃的人,即使窥探到一个机会,他也仿佛进了“天堂”。
1981年10月,这个年轻人作为翻译随某京剧团出访。11月3日晚,当最后一个国家的一场演出圆满结束后,演员们都去参加招待会。席间,忽然有人问道:“咱们的翻译哪里去了?”开始人们没有在意。见多识广的翻译对这种场合习以为常了,不必自始至终陪在这儿。人们回到旅馆已经是下半夜了,房间里仍然不见翻译的影子。他能上哪儿呢?这时,一位细心的同志向团长报告了一个危险的迹象:他的牙具不在了,提包也不在了。人们的心格登一下,莫非他……
人们不愿轻易用“莫非”这个字眼推测一个人,但是此人的去向又恰恰是到了那“莫非”的地方。
当地警方正在查询这位年轻人。对外交礼仪颇为熟悉的他,此刻显得手足无措了。
——你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留在这里。
警方问明他的身份后,郑重地告诉他:
——留在这里,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你要再三考虑。
年轻人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送上门来,却受到对方的冷待。他十分尴尬、难堪,低着头重复了刚才的话:
——我希望留在这里。
警方向他讲明当地情况,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
——留下可以,找工作不可能。
年轻人仿佛此刻才明白:这里不是礼宾司,不需要外交辞令;对方是冷峻的,对他并没有兴趣。他只好有气无力地再次重复刚才的话:
——我希望留在这里。
“希望”,“希望”,他在别人面前讲了三次“希望”。人们常常要讲到自己的希望:一个爱国者,总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振兴和富强上;而这个年轻人的希望却投眼在异国的土地上。有的人讲起自己的希望,受到别人的尊重和赞扬;而这个青年讲到自己希望的时候,别人投去鄙夷目光,这种希望是没有任何光彩的。
出逃的目的,他总算达到了;但进入了“天堂”,景况并不那么美妙。
这里的竞争使他不赛而栗
他选择的“天堂”的确是个“高福利”国家。但是这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却有近30万失业者。救济金哪里来的?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税收。“天堂”里的温饱就靠税收维系着。交税是人们不情愿的,那么由税收演变的“福利”当然就很少有“爱”的成份了——何况对一个外籍人。
在这个“天堂”里,他可以领取一份救济金,但却难于找到一份工作。他曾打听到某学院需要人。这个学院里有位教师因需要休养,校方决定补进一人,为期一年。校方登报公开招聘,很快有7人提出申情。校方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核、评议。一个月后,确定了人选。刚刚公布结果,一个落选者就提出异议,委员会只好重新评议。又经过一个月,总算定了下来。入选者刚要报到,政府来了一道指令:为紧缩开支,暂时不得录用新人。“竞争”这个词过去他听说过,但“竞争” 在这里激化到这个程度,使他不寒而栗。
找不到固定的工作,能给人帮帮忙也是好的。他又打听到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半官方机构要人。这里的确有些抄抄写写的工作。经人介绍,他开始在这里帮忙。不久,他发现人们对他冷淡了。原来人们知道了他的底细。一个规规矩矩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怎么能使用一个偷偷摸摸从中国跑出来的人呢?很快他知趣而退了。
有人告诉他,这里还有一种记时付酬的工作。譬如扫马路、洗碗碟,一小时的收入也很可观。他不想再听下去。他想,到“高福利”国家,追求的难道就是这个吗?这种事,我死也不干。
尽管警方当初对他有过忠告,但他总有一种幻想:我是个大学生,我是有一技之长的人,总可以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年轻人爱说事业。什么是事业呢?学历和地位不是事业,金钱和名誉也不是事业。事业不是一个人的事。真正有事业心的人,首先是爱国的。外语固然是他的一技之长,但是,这一技之长如果不和爱国之心凝聚在一起,莫说事业,就是作为谋生的职业,又有谁看得起?
他越发感到“身份危机”
在当地大学生举办的“中国日”联欢会上,放映电影《今日中国》。电影开始后,这位年轻人悄悄地走进来。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要来看看祖国的土地和在这国土上生活的人们?他不敢堂堂正正地坐在前面,只是坐在偏僻的角落里。电影即将结束时,他又悄悄地离开了。他不敢在这种场合公开露面。他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在当地一个图书馆里,他偶然碰到一位在当地大学里任教的中国专家。他十分留心当地的每一个中国人。他小心谨慎地凑上去搭话。专家并不认识他,只是有礼貌地对他说:“我们用什么语言交谈?英语,汉语,还是当地的语言?”年轻人的脸变得灰白了,低声说:“当然是用汉语。”简短的交谈之后,他走开了。他不愿让人们认为他忘了祖国。但和祖国派来的专家在一起,该谈什么呢?他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假日里,中国留学生应邀和当地大学生外出郊游,恰巧遇到这位年轻人。朋友们邀他一起去玩一玩,他显得十分尴尬,去还是去了,但一路沉默寡言。年轻人谁不愿意和大伙有说有笑,但在中外青年的正常交往中,他又怎能不考虑自己的身份。
在这里,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主人,还是客人。主人应有的资格,他不具备;客人应有的尊贵,他更不具备。
他曾做过客人,不论是在外留学,还是出国随访,人们都尊敬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受到热情的接待。现在,他已由“使者”变为“难民”了。战争中一些人沦为“难民”,还能得到人们的同情;一些人受迫害沦为“难民”,还能得到人们的款待;不光彩的出逃者沦为“难民”,在人们眼里就成为卑鄙者了。
投奔到这个国家后,他多么希望由“客人”变为“主人”。但这里的态度是明显的:你可以丢开“客人”的架子,但却难于让你进入“主人”的行列!
为了摆脱困境,他曾鼓起勇气找到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专家。在长谈中他开始流露出悔恨。这位专家并没有和他接触的义务,但我们的专家还是尽了一位师长的责任。批评、忠告、开导,他都默默地听着。谈到归宿的时候,他显得十分茫然。“我算个什么呢?跟您不一样啊!”
“我算个什么呢?”他的确强烈地感到了自己身份的危机。职业是一种身份,年龄和经历也是一种身份,但最重要的身份莫过于自身的人格和国格。当这种危机来临的时候,一个人就快要毁灭了。
悔恨并没有促成决心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记述一下在异国土地上,他和那位中国专家的一次谈话。
这位专家是一位戴着眼镜,镜片后面闪动着和善目光的年近五旬的人。她和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成年人一样,鄙视那些背弃祖国的人,但对一个眼看着走向毁灭边缘的人,又抱有一种欲往救援的心愿。
当这年轻人找上门来的时候,她没有回避。她相信,真理还会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挥一些威力。
专家:你为什么要离开祖国呢?
年轻人:我觉得中国缺乏民主和自由,“西单墙”那么一点位置,还被撤掉了。
专家:你大概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民主和自由如果仅仅在那么一块小小的墙上,中国早就没有希望了。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那时人们几乎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东西。建国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党和国家正在培育适合我们国情的民主风气。这种民主是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而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这种真正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能比吗?可有些人偏偏不珍惜更不善于运用这种正当的民主权利。一个民族要培育起正常的民主风气是多么地不容易。你应该看到这个现实。
年轻人:正因为我正视现实,我才有那么多想不通的东西,我才决定……
专家那低沉的声音里已经有了几分愤怒:中国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他们都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吗?十年内乱中,他们被整得那么苦,但他们终于挺过来了。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在光明里有那么一些阴暗点,你就觉得一团漆黑了。你以为自己留了几年学,就看到仙山琼阁了,那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影罢了。这些,你现在大概有些体会了吧。
这里,与其说是交谈,不如说是“交火”。心灵的撞击,多少使他清醒一些了。沉默,有时倒是一个人反省的表现。临走的时候,他只是说:“后悔见到您太晚了。”
悔恨并没有促成决心,他还徘徊在他国的土地上。年轻人呵,如果你迷途知返,祖国是会宽恕回头的浪子的。
他还幻想把孤帆靠在“爱”的码头上
一年多“天堂”的生活,使他觉得没必要那么“正经”了。工作已没有指望,做人也失去资格,生活还能靠什么解脱呢?他想起不知是什么人讲过的一句话:“人生应该跟着爱情走。”
他过去的那位女友,本来是一位挺好的姑娘,他们之间也有过一段挺好的爱情。可他说毁就毁了。后来虽然一次次地仟悔,可是一切无法挽回了。
他本希望把这只孤帆靠在一个“爱”的码头上。但在这个“天堂”里,“性”的结合并不困难,可“爱”的融和却很难找到。
就在他住的公寓里,他从自己的房间搬到一个女人的屋子里。虽然她还是大学生,但已年近四十。她本是个独身主义者,但不知为什么看中了这东方小青年。
在这里,我们不愿意多写他的私生活。至于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在和那位中国专家的谈话时,只是淡淡地说:“我有这种需要,她也有这种需要。至于将来,很难说。这里的女人靠不住。”
双方明明知道对方都靠不住,却还要厮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能够幸福吗?这里我们只想告诉读者最后的结局:这位年轻人在极度苦闷中死在公寓里,“孤帆”最终还是沉没了。
他给自己做出的结论
人死了,但死前他不想给人们留下更多的猜测。如果说他以前写给家里的信主要是粉饰和掩盖,那么最后这封诀别信总算说出了真情。要说所有的问题都认识清楚了,不大可能;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自我结论还是发人深省的。
事到如今,我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了。我在这里的头一年,一切都还顺利。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是我对现实没有认清。生活在这个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主要问题是精神上的,我很快地便感到了精神上的空虚,又找不到工作,打发时间成为问题。这不仅是我的问题,许多当地人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我认识到人生每时每刻都站在选择点上,选择是必要的,或者走这条路,或者走那条路。你说我不想选择或不做选择,这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这就是当今奉行于欧美的存在主义。……
我现在还认识到自由是相对的,自由的定义应该是不失去巳取得的成果。人生真正的价值是肉眼看不到的,是物质以外的无形的东西。
家庭成员之间要经常沟通思想,如互祝生日快乐之类,非常重要。我当时出走时就是由于长期在外单身生活,和家中有断沟的结果。
我是做了一件错事、蠢事。人生应该跟着爱情走,谁破坏爱情,谁先吃苦头……
切防白人的笑脸,笑脸的背后藏着的就是刀子。千好万好不如家好,我很想家,但我回不去了。一失足铸成千古恨,我后悔、自恨,请让我去吧……
我太自信了,太狂了。实际上我只是个顽童而巳。这个世界大不可辨,花花绿绿无奇不有,不要为失去我而过分伤心。这种事在西方多得是。这个世界是好人受气,坏人得势的地方。就象越有钱的人越自私一样,越发达地区的人越自私,自私到不多给一丝笑容的程度,而且人际之间的关系勾心斗角,复杂霉烂透顶。
我对生活巳经十分厌倦了。请代我向……告别。
一个人认识真理往往要有一个过程,有时甚至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但要切记艰难的历程绝不包括叛逃;付出的代价绝不包括自寻毁灭。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这个年轻人铸成了大错。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过:“对于真理我们必须反复地宣传,因为错误也有人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个别的人而是大批的人在宣传。”来自“天堂”的挽歌警示我们,在那些“一切向外看”,以为资本主义就是“天堂”的思潮面前,宣传真理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这里提供的只是一服清醒剂!
(插图:聂昌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