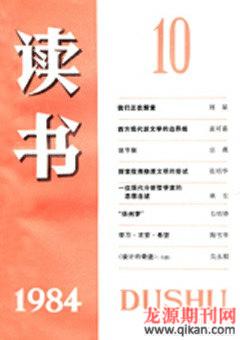译名别议
1984-07-15 05:54王少梅
读书 1984年10期
王少梅
读董乐山《译名改革刍议》(《读书》八四年七月号),引起兴味。旁通连类,为之打气帮腔。
钱锺书先生小说的人物,如在《围城》155页、《人·兽·鬼》92页中,均曾论及译名。小说家常借笔下的人物作自己的传声筒,并且,小说也可谈艺(详见《旧文四篇》26页、《管锥编》656—7页,参看15、62、1416、1517页)。《围城》即把T.S.Eliot、T.Corbiére、Leopardi、F.Werfel分别戏译为:爱利恶德、拷背延耳、来屋拜地、肥儿飞儿。译名依声寓意、声意相宣双关。既然“异域之言亦如禽虫之鸣叫,人聆而莫解”(《管锥编》1329页;参看《也是集》27—8页),那么似乎也可以效法中国古典或民间的禽言诗,拟声达意、依声寓意而又声意相宣地译名(参看《宋诗选注》167页、《管锥编》116—8页、《增订》114页)。当然,译者所译未必巧合贴切原作的音意,也容易走样变相。不过,翻译文艺作品里的人名未尝不可尝试尝试——百花齐放嘛。“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妙造化境(《旧文四篇》62页),译名颇为关节,值得费劲用功去探索琢磨。同期许国璋文缩用外国人名头一个字母,干净适当,可法。
猜你喜欢
廉政瞭望·下半月(2022年4期)2022-05-12
计算机应用文摘·触控(2019年13期)2019-08-26
学生天地·小学低年级版(2018年12期)2018-01-15
神州民俗·上半月(2017年5期)2017-06-01
求知导刊(2017年5期)2017-04-15
读读书(2016年3期)2016-12-10
作文与考试·高中版(2016年13期)2016-05-28
作文通讯·高中版(2016年6期)2016-05-14
读书(1991年3期)1991-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