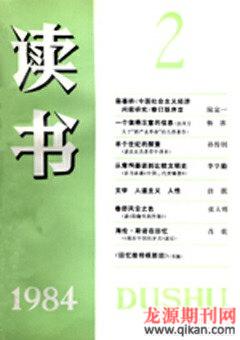丁声树同志的治学精神
杨伯峻
丁声树字梧梓,凡是和他相交较早较久的,很少人不称他为梧梓,我写这篇文字,还是习惯地称他梧梓。
他的确是“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他的爱国主义不始于坚决拒绝去台湾,而是至迟开始于七七事变时。他于一九三八年写了一篇《<诗·卷耳、
去岁卢沟桥之变,岛夷肆虐,冯陵神州。……不自揣量,亦欲放下纸笔,执干戈以卫社稷,遂举十年中藏读之书、积存之稿而尽弃之。人事因循,载离寒暑,未遂从戎之愿,空怀报国之心,展转湘滇,仍碌碌于几案间,良足愧也。
自然,怎么样才能真正“卫社稷”,当时只是埋头书本的丁梧梓是不甚了解的,结果落得“空怀报国之心”而已。那几句话,不仅是自愧,其中包含多少酸辛。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他喜欢听钱玄同先生的“音韵沿革”和《说文解字》两门选修课。他是玄同先生的得意学生。他熟于《说文》,又于残本《切韵》、《广韵》以及历代韵书、字书有研究。他写的毕业论文,玄同先生给他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足见他于古人所谓“小学”功力之深。他又长于“经学”,于《诗经》用力尤深,好几篇关于《诗经》的训诂论文,结论都凿切不移。关于他的治学方法,可以说出下列几点。
第一,能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重庆有个北碚,碚字读培,还是读倍,不见于各种字书。不少人也不愿意探讨这个问题的。一则管它读阳平声或者去声,无关宏旨。二则古今字书都没收这个字,在古今若干万部书中去寻觅这个字的音读,实在太费劲了。梧梓不这样看待。我不晓得他查了多少书,他却肯定以“碚”为地名的,不止北碚,更有著名的宜昌虾蟆碚、荆门十二碚,于是乎遍考两宋人诗文集和与此有关的书,用各书异体字作“背”,苏轼、苏辙兄弟唱和诗都有“碚”字,依诗的格律,应读去声。另外还用了若干宋人材料作论证。真是狮子搏兔,用尽全力。古今字书所没有的字,今天《现代汉语词典》却有了,说:“碚,bèi地名用字:北碚(在四川。”连注音短短十一个字,得来好不容易!读者试翻阅《“碚”字音读答问》,便足以知道了。山西省南部有个
第二,他每为一文,一定先把有关资料搜集得十分完备。引用各书,必参考不同版本。如果引用“经书”,甚至还参考汉石经残字,如《释否定词“弗”“不”》(载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引用《尚书·盘庚中》“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便引《隶释》所载《汉石经》“弗”作“不”。又如《广韵》入声“物”韵“弗”纽内有“不”字,并注云,与“弗”同。梧梓考之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故宫博物院所藏王仁胸《刊缪补缺切韵》和唐写本《唐韵》,“物”韵内都没有“不”字,便断定今本《广韵·物韵》里的“不”字是宋代人所增加。这样细密而认真,一直是他治学和工作的负责精神。他的论文所引用的资料是无懈可击的。
第三,他每为一文,不但收集正面例证,更重视反面例证,也列举和他论点不相涉的有关例证。总之,前后左右每个方面都考虑周到。拿《论<诗经>中的“何”“曷”“胡”》(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一文而论,某些用法,只见于《诗经》,《尚书》却和《诗经》有所不同。即在《诗经》中,也有不同用法,梧梓也举了出来;甚至《易·损·卦辞》只有一条不符合他的论点的例句,他也举出来。再举《诗经“式”字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一文论,他从“式”字每与“无”字对言,“式”又与“虽”字对言,审其辞气,断定“式”是“应当”之义。复从“式”字说到“职”字,“职”和“式”古音相近,《诗经》“职”字也有和“无”对言的,因此,“职”也和“式”一样外,可以解作“应当”。除此之,《诗经》中还有难以解释的“式”字,他都一一列举出来,好使其他学人继续研究。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实足以为今日治学者的楷模。
第四,他每为一文,不但不抹煞前人的成就,就是同时人的帮助,他一定也注明出来,从不掠美。譬如《<诗经>“式”字说》,曾引朱熹《诗集传》,然后说:“朱因《诗》之上句言‘虽,故增‘亦当二字于下句以足其义,初非以‘当解‘式,而适符‘式字之本旨,妙得诗人之语意矣。”朱熹仅仅偶然得诗人之语意,他也给以说明。又如《<诗·卷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