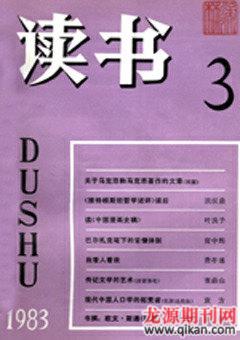怀克异
王维玲
李克异同志逝世整整三周年了。三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总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是不幸的,却是令人敬佩的。在他生命的航程上,智慧之光,总是闪闪发亮;生命之火,总是燃烧不,息。克异就是靠坚强和自信,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压力,挺过来的。即使在最不幸的日子里,他也坚信祖国大地必然会芳草常青,春光融融。
不管他自己的命运有多么不幸,克异对党的伟大,始终坚信不移。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归心似箭》和《杨靖宇》,就是最好的佐证。
克异和人民,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人民,是心连心的。他常说:“人民是不朽的,永远要歌颂他们!”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最初的题名就叫《不朽的人民》。
对党的信赖和对人民的深爱,支持着克异,使他忍受住了林彪、“四人帮”和极左路线强加给他的一切灾难。
克异是在三中全会的精神照耀下新生的。
一九七八年六月,在中共广东省委吴南生同志和宣传部的支持和关注下,克异应中国青年出版社之邀来京写作。克异是个病人,妻子姚绵恰被影协借调,一儿一女年纪又小,这一家人是分不开的,于是他们四口便都住进我社。尽管我们给克异提供的是一间最大的写作室,但也仅有十来平方米,我怀着十分的歉意,向克异解释这一切。出乎我的意料,克异对这间写作室却很满意,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还特意买了一盆绿意葱葱的花,摆在窗口,显得这间小房格外的有生气。他告诉我,这条件已经是很好了。说这话时,他那双诚实、憨厚的眼睛里充满了激动,“你知道,我过去的住宿条件吗?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住房前的甬道里,堆满了杂物,出出进进都不方便,对面是集体厨房,天一亮,鸡鸣鸭叫,烟薰火燎,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我每天都要在晚上十时以后,等左邻右舍、妻子儿女都睡下,才能开始写作。”克异告诉我,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中,写出了《历史的回声》的第一部,并且构思了第二部,翻译了巴尔扎克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农民》。显示了一个革命者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毅力!
《历史的回声》是克异计划要写的一部多部头的长篇小说。以一八九一年沙俄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为背景,揭露和控诉了沙俄帝国主义对我东北人民实行欺骗和奴役、镇压和屠杀的侵略罪行。看过第一部初稿,我们已满怀信心和希望。记得克异听了我们的意见后,很兴奋,跟着他就干劲十足地投入了第一部的修改。结构虽有所调整变动,人物虽有所增补加强……但这一切,全都在克异的意料之中,他早已胸有成竹。当时,他着急的不是文思不能泉涌、文笔不能酣畅,而是时间紧迫!他有那么多宏深壮丽的生活要写,有那么多气势磅礴的场面要构思,有那么多有姿有彩的人物要描绘!时间对于一个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人民作家来说,实在太宝贵了!
就这样,克异不停地写,不停地想,经过半年的努力,又一次在他的修改稿中,再现了历史的烟尘,人民的风貌;再现了家乡的风土人情,山川草木;再现了沙俄的嘴脸和暴徒的眉眼……小说逼真但不原始,丰富但不缭乱,复杂但不纷繁,细致入微但不支离破碎,气魄之宏大,境界之辽阔,比预料的更令人满意。这固然与克异倾注了大量心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克异有着丰富的生活积累。他青年时代历尽坎坷,以后又目睹东北人民沦亡之苦,亡国之恨,特别是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熟悉和了解,给他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生活素材,使他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
对克异,我并不能说是非常熟悉的,但我们很知心,特别是他的为人和才华,使我对他钦敬。克异来京后,考虑到他一家四口都要学习和写作,因此,我们除了给克异准备了一张特大号的写字台外,还放了一张两屉桌,专供他的儿女学习用。但我常常发现,克异不是坐在软椅上,舒舒展展地伏案写作,而是局缩在床头,利用书桌的一角,不停地写,那样子叫人看了很不舒服。是不是因为房子太小?还是桌子不够用?一次我问起了他,克异露出了憨厚难言的神色,温和地说道:“我不习惯!”说完,他怕我误会才告诉我,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伏案写作了。在广州时,他是坐在藤椅上,垫着一块木板写作的。住院期间,他在胸前放上一块木板,坐在病床上写……来北京以后,完全换了一个天地,安静的写作环境,舒舒服服的写作条件,思想可以自由骋驰,时间可以自由支配,食住不要自己去操心,但长期形成的习惯,却不能一下子就适应。“我那么坐着写,写不出来呀!”我听了一阵心酸,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克异却完全没有觉察到,他兴致勃勃地说:“我的黄金时代,来得迟了一点,但还不算太晚,我要用三年时间,把《历史的回声》四部写完。”说这话时,那刚毅的表情,激动的神色,至今历历在目。克异对自己的才华一贯是估计不足的,但对他的体质又估计得过高。他毕竟太虚弱了,来京半年,只因为一次平常的感冒,便哮喘加剧,高烧不退,最后被送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也没有停止构思和写作,床头柜的里里外外,床上枕下,放满了书籍、稿纸和手稿,他又象过去住院时那样,打吊针时构思小说,打完吊针便伏在病床上写小说,医生护士只能被他感动,却无法说服他。
克异对自己的健康,从来是马马虎虎的,但他对别人却关心倍至。他认识一位老中医,知道我患有胆石症,几次动员我去,还给我讲了这位神医的一些故事,以致使我十分动心,我们相约在他给《收获》的稿子全部寄出后就去,谁能想到,他竟在几日之后脑干出血突然猝死,想起这件事,我就无比悲恸。
我和克异同志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他给我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呢?这是因为他的诚实和真挚,让人一接触就感到可亲可近,他总是诚心诚意地了解别人的艰难、困苦和需求,从而尽力去帮助。他热情而实在,没有一丝虚假和客套,但同时又有着鲜明的是非爱憎;他有着赤子一般的忠诚、和善和忍让精神,但从不随意滥用自己的感情。这一切不仅反映在亲人之间和同志之间的关系上,同样也反映在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和小说里,他把美学的感情和道德的感情,融成一体。
克异逝世的前两天,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五月二十五日的中午,我在大门口碰到他,他举着刚刚买来的茶叶,一脸笑容,对我说:“一块钱一两的,你不尝尝!”他刚理了发,神采奕奕,看得出当时他的心境是非常好的。晚上下班时,我又在院内羽毛球场上碰到他,他跑过来,一脸激动,“我刚接过电话,约我去谈平反问题,要把过去的档案拿给我看,还真有个结论,要当着我的面烧毁。”说这话时,他没有愤恨和不满,充满了感激之情,只是在谈起那份“结论”的时候,在那双诚实的眼睛里,闪出一丝迷茫的神色。过后我才知道,就是这个没有和本人见过面的“结论”,在已流逝的岁月中,使克异的才华倍受挫伤。
当时,我知道《收获》正催他的稿子,我怕他精力分散,影响小说修改的进度,便说:“先不忙,二十年的时间都过去了,何在乎这几天,忙过这一阵再去吧!”克异点点头,表现出一种知心的赞许。
第二天上午工间操休息时,我又在报刊资料室碰上克异,他微红的脸色,显得精神格外的饱满。我说:“克异,你的气色真好!”他笑着说:“怎能不好,昨天接到《收获》的电报,刚才又打来长途电话,函电交加!他们要发表,你们要出版,电影(指《归心似箭》)要去看样片,对我来说,这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我完全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是啊!克异的电影剧本被压了十多年,他的长篇小说从酝酿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现在政治上很快就要彻底平反,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他在事业上的宿愿,也都相继要实现了,这如何能不叫他激动、兴奋!
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天下午四时左右,姚雪垠同志当时的助手,给克异去传呼电话,才发现他已不省人事。我得知后赶忙跑上小楼,推开克异的房门,立时呆了,傻了。克异背靠着墙,斜坐在床上,脸色蜡黄,没一点血色,他的头深深低下,口边吐出的白沫,早已成为一片白迹,双腿搭拉在床下……看来他自知不适,想躺下休息,刚把笔放下,还没有来得及躺下,就过去了。我赶忙把同志们呼唤来,轻轻的把克异放平,把双腿抱上床去,我把手放在他的腕上,已经没有一点脉搏了,鼻口之间,也没有一丝气息。几分钟后,急救站的医生来了,方知克异已经死去多时,但我们不死心,苦苦哀求,定要他们抢救,医护人员连连打了几针,没有任何反应,立即决定,送往医院抢救。到医院时,已经完全无望了。
几小时前,克异还有说有笑;几小时后,他竟然和我们永诀了。疑真疑梦,不知如何适应。克异走得太匆忙,太急迫了,无论是他的亲人,还是他的挚友,都对他的早去感到茫然!
克异逝世整整三年了。这三年,他写的电影剧本《归心似箭》被拍成影片放映后,赢得了社会上的好评;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也已出版,引起了文学界、评论界的重视;克异另一个电影文学剧本《杨靖宇》已发表,可望拍摄。未足花甲人先去,回声阵阵寄衷情。对克异来说,生命之路是太短了!他无疑是一个早逝的作家;但他走过的艺术之路和留在人世间的艺术成果,却有很强的生命力,会长留人间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为纪念克异逝世三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