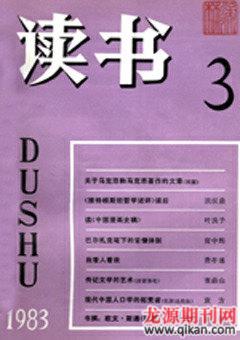辩解的辩解
〔日〕竹内实
几个月以前,已经忘记是谁,有一个朋友见了我就说:看了最近到的《读书》杂志没有?他说那里有一篇文章讲到我。我马上到所里办公室负责收纳、登记杂志工作的一角去问,拿到了《读书》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那时我心里是有内疚的。在此地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们里,对于《读书》杂志的评价很好,我也曾经听了人家的推荐订了一段时间。但,我的书太多,在研究室里放不下来了,勉强放下来也不好整理。因此,从今年开始,尽量少订杂志,也采取了取消已经订好了的蛮横手段。《读书》也是被取消之一。拿到了它,难免有再会自已多少违背过诺言的友人之感。
果然有一篇提到我的文章。是何为先生的《在北海道的文学交流》。是的,正如这题目所示,我跟何为先生在北海道见过面。还有韶华先生、陈喜儒先生;陈先生当翻译帮我们的忙。我已经拜读过韶华先生在《鸭绿江》杂志上连载的《北海道纪行》;是此地的一个订这家杂志的朋友复印后送给我看的。
读完了何为先生的文章之后,正如读韶华先生的文章时一样,我心里涌现出我们在北海道新闻社的一间客厅里见面、谈话的情景,再一次浸沉在当时的愉快的、融洽的、而对我来说是得到许多教益的气氛中。我觉得: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由现代中国的作家来描绘,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而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事。两位先生笔调都没有浮夸。但我多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还是过奖了。
在此地有一位外国籍(也不是中国籍)的年轻朋友,有一天开完所里的讨论会之后,在我研究室里一面休息,一面聊天。我不大喜欢拧开天花板的电灯,只拧开书桌上的比较小的电灯。我们喝一点点威士忌。彼此的面孔在不太黑也不太亮的光线中,有时看见有时消失,有点象英国童话里的猫的笑脸。
这位朋友是《读书》杂志的热烈的爱读者,碰巧他手里拿着一本。谈话之中,他提及了何为先生的文章,问我读了没有。我说:我读了,其中有一句记错了我的话。这个朋友就劝我投稿。
我指的是何为先生所记录的我的发言:“叶圣陶先生文字平易,译成日语很方便”。
这与我平常的看法不一致了。我的看法是:叶圣陶先生文字平易,但要译成日语就很难。
我在当时讲的,也许如何为先生所记的那样。但也许我的口音不清楚,或者说明不够,被何为先生了解为他所记录的那样(这就证明:我觉得何为先生对我的中文有所过奖这个感觉是对的)。
我认为:叶圣陶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文字)是地道的白话文、地道的中文,平易、素朴,但每个字、每个词富有实在的内容,想要更换别的字、词也不可能。想把它译成日文,在日文里找相当于它的日文字、日文词,难了。而把这些字、词组织成象叶先生的文章所具有的调子,就更难了。
人们也许会怪我:难道除了叶圣陶以外,其他中国作家都没有写白话文?用的不是中文?不平易?我承认这反问是有道理的。但,我还是要固执己见。
我这个固定观念在三十年以前就有。
那时中国出版一套丛书,叫《文学初步读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知道总共出版了多少种,每一种都很薄,三十页左右,可以塞进西装口袋那么大。其中一种是《寒假的一天》,叶圣陶著,费声福插图。
偏巧今天有小小的空闲,整理平常不大照顾的研究室的书架,发现有一捆书就是这套丛书;一共有三十九种。都是一九五三年左右出版的。
那个时候,我当了一家中文讲习会的讲师。教入门、初步还可以,但学员们上了中级,我这个讲师就很吃力,因为没有相当的教材。正好碰上了这套丛书,发现了《寒假的一天》。文字平易,内容有思想性,也有故事性。我用它来上课,因而书里面还保留着我加的注音字母和四声的符号。
我还记得:我当时感觉到这里面的许多字、词,难翻。
比方,开头的一页里就有:
“院子里阴沈沈的发白。”
这样的风景我也见过,但怎么翻?
“草草地穿著停当,我们两个开了后门,探出头去。”
在日文里找得出“停当”这样干脆利落的词?
我认为中文文章里有一批字、词很有中国香气、中国味道,如果译成日文(姑且不提日文以外)它就消失。当然,当时我的中文水平比现在还低,如果现在有相当的时间也许还可以勉强译出。但是,当时我头脑里所发生的上面的看法一直到如今还不变。并且我认为:叶圣陶先生的文章屹立在中国文坛里的理由之一就在这里。所以我喜欢它。有这样的文章,才给开始学中文的外国人带来一种学中文的甜蜜感。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除了叶圣陶先生以外的中国的作家的文章没有应有的中国香气、中国味道;也不是说:过去的日译本在翻译上有毛病;我只是把三十年以来的幼稚的看法,在北海道见到中国作家喜出望外之余,偶然、冒昧的吐露出来而已;而它的后果就是这个辩解。
也许我已经是一个“遗老”,即语言上的“遗老”,所以这样固执。但,这样说,又有语病了:把叶圣陶先生划成遗老成份了。我这里讲的,并不是那个意思。
这样,我终于作了这篇《辩解的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