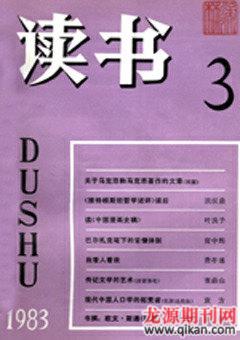读志一议
陈香白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司马光誉之为“博物之书”,章学诚称它系“一方之全书”。
读志,人生一乐也!当你打开了本地区的史志,其建置、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古迹、物产、风俗、金石、艺文等等,无不了如指掌;特别是“人物”一项,最能引起兴味,读来颇感亲切。但有时也会出现不满足的情绪,而正是由于有这种情绪,便引来一系列的思考。
假期得暇,遂着手整理潮州明代解元的行藏录。先翻光绪《海阳县志》,卷二十有“坊表”,其中之“圣域坊”建于清代,首列饶平盛端明……。再翻乾隆《潮州府志》,卷八有“坊表”,其中之“六贤坊”也列盛端明之名;但卷之二十八至三十的“人物”部,却找不到盛氏传;卷二十六的“选举表·上”虽有载,甚简,只介绍他是弘治十一年解元,弘治十五年进士,下加附注云:“饶平人,选庶吉士,累官礼部尚书,谥荣简。因党陶仲文,追谥 、削职。详《明史》。”我只好按图索骥,才查出《明史》将盛氏归入列传第一百九十五“佞幸”类!所载也略:“端明,饶平人。举进士,历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粮储,劾罢,家居十年。自言通晓药石,服之可长生,由陶仲文以进,严嵩也左右之,遂召为礼部右侍郎。寻拜工部尚书,改礼部,加太子少保,皆与可学并命。二人但食禄不治事,供奉药物而已。端明颇负才名,晚由他途进,士论耻之。端明内不自安,引去,卒于家。赐祭葬,谥荣简。隆庆初,二人皆视官夺谥。”《明史》编者还在本传前评曰:“至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之属,皆起家甲科,致位通显,乃以秘术干荣,为世戮笑,此亦佞幸之尤者!”他们究竟用什么“秘术”去拍马屁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秘方见体”条有载而不详,直到查到“进药”条,方知所谓“秘术”,淫术也!盛端明此“贤”的庐山真面目至此暴露无遗。但乾隆《潮州府志》对盛氏的所作所为却避而不谈;顺治《潮州府志》则更离奇,所载全属谀词。这是为什么?原来地方志记载人物时往往“有褒无贬”,未能全面地反映出某人一生的事实。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评曰:“州县志,下为谱牒传记持平,上为部府征信。”钱大昕也说:“方志有褒无贬,是忠厚之意;但凭公论所在,不可变黑为白。”他还在《跋新安志》中说:“桑梓之敬,自不能已。袁文长《四明志》,于史同叔,但叙其历官,而云‘事具国史。以此同意汪(即汪廷俊,世称奸人)尚,有善可称,史则其恶益著,故文稍异尔。”
紧接的思考又来了:“有褒无贬”果真是历代撰修方志人物,传的定则么?
唐玄宗年间,集贤院学士徐坚等奉敕撰写《初学记》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的“史传第二”便首次提出了“方志直文”的理论,他主张编写方志应该象司马迁著《史记》那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并引《魏书》“王肃对明帝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等语以证之。显然,历代文人修志,大多数都不能做到“方志直文”,但毕竟也有些例外。明代陕西康海修《武功县志》,全书三卷,分七编;官师则善恶并著,以寓劝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乡国之史,莫良于此”,“后来志乘,多以康氏为宗。”顺治年间,潮州知府吴颖修《潮州府志》共十二卷,第四卷特别附入“迸放诸奸”,认为贬潮的人并非全是贤人,其中也有“奸恶贯盈”之辈,如宋浑、黄潜善、徐秉哲、梁成大等四人;同卷又有“贪酷诸吏”条,除序言外,还逐一列举出知府黄
编纂地方志的工作已在全国各地区蓬勃展开,有鉴于此,谨就上述读地方志人物传之所感,愿向修志诸君进数言,聊充芹献:
一、由于是“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以一方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张恕同治《鄞县志序》),故一般都是当地人修当地志,其中难免涉及很多“乡贤名宦”,如此,则切莫以感情代替事实,一味地曲意奉承。岂不闻“夸饰则辗转迁就,欲掠古人之美,反致生后人之疑;攀附则请托夤缘,欲传先人之名,反致招同人之谤。二者皆为修志所深忌”(光绪联元《海阳县志序》)!
二、过去修地方志,其中有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修一统志(国史)准备材料;现在修地方志,何妨来个“逆过程”,参考国史对于有关人物的评价,以补充地方志之不足。
三、历代笔记文学,多有涉及人物遗闻逸事(如上述《万历野获编》载盛端明事)者,应旁搜博采,充分利用,以之丰富地方志人物传内容。
四、既勿曲意奉承,也忌任意贬斥。爱屋及乌,未必明智;因人废言,怎推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