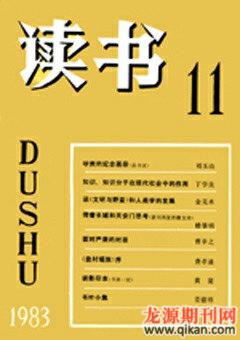朱光潜与尼采
程代熙
读《悲剧心理学》
一
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悲剧心理学》是他早年撰写的与心理学有关的三部美学论著,而《悲剧心理学》又是他美学思想的发端。他在给《悲剧心理学》写的《中译本自序》里说:“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在美学界,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关系,一般地说是清楚的,当然存在着不少误解与浮词。至于他与尼采的关系,就笔者所知,则鲜有人谈及。要了解尼采对朱光潜的影响,似有必要谈谈尼采对中国思想界,特别是文学界的影响。
乐黛云同志在一九八○年第三期《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她在文章里把尼采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划分为四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到“五四”前夕,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从王国维到早期的鲁迅、陈独秀和蔡元培都把尼采视为“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的“才士”,是“尊重个人意志的”“大艺术家”。“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前夕,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尼采的一些重要著述开始介绍了过来,如田汉介绍了尼采的美学专著《悲剧之发生》(即《悲剧的诞生》),此外,郭沫若和沈雁冰分别翻译了《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片断,鲁迅翻译了《如是说》的序言。这时尼采在中国文学界仍然主要是一个思想革新者和思想解放者的形象。一九二五年大革命以后到四十年代以前,是第三阶段。乐黛云同志在文章里说,大革命以后,“由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广大工农群众和很多知识分子都已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的革命道路,纷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尼采的影响遂逐渐减弱以至消亡。”并引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高长虹等人的批评为例。四十年代是第四个阶段。战国策派把尼采奉为“维护反动统治,鼓吹战争,镇压群众”的“绝对偶像”。
乐黛云同志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力作,她具体地分析了尼采对中国文艺界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及其成因。我只是对她说自一九二五年以后(直到四十年代以前),“尼采的影响遂逐渐减弱以至消亡”这一断语有些不同看法。旁的不论,倘以鲁迅来说,就不是如此。例如,鲁迅在一九三○年发表在《萌芽月刊》上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写道:“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按:指郭沫若未译完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笔者),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这正是鲁迅思想上最成熟和最光辉的时期,但他并不曾忘却尼采,他还在大声疾呼要翻译出版尼采的著作。此外,老出版家赵家璧同志在《鲁迅·梵澄·尼采》一文里根据他亲身的经历给我们介绍了鲁迅向良友图书公司推荐出版梵澄(即徐诗荃,现名徐梵澄)翻译的《尼采自传》的详情。鲁迅认为“先让我国读者从中了解尼采的生平和著作,也是一件有益的事”。《尼采自传》正是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下,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由良友图书公司付梓问世。这之后不久,鲁迅还向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推荐徐诗荃译的尼采的重要著作《苏鲁支如此说》(即《察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赵家璧同志认为“鲁迅先生直到晚年,对尼采还是深有感情的”。
至于人们乐于引用的、用以证明鲁迅已经完全否弃了尼采思想影响的那段话,是在他谈到狂飚社成员向培良的小说《我离开十字街头》时讲的:“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飚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鲁迅在这里确乎批评(说批判也行)了尼采,但他批评的一是尼采那种坐等天上掉下一个“超人”来,而自己不采取革命行动的思想;二是安于空虚;三是虚无主义。鲁迅肯定的是尼采那种“纵忤时人不惧”的反抗精神,而不是他的“不行动主义”。对于这一点,鲁迅不是在一九三五年才开始批评,而是早在“五四”运动那一年,他就对尼采发出类似这样的烦言了。
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前辈他们接受的主要是尼采的哲学思想;战国策派所尊奉的应该说也主要是尼采的哲学思想。二者不同的是,鲁迅等人是企图借尼采敢于破坏旧文化、敢于反对一切权威的思想来反抗当时旧中国的一切社会黑暗势力;而战国策派则不然。
二
朱光潜接受尼采的思想影响较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要晚得多。从他的著作来看,他是在一九二五年(即大革命那一年)留学欧洲之后,才开始接受尼采的影响的。他先后在英法留学八年。一九二七年在爱丁堡大学宣读的论文《论悲剧的快感》,就是他一九三三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的前身。旅欧期间,对朱光潜文艺思想,甚至在他的人生观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尼采的思想,主要还不是尼采思想的昂扬向上、要求奋发的一面,而是他那悲观、失望的一面。
英国意识流文学的始祖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谈到一九一四年左右和一九二五年左右步入文坛的两代英国作家说,这两代作家大都出身中产阶级,但却受到了高等教育,这把他们抬高到普通人民之上。他们就象生活在一座高高的塔楼上一样远离了自己的时代和人民。他们原以为塔里最安全。但未久塔身便开始倾斜,而且倾斜到了危险的程度,他们于是感到自身不安全了。他们先是感到自怜,然后又对引起他们不安的那个社会感到愤恨。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倾斜到左边去了。美国学者杜博妮女士在她的论文《朱光潜论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美学和社会背景》一文里,引用了伍尔芙的这番话之后写道:这种情况也大致适用于同时期的中国文坛,“从一九二五年开始,大多数〔中国〕青年作家发现他们越来越向左移动,他们的作品中也掺和着不安、自怜和愤恨。”“但是虽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发生了动摇中国社会基础的一次又一次的剧烈震动,朱光潜却没有象其他人一样向左倾斜,而是向古老的传统倾斜。”杜博妮认为,朱光潜那时的政治态度是中间偏右。朱光潜表示她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虽然相当尖锐。
形成朱光潜的艺术观、人生观的因素很多,但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尼采的思想,特别是他的美学思想。
三
尼采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源于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叫巴克斯,他是天帝宙斯的儿子,其母是忒拜王的女儿,早夭。巴克斯是在宙斯大腿里长大的。他是葡萄的第一个培植者,也是酿制葡萄酒的第一个发明家。这就是他成为酒神的由来。酒神有很多信徒,其中多数是女人。他们成天以酒取乐,边喝边舞。舞蹈和抒情诗就起源于酒神的载歌载舞。日神阿波罗,也是天帝宙斯和托勒所生的儿子。据希腊神话传说,阿波罗是从赫利俄斯神手中夺取了太阳之后成为奥林普斯山上的太阳神,即光明之神的。他是音乐和诗歌之神。
尼采就用酒神和日神来象征人类的两种基本心理经验。
酒神象征的人类的心理经验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完全被打破,人重新与自然合为一体,融入到那神秘的原始时代的统一中去。他如醉如痴,狂歌狂舞,尽情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纵情享受欢乐的喜悦。人生犹如一场狂舞欢歌的筵席。日神象征的人类的心理经验则与此相反。如果说酒神是在任意驱使人类的情感,而日神则使人注重理性,讲求节度。具有日神精神的人,好比是一位怡静的哲学家,他透过静观梦幻世界的美丽的外衣,寻求一种强烈而又平静的乐趣。他在一旁静观人世的虚妄、命运的机诈,总之,五光十色的迷人的世俗生活图画,不仅给他快乐,而且使他感到人生是“一场梦”,他说他要“继续做梦”!尼采据此把日神又称为梦神,日神的心理经验即梦境;酒神即醉神,它代表的人类的心理经验是一种醉境。
这两种基本的心理经验,也就是两种心理境界便产生出两种不同的艺术。酒神精神主要表现于音乐。尼采说:“酒神精神的音乐家勿须借助画面,本身就是那原始痛苦和那痛苦的原始回响”。酒神的手舞足蹈产生了音乐,随着音乐而诞生的就是抒情诗。尼采说抒情诗乃是“音乐在图画和表象中射出的光辉”。民歌是抒情诗的原始形式,因此,尼采说,凡是民歌兴盛的时代,都是崇奉酒神的奔放不羁的时代。“浮动在甜蜜的快感之中”的日神形象,则主要体现为造形艺术(绘画、雕塑)和史诗。如果说酒神的音乐艺术“不是现象的复制,而是意志本身的直接写照”,那末日神的艺术所追求的则是“个性原则”的天才化身。雅典神庙上雕刻的天神形象和荷马两大史诗里所描绘的那些英雄形象,就是这种日神艺术的最好的说明。
尼采说,在酒神的音乐艺术和日神的造形艺术之间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因为前者是主观的艺术,后者是客观的艺术。这鸿沟的两壁虽然十分陡峭,但仍有可以互通信息,甚至还有使鸿沟两边得以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条条小道。这是因为“在每一种艺术的上升之中,我们首先特别要求克服主观性”;“只要真正是艺术的作品,不管是多么小的作品,没有一点客观化,没有纯粹与利害无关的静观,都是不可想象的”。尼采的这番话是讲,举凡艺术品,无不具有克服主观性的要求,也无不表现出某种客观的观照。例如,音乐是意志或酒神精神的客观化,而主观艺术的抒情诗则可以视为音乐的客观化,即把音乐转化为清晰可见的观念和形象。
朱光潜在介绍了尼采的关于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的思想后,他写了一段总结性的文字。他说:
“尼采用审美的解释来代替对人世的道德的解释。现实是痛苦的,但它的外表又是迷人的。不要到现实世界里去寻找正义和幸福,因为你永远也找不到;但是,如果你象艺术家看待风景那样看待它,你就会发现它是美丽而崇高的。尼采的格言:‘从形象中得解救,就是这个意思。酒神艺术和日神艺术都是逃避的手段:酒神艺术沉浸在不断变动的旋涡之中以逃避存在的痛苦;日神艺术则凝视存在的形象以逃避变动的痛苦。”
这段概括是有相当见地的,它既是对尼采美学思想的解释,也是朱先生对尼采思想的理解。也正是这种理解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艺术观。但朱先生的这段文字只是概括了尼采美学思想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他未触及。
尼采固然崇奉的是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即醉境)艺术和日神(即梦境)艺术,但他看重的是酒神精神及与之相应的醉境境界。例如他说“酒神比起梦神来,就显然有所不同,它是永恒的本源(按:指意志——笔者)的艺术力量”。①尼采之所以注重酒神精神,他认为这是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它不安于静穆的观照,它要求行动,因为它本身就是意志的化身。尼采看到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下半期)德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特别是文化上(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的萎靡不振时特别强调道:“我们的文化如此衰落,一片荒凉景象,触目惊心,一旦接触到酒神的魔力,将突然发生变化!一阵狂飚扫荡着一切衰老、腐朽、残破、凋零的东西,把它们……卷到云霄。我们彷徨四顾,……只见下界突然升入金色的光辉里,这样丰茂青翠,这样生机勃勃,这样依依不舍。悲剧就端坐在生机蓬勃、苦乐兼并的情景之中,庄严肃穆,悠然神往;她在倾听一支遥远的哀歌,歌中唱到‘万有之母,她们的名字是幻想,意志,痛苦。”尼采甚至呼吁道:“朋友,同我一起信仰酒神的生涯”;“……放胆做个悲剧英雄吧。因为您必将得救,您得要追随酒神信徒的行列,从印度走到希腊!武装起来,准备作艰苦的斗争,但是您要信赖您的神灵的奇迹。”②
尼采的这种思想,不仅见于他的《悲剧的诞生》,也见于他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论》以及其他重要著述。对于他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主,张“掊物质张灵明,任个人排众数”,就据的是尼采的上述精神。法西斯分子则把尼采的这种思想作为他们强权政治的理论根据。尼采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和思想家,因此,说法西斯分子利用了尼采的上述思想,这是事实,至于说他“预示了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所作的垂死挣扎”,就显得根据不足了,尽管类似这样的说法已经成了一种口头禅。
四
尼采侧重的是酒神精神和酒神艺术,朱光潜侧重的却是日神精神和梦境艺术。具有日神精神的艺术家追求的是静观人生,怡情养性的境界。所以朱光潜倡导的艺术是不涉时事,独立自主。例如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里,他对人生就是采取一种超脱的态度。他说:“我无论站在台上或站在台下时,对于失败,对于罪孽,对于殃咎,都是用一副冷眼看待,都是用一个热心惊赞。”因为人生的目的就在于生活。对于生活中的悲剧喜剧,他都同样看待,也勿须去认真理会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区别。在《谈美》,即《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一书的《开场话》里,他进一步说道:“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③《谈美》著于一九三二年,时朱光潜还留学欧洲。这正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以及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挑起松沪战争之后不久,中国面临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这一切恰恰就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朱光潜对于酿成当时危急时局的那班“饱食暖衣高官厚禄”之辈是不满的。他也想变革这种不合理的现实生活,但由于尼采的日神精神对他影响甚深,只看重艺术性,而忽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所以他的变革办法是用艺术来净化人心和美化人心。这完全是天真的书生之见。这是朱光潜文艺思想,以致美学思想的核心内涵。
他说的净化人心和美化人心,就是指“超脱”而言。“超脱”能使人在忧愁和不如意之外看见蓝天,找到人生问题的和谐解决。他在《孟实文钞》里欣然写道:“我不敢说它对于旁人怎样,这种超世脱俗的态度对于我都是一种救星。它帮助我忘去许多痛苦,容忍许多人所不能容忍的人和事,并且给过我许多生命力,使我勤勤恳恳地做人。”
生活在尘世当中,又要想超然于它,这不仅是一种矛盾的想法,在绝对意义上讲,也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事实上,朱先生自己也难以做到这一点。
朱光潜在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上也始终把“超脱”视为艺术上的最高境界。但这并不是说他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追随者。相反,对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他倒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欣赏和执着地追求的是为人生而艺术。关于这,他在《谈美》一书里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文字。他写道:
“严格的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④
要获得人生的情趣,关键在于“超脱”,用超然和恬静的心灵来造化人生,也用这样的心灵来表现人生。朱光潜的“超脱”思想在艺术理论上的根据,就是心理学上的“距离说”。“距离说”是近代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朱光潜的“距离说”有两个主要的根源,一是立普司的“移情论”和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的“距离”概念。朱光潜不仅在《悲剧与人生的距离》和《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两篇文章里,还在《悲剧心理学》的第二章里专章讨论了“距离说”的重要性。我们这里就不具体来介绍了。
但是,必须在这里说明的是,由于他把“距离说”讲得过了头,走向了极端,就使他在艺术欣赏和审美活动中过分地注重形式,讲求形式。他批评说,浪漫主义艺术(或“理想主义”)的毛病在于“距离过度”,而自然主义艺术又往往“距离不足”。他的结论是:“艺术在本质上是形式主义的和反写实主义(按:即“反现实主义”——笔者)的。”而且还特别强调说,艺术中真正近代的进步的运动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近代形式主义。
由于这样,朱光潜在艺术欣赏和审美评价上过分重视古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西方艺术成就,对于西方近代和现代,尤其是当代的艺术作品是很少能进入他的视野的,即使他注意到了,也认为是无法与古代和文艺复兴相匹敌的。例如,他在《悲剧心理学》的第五章里写道:狄德罗、莱辛所大力提倡的“市民悲剧”,就少有获得高度成功的。“随着‘市民悲剧的兴起,真正的悲剧就从舞台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只是小说、问题剧和电视剧。巴尔扎克写了《高老头》,屠格涅夫写了《草原上的李尔王》,然而在莎士比亚旁边,这两个故事显得多么寒伧!”
尼采对朱光潜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以上,我们只是就一个方面,即尼采的日神精神和梦境艺术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影响作了一点简略的介绍。当然,这说的是解放前的情况。建国以来,朱光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是相当自觉和刻苦的,对于自己的解剖也是毫不留情的。他执笔编写的《西方美学史》,就是他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这部学术专著里,我们可以看到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确有了深刻的变化。看不到这种变化,或者忽视或者低估朱光潜美学思想上所达到的成就都是不正确的。
(《悲剧心理学》,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月版,0.80元)
①尼采:《悲剧的诞生》第二十五章。转引自伍蠡甫:《西方文论中的非理性主义》。
②尼采:《悲剧的诞生》第二十六章。转引自伍蠡甫:《西方文论中的非理性主义》。
③朱光潜:《谈美》,开明书店一九四七年第十五版,第2页。
④朱光潜:《谈美》,第127—128、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