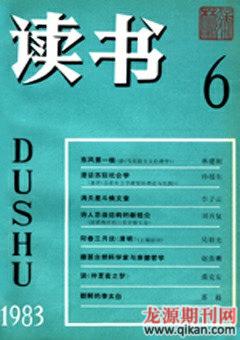维克多·塞加伦诗中的汉语典故
若埃尔·夏皮罗 冯国忠
维克多·塞加伦(Victor Segalen)是二十世纪被人忽略了的极富魅力的作家之一。对他作品的研究真正打开了通往有价值的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之门。塞加伦是最早把中国的语言文化巧妙而有意识地糅合到欧洲文学作品中去的西方作家之一。
有很多西方现代作家被人误以为懂得东方文化,并利用了对东方文化的这种了解。其实这些作家往往把读者引入歧途。他们的无知只是使西方意识中亚洲的形象歪曲得更厉害。保罗·克洛代(Paul Clau-del)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
克洛代的《东方的认识》(Connaissance de LEst)与其说是让人认识东方,不如说是认识克洛代自己。他的毛病出在用西方天主教徒的眼光去看东方。他用的词汇(安息日、亚伯拉罕的怀里、圣灵降临节、耶路撒冷、上帝、迦南)和他想深入认识的那种文明格格不入,因而使他无法达到认识东方的目的。
庞德对中国的妄解甚至更严重。庞德的谬误和许多不懂中文却奢谈中国的人一样,纯粹是假汉学。他的理论和翻译都来源于费诺洛萨(Ernest Fenollosa)的手稿。费诺洛萨自己谦逊地承认汉学知识有限〔不及李雅各(James Legge)这样的人〕。庞德却不理会这样的承认,并在他编定的费诺洛萨作品集中,公开批评费诺洛萨的谦逊。
由于庞德的不断影响,西方读者得到的是关于中国和中文的歪曲形象。在《阅读初步》(ABC of Reading)这本书里,他讨论了汉字的构成。他举红色的“红”字为例。“他(中国人)要给‘红字下定义。他怎样能在一幅不是用红颜色画的画里做到这一点呢?他(或者说他的祖先)就把表示玫瑰、铁锈、樱桃和火烈鸟这四样东西的图画文字的简体放在一起。”
庞德暴露出他对中文完全无知。“红”字是由糸(表示丝)和工(工作)两个部首合成的,其中根本没有什么“表示玫瑰、铁锈、樱桃和火烈鸟的图画文字的简体”。尤其明显的是,这些字并不属于那些包括所有表意符号的二百一十四个部首。
这是个相当严重的错误,因为庞德的东方诗论正是基于他对汉语的这种虚假认识,而且,大量西方读者竟然对他深信不疑。
庞德这些人因缺乏知识而提出的荒唐见解混淆了欧洲人对亚洲的看法。要揭露他们,就必须开展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同样,要鼓励象塞加伦这样真正深入到另一种文明的诗人,也必要进行这类研究。
遗憾的是,人们很少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塞加伦。也就是说,塞加伦以往用来补充他诗中法语意义的那些汉字,一直被人忽略。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分析《石碑集》中的三首诗,揭示故意加进诗中的汉语典故的意义,以说明塞加伦对汉字的倚重。
然而,在研究《石碑集》以前,我们必须了解亨利·布依埃(Henry Bouillier)教授对研究塞加伦所做的重要贡献。塞加伦从湮没无闻到广为人知,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亨利·布依埃对其诗作深邃的批评鉴赏。不过,布依埃提出的关于汉字的几个问题至今未获解决。我将通过解释塞加伦引用某些表意文字的方法和原因来试图对他作品的特定方面作一补充,从而着重说明《石碑集》的作者运用汉字的匠心。
运用中国文学典故最有趣的例子之一是那首题为《我的情人德行如水》的诗。
复水难收
“我的情人德行如水:明亮的微笑,流动的身姿,清澈的嗓音和滴沥的歌唱。
而有时——尽管我——眼睛里流动着火,她知道怎样颤抖着把火拨旺:把水泼在火红的炭上。
我的生机勃勃的水啊,溢了出来,全部复在了地上!
她滑动,她逃跑;——可我渴,我在后面追赶她。
我用手截断,陶醉地用双手掬着她,把她捧到唇边:
可我吞吃了一捧污泥。”
亨利·布依埃在他对《石碑集》的评论里写道:“尽管P.魏格尔(Wieger)在其《历史文献》和《民谣》里已做了不少研究,但我们仍有必要搞清塞加伦所引的这段轶事的出处。”而要达此目的,人们必须要有古汉语的基础。
“复水难收”——这条引语的意思是“泼在地上的水难以收回来”,或者比喻“事成定局,无法挽回”。《汉书》和《今古奇观》里都提到过这个典故。这是一个关于朱买臣的讽喻故事。朱买臣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竟至耽误卖柴,陷入了贫困。他的妻子不理解他,坚持要他放弃读书,去赚钱糊口。多次劝说无效后,她离他而去,另嫁他人。此后许多年,朱买臣仍自学不辍。在中国古代,如果一个人(甚至穷人)通过复杂艰深的考试,就可以获得高官。朱买臣后来考试中选,被皇帝授官太守。在朱驰驿赴任途中,他先前的妻子跪在他面前,乞求宽恕复婚。因此,朱买臣把水泼在衙前高高的石阶上,说,“如果泼水可复收,你我也可复合。不过,一个人不要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抱有幻想。”因此,“复水难收”这个典故也就传了下来。
塞加伦诗中的“情人”有着朱买臣泼在石阶上的水那样的“德行”。人们现在能够欣赏塞加伦把法语里预先感受到的情境和汉字的效果紧密相接的技巧了。“溢”出的水(代表那个男人对其情人的热恋)和变男人痛苦为女人痛苦(用惩罚的形式)的“复”字并列,从而使得这首诗具有讽刺意味。
《石碑集》中只有理解了汉字才能全面欣赏法文的另一首诗是《池》。它是《三首古谣曲》的第一首。
作咸池之池
“在这些池的圆圆的掌心里,溺着天的面庞:
我转动球体,把天仔细观察。
池,被十二乐音的兄弟般的回声所敲击:
我融化了确定这些乐音的十二钟。”
“动荡的池——翻转来的液体的天和乐钟,
让赏识我的才能的人
在强大、至上的天穹下回响。
为此,我将治下的赞歌命名为:池。”
在《石碑集》的序言中,塞加伦把汉字当作“象征游戏”。在《池》中,主要的“象征游戏是意为小湖或潭的“池”字。但当它和意为“全部”的“咸”字结合在一起时,就有了更多的比喻意味。
“咸池”指的是传说中的“黄帝”创造的歌(诗),因此,它们暗指的是中国音乐的神秘起源。人们在《通典》里也看到这两个字,只不过是黄帝被用作主语,即“黄帝作咸池”。
塞加伦虽然没有在他的著作完成稿中提到“黄帝”,但他在手稿里确实谈到了他(但他没有讨论这条引语和诗歌之间的确切关系)。
要理解《池》,就必须了解这首诗中提到的传说的起源。黄帝派他的部下伶伦去昆仑山西边的大夏砍竹管,因为从这些竹管上可得到基本的音高。伶伦根据黄帝的命令确定了乐音,并把这些音调和天堂之声进行了比较。这些“十二”节竹管被命名为“律”。它们也被称为“十二钟”。
人们可以看出塞加伦怎样巧妙地把表意文字的主题糅进了法语里(运用“池”和“咸池”的意思)。诗句“池,被十二乐音的兄弟般的回声所敲击,/我融化了确定这些乐音的十二钟”表明了塞加伦怎样运用了“池”和“咸池”二者的结合。在提及这个传说时,塞加伦重复了“十二”这一象征性的数字,同时利用表示液体的词(池,融化)使“池——咸池”这一主题更富流动感。
《石碑集》结尾部分的一首诗是《时刻》。亨利·布依埃曾讲过,“再也没有比《时刻》这首诗所依据的出处文字更简洁,情节更特别的了。”
然而,我们有必要了解这首诗所依据的出处,因为它是塞加伦受到东方影响的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很可能是在欧洲文学里第一次表明了一首法国诗歌怎样受益于一条汉语引文。
这条汉语引文采自老子的《道德经》的第二句。塞加伦本人把他的研究道家思想的有魅力的著作称之为“我思想上喜爱的哲学著述”。
“我忙把今天的所闻强加给你的表面——石火飞翔、可见的现实的面积;
我把所感到的(犹如内脏坠落时的紧束感)摊开在你的皮肤上——爽身的、潮湿的丝袍;
你的血管织成的波纹没有其他皱摺:为了使我在眼距之内看清,你不要后退;除了一面凹一面凸的必要空间之外,没有什么深度。
这样,被我弃置的我今天的所闻如此坦率,如此丰富,如此明了;它打量着我,用肩膀支持着我,永不疲倦。
我失去了隐藏的价值和秘密,而你却涂去了坚实的记忆——化石般坚硬的时刻、高傲的保卫者。
从这……这是什么……已经分化,分解,已被吸收,这已在我的深不可测的污泥中暗暗地发酵。”
“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说明了事物的矛盾性是道家思想的基础。塞加伦非常喜爱中国人运用矛盾的方式。因此,他在《石碑集》中也利用了矛盾。汉学里的这种对立精神包含在称作“阴阳”的哲学里。
在《时刻》这首诗里,塞加伦把道家的“名可名,非常名”和他本人在诗里表现的对矛盾的个人感受平列了起来。这里,关键的字(或者更为恰当地说“象征游戏”)是“名”。
当他说“我把它强加给你的表面——石火飞翔”时,“它”(直接宾语)指的是“名”。这第一行是和最后一行相对的。在最后一行里,“名”“已经分化,分解”。塞加伦有意选择了《道德经》的第二句,以满足他自己记述无法表达“常名”的写诗需要。通过解释老子的作品为自己的创作服务,塞加伦认为“名可名,非常名”包含有无法确切描述人们在创作“时刻”的感受的意味。
塞加伦试图用文学的形式(在道家思想的背景里)使这个正在逝去的“时刻”丧失活力,这是他的诗歌的基础。
塞加伦对汉字的运用既富诗意又很深刻。作为《石碑集》的作者,他打开了通往真正的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