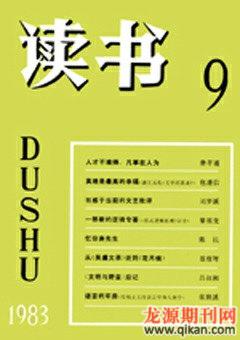引人入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
祁庆富
前些时候,我去拜访民族学界的老前辈林耀华先生。谈话间,他拿出新近出版的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利普斯所著《事物的起源》的中译本给我看。早在六十年代,林先生就向译者汪宁生同志推荐过这本书,现在已故的民族史学者傅乐焕先生还把自己珍藏的该书英文本赠与译者,鼓励他
一
本书的作者利普斯(JuliusE.Lips)生于德国的萨尔地区,曾长期在科隆大学担任人类学系主任和教授。一九三四年他应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士·鲍亚士(FranzBoas)的邀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他一方面在大学里教人类学,一方面受学术团体的委托,从事实地调查。他曾对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的印第安人进行过长期调查,发表过一系列著作。这本《事物的起源》,是他写的一本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性著作。
在我国,文化人类学至今似乎仍是一个冷僻的术语,不为人们所熟知。可是,在国外,尤其在西方,它却是一门影响颇大的重要学科。文化人类学做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欧美各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门科学的资料积累,却直可追溯到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时代。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在与异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发现了与自己大相径庭的异民族文化,并将这种文化记载于史籍之中。文化人类学的萌芽发端于对异民族文化的研究。在我国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著作中,就已不难发现这种萌芽状态中的文化人类学资料。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公元十五至十六世纪,世界范围的新航路被开辟。一四九二年,哥伦布航抵美洲“新大陆”。一五一九年至一五二二年,麦哲伦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这样,近代的地理发现打开了人类相互交往的视野。自此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对于世界各地,尤其是殖民地民族的文化了解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便应运而生。经过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的交通手段和信息传递方式使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使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相互交往越来越多,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相互接触、交往、冲突、反馈和影响也日益频繁。以全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也就更显得重要。正因如此,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里,文化人类学都是一门颇受重视的学科。
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世纪多的历史,但至今其学科名称仍不统一。在英文中,文化人类学写作CulturalAnthropol-ogy。这一概念与“民族学”(Ethnol-ogy)是一对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的术语。按照美国人的概念,文化人类学作为“人类学”(Anthropology)的分支,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以整个人类文化及其发生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包括民族学(Ethnology)、史前考古学(Prehistoricarchaeology)和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可是在英国,却习惯于用民族学(Ethnology)的概念取代人类学(Anthropology),这样,文化人类学(CulcuralAnthropology)又成为民族学的分支。
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各国,对“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所赋予的含义是不一致的。尽管如此,“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内涵仍然是大同小异,就主要方面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都差不多。所以,不少学者主张二者是同一学科的不同术语,在西方各国及日本,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的概念仍是并行使用的。
二
利普斯这本《事物的起源》共十五章,书中征引了大量民族志和考古学材料,从人类的衣食住行,到生老病死,乃至于商品交换、信息传递,探索了各种生产活动、日用器具、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的起源问题。内容涉及到远古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概而言之,可以说是一本简明的远古人类文化史。因此该书原来的副标题,就叫做《文化人类史》。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具有独自特点的文化。并且,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又都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探索这种历史的连续性,就是追溯世界上各种事物的起源。即使是处在原始时代的人,也在他们的口碑传说中保留着历史的记忆。进入文化社会以后,人们探索历史连续性的欲望就表现得越来越强烈,对于世上任何事物总想刨根问底,总爱问一个从何而来?何时开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种溯本求源的愿望可以在这本《事物的起源》中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作者利普斯在本书中提供了大量一般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材料。由于作者对于一般公众的心理进行过认真研究,所以他选择的“新鲜材料”并不是冷僻的,涉及的问题,亦是一般人所感兴趣的。例如,任何人都有一个“家”。那么,最古老的人类之“家”是什么样子?本书第一章《家和家具》向读者描述了远古时代的“洞穴”之家,塔斯马尼亚人的“风篱”之家,爱斯基摩人的“雪屋”之家,印第安人及其他许多民族的“帐篷”之家……。当你置身在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群中,再去体会一下“家”的演变史,不能不对人类为自身生存而进行过的漫长而艰巨的创造性劳动而感慨万分!
作者在序言中还写道:“写这本书是为有助于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努力增进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合作。”在人类短暂的文明发达史中,已创造了无比丰富的灿烂文化。当今的世界,高超的通讯手段已远远胜过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航天飞机遨游太空的事实使嫦娥奔月的传说大为逊色。然而,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文化却是几千年来全人类共同文化的结晶。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追溯出现代文明的最古老的起源。本书第三章题为《最早的“机器人”》,作者以丰富的民族学材料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原始类型的“捕机”:北美塔尔坦印第安人猎取熊、狼和水獭的重力捕机,拉布拉多的印第安人网套捕机,喀麦隆的钉轮捕机,西非捉老鼠的和带有鱼笼的跳柱捕机……。看到这些材料,任何研究机械学和运动学的工程师,都不会否认这些捕机上的扳动装置是现代技术中占有卓越地位的继动机械结构的最早应用。本书第九章《从信号到报纸》向我们介绍了纷然杂陈的原始人类信息传递方式。在这一章中还列举了各种原始的图画文字,给读者展现了一幅幅古代无名圣者的杰作。不能不使人感到,现代人类的高度文明既不是仁慈的上帝所赋予,也不是某个超人的天才所独创,它是整个人类文化乳汁长期哺育的结果。
我们的世界,是多民族组成的人类社会。每一个民族,不管其肤色如何,不管其历史长短,不管其文化发展快慢,都在历史的进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民族文化,都为我们的地球增辉生色。这本书中,广泛地收罗了世界上许多民族,特别是那些社会发展进程还处在后进阶段上的民族的创造与发明。作者虽然是一位西方人类学家,但他较少种族偏见和民族歧视,比较公正地指出,世界上各民族都对人类文化作出过贡献,即使最原始的民族也有自己的创造。他在第五章中列举了美洲印第安人在农业、畜牧业以及工艺等方面的一系列发现和发明。他说:“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学家应在自己的领域中为促使各个民族和文化之间更好了解而工作。我们从原始人那里得来的遗产,是所有种族和民族所共有的。由人类学材料所揭示出所有民族的共性,最终将为世界大同的实现作出贡献。人类文化的最早发明和赐予者不能用肤色、民族或宗教来区分——他们是无名的。但他们很多人献给人类的幸福,远比许多现代政治家为多。”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类型的文化,但这些文化类型,又是互相联系着的,有的可以找出相同的因子。研究各种不同类型文化的异同,对于加强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相互交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参考的比较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举例来说,就古老的搬运形式而言,扁担这种搬运工具,并非中国所独有,北美墨西哥印第安人也习惯使用扁担。该书第七章用图片形式介绍了阿兹蒂克人、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墨西哥人、比属莫巴利人用前额承负带子的搬运法。今天中国的西南各族中,例如在哈尼族中,仍然流行这种搬运法。更令人惊奇的是,把该书的这种搬运法图片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二千年前的青铜器上的图片相对照,真是何其相似乃尔!读了这本书,我们不但会对世界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有了概观的了解,还会为研究中国各民族文化找到可资比较的参考资料。
三
一本妙趣横生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译成中文,弄不好就会变得晦涩难读,或索然无味。汪宁生同志的译文,笔触流畅,生动活泼,保持了原作的风趣。译者还在中译本中增加了大量注释,或纠正原书的谬误,或对某一特殊的习俗、事物及地名、人名加以解释。从中可以见出译者深厚的功底。尽管如此,这本书从着手翻译到正式出版,却整整经历了十九年!而译者所据的英文版本,还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本普通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不过三十万字而已,却经历了三分之一世纪才介绍过来,不能不令人叹息“何其迟也”!从傅乐焕先生保存下英文本,到汪宁生同志把它译成中文正式出版,从这段曲折的经历中,可以窥见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之命运的一斑。
从世界范围讲,十九世纪中叶,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已在西方各国流行。说到它们的东渐,却是最先伴随着社会学学说传入中国的。二十世纪初,进化人类学派的理论和著作已被介绍进来。民族学最早被译成“民种学”,一九○三年林纾、魏易合译出版了德国哈伯兰的《民种学》(即《民族学》)。正式使用人类学名称是在一九○六年,如孙学悟的《人类学概论》、陈映璜的《人类学》等。“民族学”一词的正式使用,始于一九二六年蔡元培写的《说民族学》一文。自此以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取得了立足之地。解放前,涌现了一批颇有成绩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出版了一批论著和译著。一九三四年建立起中国民族学会。当时,国内不少知名的学府都开设了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课程。诸如《民族学研究集刊》、《人类学集刊》等许多学术刊物也相继出现。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四年版的林惠祥先生的《文化人类学》,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吴文藻先生的《文化表格说明》,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费孝通先生译述《文化论》等,对于介绍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状况,起过较大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民族学,是解放后才正式开始的。五十年代,国家曾组织全国大批民族工作者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方面的一大笔宝贵财富。然而,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至一九五八年,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民族学便遭到当头一击,被宣判为“资产阶级的”。自此以后,民族学的学科名称被取消了,“民族学”三个字成了讳莫如深、无人敢提的禁区。至于“文化人类学”这一术语,更被遗弃。我们不妨翻一下一九六五年出版的《辞海·未定稿》,洋洋十万余条的汉语语汇中,既查不到“民族学”一词,也找不到“文化人类学”一语。作为一门学科,已被冷落到何等地步!进入七十年代末,“四人帮”被打倒了,在拨乱反正中,民族学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新版《辞海》中,已有了“民族学”一席之地。不过,“文化人类学”仍是“不见经传”。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出版的《辞海·百科增补本》还是未收这一术语。可是,在“文化社会学”的条目释文中却说:“十九世纪末在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令人不解的是,被影响而产生的学科立了条目,而影响者却避而不谈,岂不怪哉!诚然,每一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习惯来确定某一学科的名称。在我国,“文化人类学”可以不做为单独学科,而把其内容归入“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但是,“文化人类学”这一术语毕竟是客观存在,目前在国外影响颇大。况且,这一术语在我国亦曾流行过。采取不予理睬的做法未必高明。由于多年的自我封闭,使我们对于世界上各种文化人类学流派的情况了解得太少。这在我们的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是个亟待填补的“缺环”。
从这个意义上说,汪宁生译出的这本《事物的起源》,虽然是一本旧著,并非反映当今国外最新研究水平的新书,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事物的起源》,〔德〕利普斯著,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版,1.2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