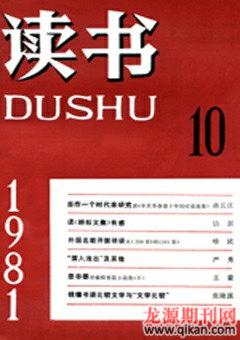读《耕耘文集》有感
洁 泯
文学之有评论,通常总是适用于评论作家及其创作方面的。至于评论一个评论家的文章,除了关于论争之类的问题外,鲜有见及。有人说,这是评论家的悲哀,悲哀处在于见不到评论者所持议论的社会反响和社会评价,倘有评论之评论,那就是一种反响了,可惜很少有。其实评论文章之少有反响,也算不得是一种悲哀,比如听讲,听者并不鼓掌,讲者也不以为是一种悲哀,听者的默默领受,并不走散,也算是一种反响的,不过这种反响是听不到的。对于评论文章多数的没有反响,似乎也可作如是理解。
可见,要求有较多的评论之评论,是一种苛求。但是可不可以说,对评论家的劳绩,人们可以永远不置一词是一种合理现象,自然不是。文学评论的意义及其作用,不独在于记叙一时期的文学风习,重要的是在剖析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倾向、创作风格的发展;比如种植,灌溉和芟除都不可少,评论家是承担这两方面的责任的。但也并非说,每一个评论家都负有如此深重之重任,而只是说,在这些重要的职责方面,一个评论家总是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有着他的劳绩的。
冯牧就是其中付出劳绩的一个。如今看到他的评论集子《耕耘文集》的出版,抑不住心头的一点欢喜。这集子是早该有了的,因为人们记得他在当代的文学评论工作中付出了的辛劳,留下了不小的印象。如今这么一本书,掩映这三十年来文学战线上的斑斑点点的战绩,其中有战果,也有失误;有欢愉,也有悲伤;有汗流,也有血痕。一本论文集竟常常是一本历史书,它照着生活的历史,文学的历史。它仿佛又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由此去观照往昔的年代,去鉴别历史和生活、思想以及艺术上的是非。所以,读这样的书,总不免会引起人低
评论之可珍贵,在于立论的评判力,在于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评判。冯牧所评论的作家和作品,虽不算多,但事隔多年,于今看来,还可窥见其昔日的锋芒,其所持论点,大抵都还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是至今犹可一读的文章。例如对李准、艾芜、李季、柳青、杜鹏程、王愿坚、高缨等的评论,都不失为是一些有益的见解。它的有益,不独在于议论的剀切、入微、周详,也常在指出作品的弱点和种种不足之处,每有独到之见。对作品的肯定和批评都是一种评判,倘说有所获益,于作家说,有时也常常胜于读者,因为它与作家的创作实践有着直接的关系。评论家要做作家的诤友,看来冯牧是在这方面尽心的。这尽心,说成是评论家的良心也不为过,一切庸俗的捧场和一味的申斥以至使用棍子之类,都和这种尽心不相干,它只是真正的有益于读者和作者。要达到这一点,则全仗评论家有过深思熟虑而出诸笔端的评判力量。狄德罗说过:“如果决定评判力的经验在记忆里尚未消失,我们便有了有识见的艺术欣赏力;如果记忆已经不清而只剩下一些印象,我们便只有艺术感觉、艺术本能。”艺术感觉固然也重要,因为是一种感性的艺术本能,它的评判常常会拘泥于艺术本身。在艺术感觉中如果唤起一种理论思辨,给以社会的、历史的、道德的、哲学的、艺术理论的以至政治的因素,那么评判力就在这里产生了。评论家的思想力是显现在评论艺术作品的社会作用的高度上和艺术见解的高度上,使思想力附丽于艺术品,使艺术品闪耀思想的光。这正是评论家的任务及其可贵的地方。
说穿了,评论家的评判力,评论家的要旨又端在于分析。对好作品,乱捧是捧不出来的,只有在分析中才能看出它的长处来。对有缺点和错误的作品,也一样需要分析,指出其错误所在;一部有缺点和错误的作品,常常有很复杂的内在因素,它需要引导,也需要指出它的某些可取之处。倘若只是一味的骂,作者不会服,读者也不愿听,所以用“骂倒”之法是不行的。例如说,《耕耘文集》中所收谈海默的一篇文章,使我联想到当年批判《洞箫横吹》时一概骂杀,不容还嘴,不由分说的那种情形。那个时候,除少数作品外,被骂杀的大抵倒是好作品。现在海默的作品证明是好的,他的新集子又已重新问世,骂了好多年,可见并未被骂倒。
但骂杀的流风,似乎至今并未稍敛。那种声色俱厉,无限上纲的粗暴作风依然有。其实它和真正的文学批评并无共同之处。文学批评需要的是说理,说理者,要击中对方要害,以理服人。倘与此有悖,声音再大,文章再多,也不过是隔靴搔痒,未能落到实处。其效果,也成了一种吓人战术。再者,批评并非如灭蝇那样简单,见蝇就打;凡见到有可批评之处,也是旨在引导,在于循循善诱,帮助对手认识和改正错误。倘对手并未认识到,要允许还嘴,互相切磋商讨,逐步求得统一,有些问题例如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可以也必须允许求同存异。批评者与人为善之心必须有,平等待人之心更不可无。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是复杂的,因此评论工作也必须遵循此种规律去求得是非的究竟。
《耕耘文集》写作的年代,大半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在那个评论空气只准以政治标准为唯一的年代里,要写出一些既有思想分析又有艺术分析的文章,既有热情支持又能切中要害的评论,是不可多得的。于今看来,这似乎是平常事,但回顾一下历史,便觉得珍贵异常。只须看看在那些年代里众多的评论文章,在今天还可资看看的,能有几多?我并非特别推崇冯牧的这些文章有如何的了不起,要说它某些文章分析的深度不足的缺点也还是有的,我说的只是那种批评精神,那种批评态度,商榷的态度,那持论的严谨,一句话,那种科学的态度,颇值得人深思默记。
还可以说一点。在过去“左”的理论影响下,文学艺术真正的繁荣受到了压抑。例如写什么人物,在文学理论上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争论。理论问题是研究作品的思想主题,思想倾向,作品能否反映生活和表现时代,作品的艺术问题等等。至于写什么人,只要能达到一定的思想要求和艺术要求,是无须苛求和限制的。而且也只能按照作家熟悉什么人为前提,才可能写出真实的文艺来。但是在当年,写反面人物,写落后人物,作品中凡对此着墨较多的,都要冒着点风险;要使这类人物当作作品的主人公来写,不消说风险更大。至于作品中出现过的一些“反面人物”,大抵是脸谱化的“千人一面的孱头和蠢材”。这个气候里,冯牧的《略谈文学上的反面教员》,提倡了把反面人物形象要写得深刻一些,在当时的理论空气中,无疑是一服清凉剂。自然,它当时也无补于创作实际,因为据说提倡把反面人物写得愈生动,愈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现在重读此文,恍如隔世。这几年来的文学新潮的汹涌之势,已将此种污浊之气吹得荡然无存了。但这文章写于一九六二年,彼时彼日,于今已不可同日而语,它的新意,在人们记忆中是至今犹存的。
《耕耘文集》还收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些论文和发言稿,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写的,在文艺战线思想解放的潮流中,都无疑是起了良好作用的。特别是对三年多来文学创作上达到的成就的肯定,对当前创作上存在问题的一些认识,有着深入的分析和阐发。此种议论,因为并非出自书斋中的论谈,与别人的利害似乎无涉,它因为是众说纷纭中的一种见解,其触着之处,也常在一些不同的论点方面。由此可想,这几年中不断出现的争论实在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文学是要向前走的,而且会向更健康的道路走下去,使之更符合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求。评论家的议论,只是对一时期的文学作出自己的评判,至于是否允当,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将会作出最公正的评论。
(《耕耘文集》,冯牧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一版,1.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