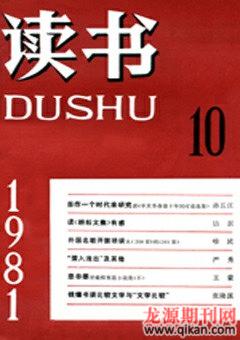外国名歌开禁琐谈
唯 民
不少音乐工作者和歌曲爱好者大概想得起五十年代末音乐出版社曾经编过一种通俗歌集叫《外国名歌200首》,出版了大小开本,前后印行七十余万册,畅销全国。据说刚上市的时候还发生过因读者争购该书新华书店柜窗被人挤破的“盛况”,连海外报刊也视为新闻。这样一本集中地介绍古今外国名歌的大全,一时确受青年读者和知识界欢迎,因此迅即传开。由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在对待科学、文化等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这本歌集出版以后就遭了厄运,其中几首著名歌曲在批判“名洋古”声中且被目为“十大软歌”,“助长了轻歌曼舞”,“美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及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在“四人帮”借机扫荡文化的刀光剑影下,《外国名歌200首》更被点名为“臭名昭著的大毒草”。——它差不多已落定为禁书了。
《外国名歌200首》在“大跃进”后编成,一九六○年已印至第四版,随后又出了续集。这两本歌集共介绍了约四百五十首歌曲,相当大的一部分确是国外长期比较流行的、有定评的佳作,或是解放前后在我国传唱的作品。占歌集三分之二以上篇幅的是十八、九世纪欧洲大作曲家的代表作,如古典歌曲中的著名歌剧选曲、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艺术歌曲以及解放前我国知识界原来熟悉的一些名歌;还有反映各国人民生活、劳动、斗争的民间歌曲。这里提供了有助于了解各个民族所处时代不同的社会风貌、了解西方专业音乐创作、表演(艺术歌曲和歌剧选曲)发展以及作曲家创作个性与风格的材料——应当说是不可多得的思想材料。但是,作为介绍给群众演唱、听赏的通俗歌集,不能说我们的编者那时已对这些西方音乐遗产进行过缜密的研究,完成了分清精华与糟粕的整理工作。因此,在选材上有所不当是难免的。例如某些歌剧选曲脱离原剧情节,剧中人物单独演唱有时会使人高深莫测、不明所以;有些艺术歌曲不联系当日的社会背景也会使人产生误解或难以理解。一些抒情歌曲(特别是某些爱情歌曲)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里传播,不能不说在某方面也有它的消极影响,如《卖布歌》、《小板凳》、《昨天晚上刮着风》、《雅娜,你不要再折磨我》等就并不适于当作“名歌”收入。作为编者,应当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与人民脉搏相通,才掌握得住这个分寸。但不论如何,把《200首》打成大毒草,把《宝贝》、《拉兹之歌》、《蓝色多瑙河》等许多作品打成“十大软歌”,那是过火批判,不足为法,今后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办了。
“四人帮”粉碎后,双百方针得到初步贯彻,思想文化领域一些不应有的禁区过不多久就开始被人冲破。一九七九年春,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当时在这方面还属仅见的《外国歌曲》(第一集),印行百余万册,超过《200首》的累积印数。曾被列名为“软歌”的一些作品重新露面。香港报刊评论说它“显是十四、五年前那本《外国名歌200首》的再编本。……选材、译词都格调较高,……对普及健康音乐有好处。”国内多数人是欢迎的,但也有人认为编辑“思想解放得不够”,有的青年读者甚至认为其中所载的歌曲不似现时的流行歌调,“没劲”(不过瘾)了。在一部分青年中,连外国民间歌曲、艺术歌曲、歌剧选曲也变得“曲高和寡”,和群众齐唱歌曲一道被人打入冷宫,不那么“行时”了。有的人看了外国电影《音乐之声》就唱《雪绒花》,看了《人证》就唱《草帽歌》,这还没什么可以非议;看了《大篷车》唱《真叫我啼笑皆非》,听了佐田雅志弹唱学他那首《男子汉宣言》就显得不伦不类,刊物发表更是大可不必。至于个别演员不问情由地在众目睽睽的大型晚会上唱什么《别在星期天》这样一首并不隐晦地写寻欢作乐的歌曲,那就更是贻人笑柄,连听者都感同受辱了。据说在某大都市还有昔日的专业演奏员“重操旧业”,在饭店舞厅大奏其《烟迷了你的眼睛》、《星星的灰尘》等三四十年代外国的轻爵士音乐,为了能体味“回到过去年代”的音乐而欣欣自喜。这里轰动一时的“新”,其实是陈年老货的“旧”,不是很显明的吗。目前从海外进口的部分卡式录音磁带虽然不无可听的音乐,但古典作品往往经过“现代化”编配的“改造”,有时弄得面目全非;有些轻音乐则不过是商品性的近代舞曲和低廉的流行歌曲,上口是容易上口,可真是喧闹得有时叫人难于入耳,更不能培养高尚的音乐情趣。
从名歌被禁到开禁以后出现的一些情况说明:禁止外国歌曲是荒谬的,开禁完全必要。但是,开禁以后必须继之以疏导,把某些人的欣赏兴趣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向群众介绍一些较为平易的世界名曲(并非都是“阳春白雪”),拿东西方音乐宝库里脍炙人口的珍品让他们品尝一下,逐步引起他们爱听和研究这些音乐的兴趣,就是疏导的办法之一。(北京、上海音乐学院和专业团体的同志去大专院校开音乐讲座,介绍中外严肃音乐便是收到成效的尝试。)那种认为外国名歌“没劲”的看法到底不是代表性的,也不会持久。不少年轻人的兴趣目前开始有所转变就是证明。
蔡特金回忆列宁对她说过:“即使艺术品是‘旧的,我们也应当保留它,把它作为一个范例,推陈出新。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我们就要撇开真正美的东西,抛弃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是因为‘这是新的,就要象崇拜神一样来崇拜新的东西呢?(列宁这里指的是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等)那是荒谬的,绝顶荒谬的!”
列宁的这种论见,在一个著名现代作曲家辟斯顿(美国人)的一席谈话中得到这样独特的响应。他对他的学生韦斯特加德说:“他们(指一些青年作曲者)似乎都经历了一定的自然演变过程。最初他们都热血沸腾,就象我们在二十年代时那样,想要摧毁过去。然后他们长大了些,他们说,‘也许归根到底,过去并不是必须摧毁的。我想我不去毁灭它了。然后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并不知道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来没研究过它。后来,他们年事稍长,对自己作自我剖析,看看自己有什么可表达;他们发现迫切需要的是对音乐遗产的深刻理解。”这是发人深省的看法,然而有的人要接受并领会这种常识性的真理还多么不容易。
再举一例:“对待那位解放音乐的巨人”、那位对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贝多芬,有人不是说他“过时”了、“老掉牙”了吗?但被认为代表新潮流的近代俄国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他年青时对别人灌输给他的贝多芬作品及其有关的“老生常谈”感到厌恶,但到他成熟起来、要更仔细地研究古典大师们创作的奏鸣曲时,他较客观地接近贝多芬,后者在他眼前便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我从他那里识别到他是无可置辩的乐器之王”;“他能成功地使得凡是愿意接受音乐的每一只耳朵都喜欢听他的音乐。”
传统虽是一种巨大的阻力,但真正优秀的传统又自有其力量和意义。我们决不能简单地以天真的革命精神予以一概抛弃。
“洋歌”开禁,《外国歌曲》出版之后,各地出版社就竞相编出了多种外国歌曲集,如《外国名歌选》、《外国抒情歌曲选》、《外国民歌100首》、《中外抒情歌曲300首》、《中外抒情独唱歌曲选》等等。所介绍的外国作品,有不少实是《200首》的旧歌重放,有些则译配加选了若干新作……冠以“抒情歌曲”之名,以别于“四人帮”横行时真情不敢露,有情不能抒,鸣不平也。此时编者不免大声疾呼:“抒情歌曲今天应予恢复名誉,以满足群众精神上的需要”;论者也随声慨叹:“熬过十年霜冻,这株人们喜爱的花苗终于绽蕾开放了”。有人甚至进而宣称:“战歌已经过时,要以抒情歌曲为主”,这是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今年二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外国名歌201首》。歌集沿袭了过去的编辑体例。在选曲上保留了原来的许多好曲目,又适量地作了新的增订,体现了“尽收精华编选而成”的原则。翻阅了歌集,感到有三点可以一提:
首先,《外国名歌201首》所收的名歌,不受时下风尚的影响局限在一般抒情歌曲上,而以若干篇幅发表了一批渗透着革命精神、真正传诵一时的名作,如表现各国无产者为打碎镣铐而斗争的传统歌曲,歌唱社会主义革命与反法西斯斗争的歌曲,第三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社会民主的歌曲,如《马赛曲》、《华沙颂》、《迎着曙光》、《我们是红色的战士》、《神圣的战争》、《沼泽士兵之歌》、《阿娜依》、《游击队之歌》等,这些作为历史铁的见证的歌曲,充满“鲜血在燃烧”的革命豪情,反映出时代真正的本质与主流。它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艺术上也非常感人,有的且可说是撼动人心。词曲大多写得很有深度,曲调素材简练(多段词的分节歌形式居多),但塑造出的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艺术技巧有其独到之处,民族音调各有特点(不同民族发展了不同的歌曲乐汇——运用了各别的音阶、旋律音型、节奏动机等)而又亲切耐听,值得我们从中汲取宝贵经验作为创作的借鉴。认为“今天已不需要时代的强音”;时代的审美要求已从壮美过渡到秀美;今天的青年不会或难以接受壮美的音乐;既然劳动、生活需要休息娱乐,就只能要缠绵、妩媚、轻盈,而不能要昂扬、激越、深蕴,这种看法将被证明为过于武断。且不论对抒情歌曲应作何明确的界说,“战歌”与抒情歌曲至少是可以并存共荣的。安定团结、“四化”建设的时代也有它自己的“强音”,不一定以“高、快、硬、响”为特征。一首抒发青年崇高革命理想的好作品难道不可以作为“时代的强音”?把优秀的革命歌曲统统降格为或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四人帮”贬抑文化价值的产物)一类干巴巴的标语口号式歌曲,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那些好歌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也是抹不掉的。
其次,《外国名歌201首》(《201首》想是难得的佳作再经遴选,比《200首》又略胜一筹之意)编得比较丰富多彩。篇幅容量不大,但所收作品却显得仪态万千。歌集中有革命歌曲、抗议歌曲、劳动歌曲、行进歌曲,又有叙事歌曲、传奇歌曲、怀乡歌曲、爱情歌曲和其它生活歌曲。有的气息宽广,有的真切如画,有的清新纯朴,有的柔细纤丽,有的豪情奔放,有的谐趣横生……总之是题材、形式、风格多样,不显单调,不致使人听腻。抒情歌曲(按这个词较广的含意)可说俯拾即是,举不胜举,如《红旗》、《天空布满灿烂星辰》是一种胸怀世界的博大抒情,《同志们,勇敢地前进》、《啊,朋友》是一种并肩战斗的豪迈抒情,《光荣牺牲》、《小号手》是悼念战友的抒情,《我的祖国》、《梭罗河》是热爱乡土的抒情,《老人河》、《伏尔加船夫曲》抒的是沉痛抗议之情,《清津浦船歌》、《拉网小调》抒的是劳动欢快之情,《母亲教我的歌》、《小小的礼品》抒的是母子挚爱之情,《当我们年轻时》、《友谊地久天长》抒的是依依惜别之情……这些歌哪一首不是真正的抒情,不是情景交融地抒发了词曲作者在特定环境下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最美好的感情?又哪一首不深深地拨动了听众的心弦?因此可以说这些歌具有真正的艺术魅力(而非感官刺激的诱惑力)。写夜莺、写玫瑰、写月夜、写草原,都各有情致;同是咏春,《春潮》、《布谷》、《春之歌》、《渴望春天》又多么不同;《魔王》、《洛累莱》、《跳蚤之歌》写得多么生动逼真;《老黑奴》、《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春天年年来到人间》写得多么沉郁深蕴;《安妮·萝莉》、《我心怀念高原》、《在最美丽的绿草地》写得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几首《摇篮曲》和《小夜曲》的旋律,各有着作者自己的印记,各自呈现出新鲜的面貌;即使都是写男女情爱,在处理上也有很大区别,如《我的太阳》、《我怎能离开你》、《星星索》、《深深的海洋》、《妈妈要我出嫁》、《可爱的珍妮薇芙》、《啊,约翰,这可不行》等,不给人雷同的感觉。歌集中一些经受了一二百年考验的曲目,有不少是西方音乐辞书里经常列名提到的,如《夏天的最后一朵玫瑰》、《伦敦德里小调》、《可爱的家》、《故乡的老亲人》、《桑塔·露琪亚》、《重归苏莲托》、《索尔维格之歌》等。有的古典歌曲和歌剧选曲在技术上难度较大,但作为稳定的保留节目,仍可提供给读者听赏。有些歌曲,如还能提供必要的背景说明,将会更受欢迎。
最后,《外国名歌201首》的歌词在译配上由于许多有经验的译配者长期努力,是基本上做到了严谨、忠实、雅致、上口的。——虽然不是全无瑕疵,水平也不一致。相信今后再版还有润饰提高的余地。
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歌曲,是最能直接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便于广泛传播的一种声乐体裁。歌曲能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培育人们美好心灵的催化剂。为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拿过来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精神食粮,应当是经过选择的好东西,这样消化吸收才对肌体有益,有利于借鉴发展我们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但介绍不能变成替代,模仿也不是艺术创造。以为趋附任何外国舶来的“新”便是打破禁区、解放思想,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还是要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蚀。“寓教于乐”这个“教”(教育、感染)还是应该肯定。有意投合部分听众的低级情调去败坏一代青少年的口味,是一桩误人害己的犯罪行为。培养听众健康的审美观,让他们识别资本主义“万花筒”中的各类货色很有必要。从作曲家到表演家到报刊编者,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艺术良心应是同人民群众休戚与共,他们应当帮助群众感受到时代的精神。在这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新时期,在加强团结、共同奋斗建设社会主义“四化”强国的时期,要他们分担这样一份神圣的职责,我想不会是过分或多余的吧!
(《外国民歌201首》,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0.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