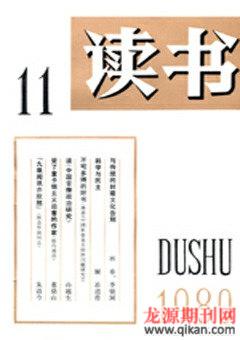怎样评价《茶花女》
陆晓禾
小仲马的《茶花女》,在短短一年里出版了三种译本。可以想见,这部小说目前拥有相当多的读者,玛格丽特和阿芒悲欢离合的故事成为了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的话题。
《茶花女》这部小说的意义是什么?报刊上已经有些评介文章谈过这个问题。但是,论述的角度、重心和提法都不甚相同。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将其中两种评价列出来加以探讨。
一种评价是:“小仲马是资产阶级作家,他在《茶花女》中针砭贵族资产阶级道德风尚,同情被污辱与被损害者的不幸命运,目的是要纠正人心,改良社会,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不懂得娼妓问题只能通过消灭资产阶级制度来解决,而以真正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只有在无产阶级中才能成为男女关系的常规。不过,他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描写,对我们今天的读者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不平,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①另一种是:“《茶花女》,一曲凄恻美丽的爱情之歌。小仲马不是巴尔扎克,他的全部作品都不曾想暴露和针砭什么。虽然他某些作品客观地有一星半点这类意义。”②
这两种评价都涉及到小仲马在《茶花女》中的主题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两者发生了分歧:前者认为小仲马的“目的是要纠正人心,改良社会,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后者认为《茶花女》是一曲“爱情之歌”,“他的全部作品都不曾想暴露和针砭什么”。究竟哪一种评价正确呢?作品的目的是一个不易明了的问题,契诃夫说:“人家常问我在小说里要表达什么,我从来不回答这类问题,我的本分是写。”这就是说,作品的目的是通过作品本身来表达的。你要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只有通过深入地阅读和研究作品本身才能得到。然而,由于各人的理解不一,答案往往不尽相同。但不管怎样,要解决作品的目的问题,除了分析作品本身而外,别无它法。
小仲马在叙述故事前,有一段简洁论述是耐人寻味的。他以为,人们并不能在人生的路口上简单地竖上一块是“善”的牌子、一块是“恶”的牌子便了事的。他认为应该向基督学习,因为基督不仅告诉人们哪是善的路,哪是恶的路,而且他还指出如何由恶转向善的途径。我以为,这段论述便是这本书的纲,它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他的立意是什么。
我们来看作品。作者并不赞美妓女,他也认为卖淫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并且他比一般人更深刻地反对它。然而作者并不是到此为止了。不,他还力图消灭这种丑恶现象,解除陷入卖淫生活的妇女们的痛苦。在《茶花女》中,玛格丽特曾经两次遇到解脱卖淫生活的机会。一次,是那位老公爵,他在悲痛欲绝地离开女儿的坟墓回家途中,遇到了长相和他女儿一模一样的玛格丽特,于是公爵哭着上去拉住了她的手,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带到家中。后来有人告诉他玛格丽特从前的行为时,公爵在几回动摇之后,仍然保持这种亲切的父女之情,条件是玛格丽特不得再过以往不名誉的生活。正在养病的玛格丽特一口答应了公爵的要求。可是回到巴黎之后,一群“爵”们又围拢上来。于是玛格丽特又过上了从前的生活。另一次是玛格丽特在那一群握有百万法郎而又冷漠无情的人们之中,发现了出身于中产阶级的阿芒这样一个正直而真心爱慕她的人时,便毅然抛弃了一切:她的马车、豪华的公寓以及象征她的污秽生活的巴黎,爱他,和他生活在一起。可是好景不长,起先是公爵向他们发难。一向把玛格丽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并且毫不吝惜地供给她生活经费的公爵,在得知她和阿芒共同生活后,即愤怒地断绝了他的慷慨援助。但这并没有吓倒年青人。玛格丽特鄙视以往的一切奢侈品,她没有它们也能生活下去。她乐于失却它们,乐于贫穷然而高尚的生活。她认为这才是幸福的生活。她感到此时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接着阿芒的父亲赶来反对。他软硬兼施,迫使玛格丽特不敢和阿芒打招呼而半夜离开了家,回到巴黎,重新堕入污秽的娼妓生活,最后在痛苦、失望和寂寞的凄惨境遇中悄然死去。
两次解脱,两次都解脱不成。可以怪罪玛格丽特本人吗?你看,当玛格丽特病愈回到巴黎时,那一群在她生病期间销声匿迹的上流社会的贵族们又包围了她,仍要她以卖淫为生。如果说这一次的没有解脱还可以怪玛格丽特的意志不坚定,那么第二次则完全归罪于老公爵和阿芒的父亲了。前者是自私的,他的解脱玛格丽特也是假的,因为他只许玛格丽特同他在一起,为他牺牲她自己的欢乐,否则为什么他要断绝玛格丽特和阿芒生活的经费呢?这一断绝,揭去了他的道貌岸然的假面具,暴露了他的龌龊自私的真面目。后者即阿芒的父亲所显示的不是一个人的形象,而是整个社会道德偏见的化身。阿芒的父亲放在玛格丽特面前的选择是:毁掉阿芒光辉的前程和其妹美满的婚姻或牺牲玛格丽特的爱情。提出这种选择即说明了在阿芒的父亲背后站着一个可怕而僵硬的社会。它对玛格丽特们抱有深刻的道德偏见,只许她们在它的脚底下象畜牲一样辗转爬行,而不允许她们直起腰来过人一样的生活。即使是已经爬起来的也要把她们再活活地踩下去。话剧里玛格丽特曾悲愤地喊道:“这就是天理吗?既然你跌倒,就再也不能爬起来,上帝会原谅你,但人们却永远不会!”就是对这个无情社会的泪的谴责!是社会不允许玛格丽特过正直的生活,是社会在玛格丽特由恶转向善时又重新把她推入火坑。社会造成她们,社会又只许她们保持她们原来的地位;社会使她们从人变成“禽兽”,社会又不允许她们从“禽兽”再变成人。这个该诅咒的社会啊!
这样,小仲马挑开了茶花女们珠光宝气的表面装饰,揭开了她们奢侈放荡的生活盖子,向人们展示出了一个高尚的灵魂,写出了它正在哭泣、受难、淌血,写出了它向往正直、高尚、幸福生活的强烈欲望。同时他也就无情地暴露和针砭了贵族们自私、虚伪和腐化的道德面貌,指出了他们及其社会的道德偏见是人们由恶转向善的障碍,是造成病态社会现象的根源。因此他力图告诉人们:卖淫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娼妓们也有争取高尚、正直、光明生活的愿望和决心。人们啊!在她们争取光明生活走向善抛弃恶时,决不能鄙视她们,拒绝她们,打击她们,而应当帮助她们,热情地、真诚地帮助她们完成这一从恶到善的转化。她们是有权享有爱情、幸福、善的生活的。因为当转变途上的荆棘和坎坷扯去了她们的华丽的外衣而露出了血淋淋的裸体时,她们在上帝的面前仍可以说是纯洁的,无罪的,因为她们得救了。
小仲马的这种想以启发人们道德意识来消除社会丑恶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然是一种“乌托邦”。因为他不懂得造成娼妓现象的根源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不懂得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娼妓问题。但能否因此说他在《茶花女》中的目的就是“要纠正人心,改良社会,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呢?“纠正人心,改良社会”,是不错的,“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似有些勉强了。因为一,如上所说,在《茶花女》中小仲马的目的是暴露和针砭贵族资产阶级自私、虚伪和腐化的道德面貌,启发人们伦理的意识,并劝诫人们向基督学习,帮助堕落者由恶转向善,而不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二,当然不能把他的暴露和针砭说成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也不能因为他没有找到罪恶的真正根源,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提出改造社会的根本办法,就说他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我们确实应当看到小仲马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就此说他本人的主观目的,或者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显得有些武断了。
另一方面,能不能说《茶花女》是一首爱情之歌,小仲马的“全部作品都不曾想暴露和针砭什么”呢?暂且不去论述小仲马的全部作品,就《茶花女》这部作品来说,我认为这一论断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当然,如果说小仲马在《茶花女》中并没有直接暴露和针砭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对的;但如果说他对那些贵族的丑恶的道德面貌也没有暴露和针砭,似乎也有些武断。从《茶花女》来说,为什么玛格丽特与阿芒的纯洁、真诚的爱情不能实现呢?原因还在于客观障碍:贵族资产阶级及其社会的道德偏见。小仲马的这一揭示也就是暴露和针砭。美丽高尚的玛格丽特的失败,就是对丑恶、虚伪的贵族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暴露和针砭。这是很显然的。今天我们看他的小说,不仅要看到作者在小说中所力图暴露和针砭的社会内容,而且因为他所暴露和针砭的社会现象也是他那个社会的本质的反映,因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从现象到本质加以分析,看到他所未直接予以揭露和批判的社会本质。是谁迫使这么许多的良家女子堕入娼妓生活的深渊?是谁在她们化了九牛二虎之力过上纯洁生活的时候又将她们残酷无情地推入污秽的非人生活?是那些贵族、是那个罪恶的剥削制度。没有那些握有百万法郎的贵族们,就没有茶花女们,问题不是很清楚吗?当阿芒追求玛格丽特时,有人就告诉他,八千法郎的年俸还不够她的车马开销。贵族们靠剥削收入,挥霍乱用,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只有这些贵族才养得起她们,也只有这些贵族才需要她们。娼妓是剥削阶级的产物,而剥削阶级,这些贵族又是依靠剥削制度作恶的。因此,只有消灭剥削制度,才能消灭它所带来的丑恶,只有消灭剥削制度,妇女才能真正翻身作人,过上纯洁美好的生活。小仲马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我们从他所描述的玛格丽特的遭遇中不正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吗?!这一结论是从对他的暴露和针砭分析中得来的。而他的暴露和针砭又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强调《茶花女》是一首爱情之歌,对于肃清否定一切爱情描写的极左流毒,固然是必要的,但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也同样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和评论这类作品。
文艺的形式多种多样,文艺的内容也纷繁复杂。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作品固然最好,仅只是个人主观感情抒发的作品也不能忽视。象“四人帮”那样,在一个公鸡身上大找“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内容,固属可笑;然而倘若将有暴露和针砭内容的作品说成没有社会内容,也是不正确的。
①《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十日,张英伦:《<茶花女>是一本什么书》。
②《读书》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林大中:《黄色,色情,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