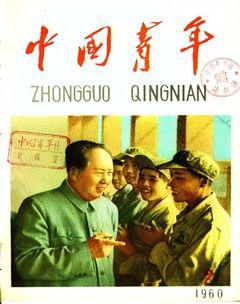红色医生李贡
叶君健
李贡是1954年从兰州卫生学校毕业出来的一个年轻医生。他是一个相当严肃——严肃得有点近乎拘谨的人。他的话语很少,面孔上老是罩着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缺乏热情和幻想的人。譬如,就他的工作而言,他就希望能有机会到藏族的同胞中间去服务。他觉得藏胞是些美丽可爱、甚至于充满了诗情的人。他喜欢他们的歌唱和舞蹈。为这样的人服务是一种幸福。
他的这种想法很快就被领导察觉了。他毕业时,党就把他分派到甘肃南藏族自治州去工作。但理想不一定就是事实本身。它往往和事实保持好长一段距离。甘南的情况就是如此。从地形上看,它是一片茫茫的草地,荒凉得不可以再荒凉。至于这个荒凉草地上的居民,他们在封建王公和反动喇嘛的残暴统治下,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悲剧还不止此。由于过去反动的汉族统治者对藏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压榨,藏族反动王公和喇嘛就利用这种历史上的不幸来煽起藏族和汉族之间的仇恨,借此以模糊他们内部的阶级矛盾。李贡一到他的工作岗位就发现了这种情况。
藏族同胞生了病以后,情愿把整头的牛羊送给反动的喇嘛,求他们来画符念咒,而不来找我们派去的医生。
有一天晚上,李贡所属的那个工作组在草地上发现了一个饿倒的藏族姑娘。他俩立刻把她抬进帐篷里来,给她水喝,给她饭吃,给她温暖;但她还不相信世上居然有这样无条件爱护她的好人。她怀疑人间哪会有这样的热情。但怀疑总经不起真诚的感染。她慢慢地觉悟过来了。她象对待亲人似地,开始吐出她心里的实情。她原来是一个有钱牧主的奴仆。她劳动了一年以后,牧主不但不给她工资,反而剥 去了她身上唯一的一件完整的皮衣。听完了她的故事,我们这位年轻医生当时就流下了眼泪。他想:这些受难的同胞,不依靠我们的党还能依靠什么人?他觉得为这些同胞工作是毛主席交给他的一桩神圣的使命。
李贡现在不是单纯在做卫生工作,而是在执行党和毛主席所交给他的一个庄严任务。哪里有病,他就到哪里去;什么时候有需要,他就什么时候到来。他的工作不分昼夜;他的季节没有寒署。他的服务是没有条件的。他既不要报酬,也不需要感谢。虽然如此,反动的藏族统治阶级和特务的谣言还在流行,说什么他的药物全是毒品。党不止一次地教导过他,真理的战士是没有理由惧怕谎言的。这一点在他的实践中也得到了证明。不久以后,有些穷人开始发现他不仅不是坏人,而且是一个朋友。他治病的本领超过任何喇嘛。除此以外,他还有一颗非常温暖的心。
这种发现是有传染性的。有一天,李贡的帐篷里来了一个名叫卓玛姬的中年妇女。她怀里抱着一个垂死的孩子。她见面的第一句能就是:“我是一个穷人。”从这句话中我们年轻医生可以体会到,卓玛姬是把共产党当作穷人的靠身。他当时心里就起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卓玛姬的孩子患的是支气管炎。由于骗人的喇嘛的耽误,由于孩子年龄太小(还不到一岁半),抵抗力弱,病情十分严重。李贡即刻把他的帐篷改成为一个病房,并且请卓玛姬也在这里住下来。
他日夜亲自看护孩子,整整有两天三夜他没有合过一次眼睛。卓玛姬有好几次把自己的皮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要他休息。但他坚持不肯,仍然守在孩子身边,按时给孩子打针吃药,按时量体温。到了第四天,孩子的温度渐渐退了。孩子开始睁开眼睛,寻找自己的母亲。卓玛姬象发了疯似地喜得跳起来。但她立刻又静下来了。她一会儿望望得救了的孩子,一会儿又望望这位疲劳得几乎要倒下来的年轻医生,不知怎的,她忽然呜咽地哭起来了。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她当时的情感,她只说了一句话:“毛主席是我们穷人的救星!”
从此,这个年轻的医生便专门治那些病情危急的人。依照喇嘛的算卦,这些人的寿数都是到了尽头,再治下去就等于“违抗神的命令”。李贡认识到,他必须用一切办法和力量来治好这些病人。因为这不仅是人道主义的问题,面且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他每治好一个病人就等于打了一次胜仗,等于为真理、为党在群众中树立起威信。
1955年春,他和工作组一道来到欧拉部落。这次和他初下草原时显然有些不同。人们已经知道“毛主席派来的医生”这个名词,而且也知道这个词的函义是“热心、诚恳和无条件地治病”。他一扎下帐篷就来了一个求医的人。这个人名叫曹加,是一个看羊的年青妇女。她的羊圈着了火,草原上那种有名的长而密的蔓草一下子就燎燃起来了。为了赶出羊群,她冲进火海中去。待她的丈夫把她救出来时,她的半个面庞和整个手臂都被烧焦了。她不仅失去了工作能力,而且还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当她被抬进这个年轻医生的账篷里来时,她只能举起两个指头做个手势,意思是说:“我是一个穷人。”
这位年轻医生轻轻地把她的伤口揭开一看,他立刻就冒出了一身冷汗。这是属于外科的病症。他对于外科并没有经验。问题还不在此。在他还没有来此以前,病人因为极度痛楚,曾经求过喇嘛。喇嘛一面念咒,一面对着她的伤口喷了许多“法水”。这种“法水”无疑地充满了细菌,因而加速了伤势的恶化。有几块地方已经烂得可以看见骨头了。怎么办呢?曹加是一个穷人,她是来找毛主席派来的医生解除痛苦的。李贡当时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必须把她的重伤治好。他坚决地对她说:“你放心吧,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从这天起他又当上了外科医生。
他的坚决的话语在病人的精神上起了镇定的作用。她的丈夫依从李贡的劝告,把自己的帐篷搬到附近来。这位临时改作外科工作的年轻医生的第一步计划,就是怎样来控制腐烂和阻止病灶的扩大。他一面在伤口上敷药,一面在皮下打针。这样一天三次,他同时做大夫、护士和护理员,因为这个小小临时“医院”的全体干部一共只有他一人。当曹加夜里痛得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替她打镇定剂。在他这样日夜细心看护和治疗下,她的伤口腐烂的情况终于被控制住了,两个星期以后,发炎的现象基本上减轻了。
曹加不知道是由于放心不下羊群呢,还是由于迷信以为伤口没有合起来,就证明医生不灵,她在十五天头上忽然拆下帐篷悄悄搬走了。李贡一发现这件事顿时感到惶惑起来。她为什么在病没有治好以前就走掉了呢?是她不信任自己吗?还是因为她听信了反动派的那套谣言——什么“共产党的医生不怀好意”,什么“共产党要用毒药来弄死藏人”。从政治角度来说,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算是失败,而这种失败却是在他手上造成。他感到惭愧,也感到难过。党把他派到藏胞中间来,是叫他这样工作的吗?他觉得对不起党和毛主席。他呆呆地望着曹加曾经支过帐篷的那块地方,差不多整整有一个上午站不起来。
还没有来得及去寻找曹加,他和工作组因其他的任务被调走了。1956年4月间他又和工作组回到了欧拉地区。事情真是巧得很,他又遇见了曹加。曹加的伤并没有好,并且由于长期的疏忽,正在恶化。他庆幸遇见她恰是时候。他不但有机会解除她的痛苦,而且还有机会挽回党的威信。但事实证明他的乐观是早熟的。曹加虽然答应每天按时来治疗,但是现在治疗却不是那么简单。腐烂的面积太大了。伤势不仅收不住口,新的肌肉连生长的可能性都没有。他带来的药品并不太多,而且由于自己不是一个外科医生,有许多必要的医疗器械也缺乏。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不仅没有把握治好,即使能治好也治得很慢;而时间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却又起很重要的作用。
他感到很苦恼。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她很快地解除痛苦呢?他真希望她的伤口能生长在自己身上,为她分担一部分痛苦。这样他多少也可以感到心安。
有一天早晨,当他正在学习政治理论的时候,帐篷外面已经集结了一群候诊的病人,曹加也在其中。有一位初诊的老太太和曹加谈起她的病情来,同时顺便问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的医生究竟有多大的本领?”曹加想了一下,没有直接答复。她只是把她的那只烧伤了的手臂伸出来,说:“你看,我治了很久,但至今还没有结果。恐怕我还得去求喇嘛。”
李贡当时就急了,他停止了自己的学习,立刻把曹加请进帐篷里来。他坦率地对她说:“我个人的医道不行,并不能说明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医道不行。我可以向你担保,我们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他停了一下,观察曹加的表情。曹加的脸上出现了一点犹疑的颜色。于是他继续说:“在兰州我们有非常高明的医生。他们连心脏都可以开刀。我担保他们会很快地把你的伤治好。我介绍你到兰州去一趟好不好?我们负担你来往旅费和一切其他开支。”
这时曹加作出一个苦笑,摇了摇头说:“我看我的病就这样拖下去了,反正不会死,我感谢你的盛情。”
这句话并非完全表示她对汉族医生的不信任。这里面还包含着一种迷信:过去和现在反动派一直在造谣,说内地太热,藏民一去就会闷死。她害怕伤没有治好,反而会送掉一条命。这位年轻医生没有办法,就在当天下午去找她的丈夫,希望通过理智的说服,可以获得他的支持。哪知他更不了解这位医生的诚意。他委婉地说,他们不愿意再为医生增添更多的麻烦。这时李贡才肯定知道,他们对自己已经失去了信心。
“请相信我,我一定会治好你妻子的伤。”他紧紧地拉着这位牧人的手说。接着,他引了藏民所常用的一句成语,以加重他的语气:“我拿出我的脑袋来保证!”
他当时所顾虑的唯一的事是:可能曹加真的又去求那些骗人的喇嘛,如果这些喇嘛再在她的伤口上喷几次那种充满细菌的“法水”,那不仅他过去的治疗会全功尽弃,她的伤势还会加快地转剧。还好,他的至诚终于感动了她,曹加答应第二天继续来治,而第二天她也果然来了。第三天也来了,第四天也来了。他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他为为她包扎伤口时那种慎重的态度,他急迫地要解除她的痛苦的那种热情,逐渐打动了她的心,使她开始认识到这位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是一个好人。她开始信任他。这种信任在他们的关系上展开了新的一页。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她的伤势呢?
他尽了一切努力,但是进展仍然很慢,如果现有的医疗条件不改变,要想及早地得到满意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了。而且附近也没有其他的医生可以共同研究这个问题。他开始失眠了。难道就让她的伤这样拖下去,使得她再次对他失去信任吗?这样作既对不起毛主席,也对不起病人。不!条件固然困难,但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是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吓倒的。他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而且也应当能想出一个办法来。他把他所随身带来的几本医书一页一页地翻阅,他把他在实习期间所经历过和见过的病证一桩一桩地回忆。他白天看病,晚间就钻在这种研究和回忆之中,想是否能找出一个治疗这种伤势的办法。他现在已经不是在失眠,而是在不睡眠。这种不睡眠的征象很快就在他的脸上和服神上表露了出来。
曹加注意到了这种征象。
“医生,你病了吗?”她关心地问。声音里第一次流露出她对医生的深厚的感情。“啊!医生,假如你病了我们怎么办?”
这几句意想不到的话温暖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心。他当时脸上就容光焕发,表现出一个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饱满的青春气息。他兴奋起来。他开始有勇气说出好几次跳到他口边而他始终不敢说出的那件事情。
“我一点也没有病,”他说着,作出了一个微笑。“相反地,我现在感到非常愉快。我想出了一个治好你的伤势的办法。”
“什么办法?”曹加急迫地问。
他犹疑了一下,但最后还是决定对她讲了。
“在外科手术上有种叫做植皮的法子。”他故作镇定地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好象他过去曾经作过这种手术似的。“把病人身上的皮——譬如腿上的皮——移植到伤口上,伤口不仅会很快地痊好,而且好了以后还和原来的皮肤没有两样。我想为你作这种手术。”
曹加听了这段话有中晌没有作声。最后她依旧没有作声就站起来。她头也不回地向门外走去。
“曹加,请你坐下来,”李贡用恳求的声音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请求你坐下来。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坦白地当面告诉我。”
曹加掉过头来。但是没有坐下,“我的伤已经够痛苦了,”她说:“再在腿上割几块皮下来我受不了。”
这位年轻医生点点头,他理解她的心情。但是现在已经最后的时刻,他必须作出决断。
“不需割你腿上的皮,”他坚决地说。“我可以把我腿上的皮移到你的伤口上去,这没有任何关系,你的伤口会很快地合拢。”
曹加呆呆地看着他。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医生吗?她不相信她的耳朵。但是这位年顿医生脸上的表情是严肃的,诚恳的,正如他一直对她医疗和看护是严肃的和诚恳的一样。他可以不用怀疑,他说的完全是他心里的话。她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当她想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是由于她的心里感激呢,还是由于她心里难过,她忽然放声大哭起来。
“不!不!”她说:“你为我治病已经够累了,我不能再让你痛苦!”
“我不会痛苦,”我们这位年轻医生坚决地说。于是他又引用了藏胞所常用的那句成语:“我可以拿出我的脑袋来担保,我决不会感到痛苦。我有麻药针,一打上麻药,我的皮肤就什么知觉也没有了,你放心吧,曹加,我无论如何要治好你的病!”
这话不说犹可,一说倒使她哭得更加厉害起来了——她哭得象一个三岁的孩子。她一时无法控制她心中感情的激动,就急忙掉转身,用加快的步子走掉了。
这位年轻的医生颓然坐下来,非常失望。她为什么又走掉了呢?但仔细一想,她这次离去显然跟她第一次搬走时的情况有些不同。这次她是在感情的激动下走掉的,而这种感情是她对毛主席派来的医生所怀
有的一种感激之情。当他一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又有了新的勇气,他一跳就站起来,决定再一次去说服她。他骑上马,向曹加住的那个方向驰去。曹加已经先到家了。她正在向丈夫叙述她和医生谈话的经过,她叙述得相当激动,也充满了感情。丈夫一看到她这种神态就连连点头,似乎又懂得了这位汉族医生的诚意。当李贡走进帐篷时,丈夫正在感动地捏着妻子的手。他似乎也要流出泪来。在他们一生之中,从来没有什么人这样关心过他们的痛苦。
“医生,我们完全懂得你的诚意,”他一看见医生走进来就直截了当地说:“但我们不能使你痛苦。如果这样,神就会惩罚我们。”
“你们相信共产党吗?”医生也直截了当地问。
他们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曹加回答说:“相信。”
“那么你们就得相信共产党派来的医生的话!”李贡解释着说:“你们治病要恢靠共产党,你们将来的举福也得依靠共产党。曹加,明天收拾好你所需要的东西,到我的帐篷里来吧。我再一次用我的脑袋向你保证,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共产党派来的人从来不说假话的。”
“好,我明天一定来!”曹加肯定地说。但不一会儿她又有点动摇了。她半信半疑地问:“医生,你真的能完全治好吗?”
“一定能!”李贡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明天一清早在帐蓬里等你。”
就在这天晚上,李贡在自己的帐篷里准备了一张临时病床,并且也准备好了剪刀、麻药和消毒剂。当他最后爬上床打算去睡的时候,他的心忽然剧烈地跳动起来。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手术,而且也从来没有用剪刀剪过自己的皮肤。假如他的手临时抖起来了,假如他的手术做得不成功,那将又怎么办呢?他将怎样对病人交代呢?怎样对群众交代呢?那时政治影响之坏,将不堪设想。但是转念一想,如果他被这些顾虑吓倒了,那么政治影响岂不是更要坏吗?党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是应该具有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的。自己是根据科学办事,并不是迷信,有什么可怕的呢?
但是为了使自己镇定,也为了使病人镇定,第二天病人来到以后,他立刻就叫她在病床上躺下来,并且用消毒布把她的面孔蒙住,同时一再叮嘱她,不许她揭开消毒布偷看。然后他坐下来,在自己的腿上打了麻药针。过了一会儿以后,他就拿起那把消毒过的长剪刀,向自己腿上的皮肤剖下去。很好,他的手没有发抖。但是当他快要剪下头一块皮的时候,病床上忽然发出呜咽的哭声。原来曹加私自揭开了消毒布,一直在偷偷地观察。她一时控制不住自己难过而又感激的心情,就哭出声来了。这时医生的腿上鲜血淋淋。说来也奇怪,他不但没有惊惶,而且感到十分镇定,他一面把剪下的皮放进生理盐水中,一面尽快地包扎自己的伤处,同时向曹加发布命令:“不准你再偷看。”接着他又迅速地从自己的腿上剪下了三块活皮。没有多大一会儿功夫,他就把这四块从自己身上割下的皮肤,移植到达位受苦将近两年的藏族同胞的伤口上。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的手术作得那么敏捷、干净。事后他回忆当时思想,他所以能够保持镇定,完全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给了他勇气和信心的缘故。
三天以后,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慢慢地揭开曹加的伤口,他一看就出了一身次冷汗,同时也打了几个寒颤。这三天以来,他日夜所担心的那件事情,终于不幸的发生了;那移植的四块活皮已经死去了三块。他最后的一次努力显然是失败了。这时他心里所感到的刺痛,比针扎还要厉害。要不是由于曹加面上浮现出了一种微笑和镇定的表情,他几乎当场就要昏倒了。曹加和这位年轻医生已经建立起了感情,并且也知道他对藏民确是非常诚恳,因此她从心眼里相信这次他一定会治好她的病,这种乐观的心情恢复了她的青春活力,而那几块移植的新皮也对伤口起了有益的刺激作用。那几处腐烂地方的新陈代谢因而加速,并且不到二十天工夫新的肌肉就生好了。伤处最后收口了。这种变化是我们这位年轻医生事先没有料到的。
曹加的伤势全好以后,她和她的丈夫送来一头肥大的白绵羊。
“请你代表毛主席收下这头牲口吧,”他们齐声说。“他是穷人的父亲。这块草地上从来该有谁能象他所派来的医生这样不辞劳苦地为人治过病。”于是他们神光焕发地望着这位年轻医生,激动地说:“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父母所生,但是我们的心连着心。”
我们的年轻医生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来回答。他只是紧握着他们的手,他能感觉到他们心脏的跳动。他们三个人的确是心连着心。
1958年甘南藏族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藏族牧人牵着一匹他所心爱的骏马来投奔我们的解放军,他成了我军一个非常能干的向导。叛乱平复后,他又单枪匹马,到各地说服叛匪招他们归降。他一连招降了四批。在第五次招降的时候,他不幸遭到土匪的暗害,我们的解放军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一个年轻牧女站起来讲话,她说:“他死得光荣!我很骄傲,我们藏族出现了这样一个
勇敢的爱国的人!”这个牧女就是他的妻了曹加。她现在是欧拉公社的社员。和医生李贡一样,她现在也是我们伟大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积极分子。
(原载“新观察”1959年22期)
(作者附记)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新华社8日从兰州发出的电报,说李贡医生在去年参加甘肃省慰问野外工作人员代表团赴刘家峡工地慰问时,不幸于12月29日失足落水淹死。我感到十分沉痛,这样一个热情饱满、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突然遭到不幸的意外,对我们的人民和党说来,这的确是一个损失!
李贡同志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非常普通的年轻人。去年十月群英会期间的一个夜里,当我到北京郊外一个招待所里去访问他的时候,他还在开会没有回来。我当时呆呆地坐在接待室里,就漫无边际地想像:这个驰骋在茫茫草地上的年轻人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会不会像我们经常在电影和小说中所见到的那种传奇式的英雄呢?当他走进来和我握手的时候,我站在他面前;情不自禁地把他观察了好一会儿。和我的想像完全相反,他是一个极端朴素、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他的面孔,由于在草地上长期风吹雨打,已经变得颇为黝黑。如果我们不看他那蓝布的制服,我们很可能把他当作一个年轻的藏族牧民。他就是以这样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藏放牧人中间不分寒暑,不分昼夜地到各处巡回治病,解除那些贫困藏胞的痛苦,带给他们幸福,带给他们党和毛主席对藏族同胞的爱和关心。是的,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所做的却是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
当我仔细端详他的面部表情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在这个医生的身上我看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的特征。他是一个充满了美丽的幻想和热爱生活的人。正因为他热爱生活,所以他才满腔热诚地走向生活。我想这里最好引他自己的话:“我到玛曲不久,领导上就分配我到帐圈巡回医疗。我看到了牧民们为牧主终年放牛放羊,而终日不得温饱;个别所谓‘活佛借穷人重病问卜求医的机会,大肆剥削欺弄,有的甚至因为没有油水可榨,而拒绝为牧民算卦,牧民只好拿命硬抗。想到贫困、落后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的时候;想到党对我多年来精心培养的时候,感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不仅仅是救死扶伤,把藏族同胞从贫穷和疾病中解救山来,更重要的是一场政治斗争。”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山李贡是一个高度有原则、有党性的人。这是毛泽东时代青年人的一个特征。
这样的人,不难想像,自然也是非常勇敢的人。1958年藏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的时候,组织上分配他到部队里去做救护工作。有一位战士胸部负了重伤,喉咙里堵满了血和痰,呼吸不上。他当时眼看病人呼吸将要停止,就毫不犹豫地用嘴对着橡皮管,将他的痰和血全部吸山来。去年五月间,草地上发生了班疹伤寒。当时药物缺乏,病情严重,他在治疗病人时自己也染了这种病。他的病刚好,他知道他自己的血液中还有多量保护抗体存在,因此他就把自己的血抽出来给十几个重病人施行血液注射,使他们很快地解除了疾病的折磨,恢复健康。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那些自私自利的人看来,也许显得很“愚笨”;但在我们看来,它显示出一个多么高尚的灵魂。
在我对他的访问完毕以后,我又再次观察了一下他面上的那种严肃的表情和那对充满了想像的、深思的眼睛。我想,这个年轻人不仅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英雄,也是一个诗人。他的理想是一首诗,他的生活也是一首诗。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首伟大的诗篇。因此在我和他告别以前,我问了他一个在现在看来有点近乎傻气的问话:“你在那辽阔的草地上最喜爱的是什么东西?”
他作了一个微笑。
“我最喜爱的东西是看到人民的事业不断地发展和党的政策不断地胜利。”他说。为了怕我不懂得他的意思,他又进一步解释着说:“在那一片曾经是荒凉的、被中世纪的迷信所统治着的草地上,在那些几世纪以来一直被贫困和各种病魔威胁着的藏胞中,解放后不到十年工夫,尤其是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已经出现了人民医院一所,卫生所14个,各极卫生人员120余人,病床90余张。卫生事业遍地开花了!”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然后又用非常明确的语气接着说:“同志,开花了!”
开花了!这三个字是多么简单,但是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意义。他念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就真像念一首诗。我知道,他那时感到多么光荣,多么幸福,因为他,作为党所培养出来的一个园丁,能有机会在那个荒凉的草地上为撤下这些花种而尽一份力量。生命有时可能是短促的,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生命所播下的种子永远不会灭亡:它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会生长发育,开出一天比一天更美丽、更茂盛的花。李贡同志富有创造性的一生不仅鼓舞我们前进,也启示我们,怎样使我们的生命开出同样灿烂的花。
1960年元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