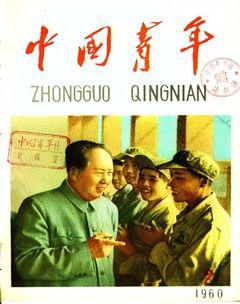黄浦江畔的风暴
徐景贤
四、火车头
早晨,初升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枝,投射在交大校园里的石子路上。老章迈着轻快的步子顺着石子路向大草坪走去。他走到南院合作社的门口,站定下来,撩起长衫下襟,把两手插在裤袋里,看着在草坪周围来来去去的同学们。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光采,注意地向四处张望,仿佛在寻找什么人。
今天是1947年5月13日,校园里和往常大不相同,显得分外热闹:有的人忙着把铺盖集中在一起,有的人忙着编队,还有些人蹲在草地上贴蓝布横幅,那横幅上写着:
“交大师生员工晋京请愿团”。
自从国民党在晋南、豫北罩事失利以后,便想克扣更多的教育经费和其他经费用来打内战,交通大学成了它们开刀的一个对象,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停办交大的航海、轮机两系,还要取消一个学院。消息传来,全校帅生员工对这种摧残教育事业的行为一致表示愤慨,派出代表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交涉,还是没有结果,群众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交大党的地下组织经过研究,觉得这次事件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时机很好,可以通过这次事件对国民党来一个冲击,揭露它的腐败,提高群众的觉悟。因此,由学生自治会召集系科代表大会辩论决定:5月13日全校学生进京请愿。今天一清早,各班级同学就忙碌地进行准备,开始集中了。
老章站在原地看了片刻,好像发现了他所要寻找的对象,就徐步向草坪中央的大旗杆走去。当他走近旗杆的时候,从旁边闪出一个身材瘦长的高个子,一头蓬松的乱发堆在头上,长方脸上架着一付黑色的玳瑁眼镜,大概因为人长得太高了,脊背有点弯弯的样子,完全是一付老成的大学生风度,这便是学生自治会主席老胡。
他们两人微微地打了一个招呼,便并肩向僻静的地方走去。走到人少的所在,老章光开腔了,他的声音和往常有些不同:
“今天学委①的负责同志亲自到我们这里来指挥战斗了!我刚才已经和他接上头,他现在正和同学们在一起,随时都可以和他取得联系。”
老胡听了也很高兴,党的领导和他们是这样地贴近,心里对今天的斗争就更加有信心了。老章义接下去说:
“依我看,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学都发动起来了,声势很大,K.M.T .②有些发慌。但是,多数同学的认识还停留在保卫交大完整这一点上,有些人只是激于一时义愤,因此还不太巩固。”说到这里,他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要从政治上提高同学们,要通过这次事件揭露K.M.T.内部的腐败,戳穿他们克扣教育经费用来打内战的阴谋,揭发他们进行派系斗争牺牲教育事业的真相,这样就把我们的护校运动和社会上的反内战运动结合起来,相互影响,相互推动,我们的斗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老章传达完了党的指示,他们又略为商量了一下几个具体问题就此匆匆分手,老胡急忙赶去指挥大队的行动了。
七点多钟,全校一千八百多个同学都在大草坪上集合;有些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和学校里的部分职员工友,都杂在学生队伍里。从校门口到图书馆一路上排着几十辆大卡车,这是总务组的同学从搬场汽车公司叫来的。穆汉祥提着一架大明速印机站在队伍的头里,他今天但任了快报编辑的职务。
大家正待上车,从上院阳台上的扩音器里忽然传出一阵叫喊声:
“同学们,同仁们,请慢一点定,现在我们的校友,公用局赵局长要来作调停!”
接着,有一个穿西装的人取下了他的礼帽,站到了扩音器前。远远望去,只见他的秃顶在太阳光下象一个电灯泡似的闪闪发亮。他咳嗽了一声:
“各位,我也是交大毕业生,和同学们有先后同窗之谊,承蒙各位师长教诲,我当然是维护交大利益的,不过,各位也要体察国家的困难,不可造次,象这样的集体请愿,实在是……”
他说到这里,只听得四面一片嘘嘘之声,便赶紧改嘴:“噢,噢,我今天受命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教育部已经答应只要大家不去请愿,一切问题可以从长计议,我以校友的身份担保,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草坪上的同学都嚷起来:
“倒底答应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说话干脆些,不要浪费时间!”
这时,只见学生自治会主席老胡在阳台上跨前一步,对同学们做了一个不要吵闹的手势,仙说:“同学们,静一下,听听这位校友替我们商量出了些什么结果,听听他准备怎样为母校效劳。”
“兄弟愿意为母校鞠躬尽瘁,鞠躬尽瘁……”这个赵局长一面不住地用手帕揩着他的秃头上冒出来的汗珠,一面果然对着扩音器连连地鞠起躬来,全场哄然,他慌忙接下去说:
“噢……噢,我刚才和朱部长通过电话,他已经答应不取消轮机系,不过,限于经费,可能暂时设在造船系下面。其他问题,请你们再派代表面谈……”
“等于白说!”
“不要给我们吃空心汤团!”
草坪上的同学又愤怒地嚷起来。
老胡拿过扩音器,讽刺地说:
同学们,我们十分感谢赵校友的鞠躬尽瘁,可惜我们的代表团已经和教育部谈判过五次之多了,结果总是八个大字:“经费不增,系科裁并”。我们学校每月实际开支五千万元,教育部却只核发一千万元;我们学校经过部里核准的教职员有四百六十三人,但是每次只发来三百零二人的工资,这还象一个认真办教育事业的教育部吗?”老胡用严峻的眼光扫了一下站在旁边发怔的赵局长,他一字一句锋利地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克扣教育经费的真相:“我们要问:政府是不是收入太少发不出教育经费呢?不!最近国家的军事预算支出增加了两倍,原来办教育事业的钱都用在打内战上了!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行动不只是为了争取一个交大的完整,我们是在为全国所有的学生和老百姓向政府请命啊!”
老胡的话刚说完,草坪上的人们已经象潮水一样涌上卡车,有的人边走边喊:
“快上车,到南京向政府请愿去!”
“我们要读书,我们不要打内战!”
一下子,几十辆卡车的发动机全部响起来,一辆接一辆地向校门口疾驰而去,赵局长在阳台上绝望地叫喊着:
“同学们,请等一等,吴国镇市长就要来了,我们要顾全大局……”
他的喊声淹没在发动机的吼声里,谁也不去理他。穆汉祥从第一辆卡车的车厢里伸出手来,向阳台上挥舞着,高高兴兴地喊道:
“再见!你的缓兵之计破产了!”
车队象一支铁流一样浩浩荡荡地驶出校门。忽然,迎面急驶过来一辆流线型汽车,在校门外石桥边停住,车门打开,从里面急匆匆地跳出一个人,头戴礼帽,身穿大衣,肥胖的脸上架着眼镜,这是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吴国桢看见大队卡车冲出校门,知道自己来迟了,索性要出无赖手法,他往石桥中央一站,叉开双腿,举起手臂,一只手里挥着手杖,想用“苦肉计”来阻止队伍前进。
这时,老章从司机背后的小窗孔里望出去,看得真切,时间紧迫了,容不得丝毫犹豫,他果断地对司机下命令:
“朝他冲过去!他不走的话到他面前来一个急刹车!”
卡车吼叫着朝吴国桢冲去,距离还剩下好几米,这个脓包市长的“英雄”架势马上就垮下来了,他的肥胖的身躯忽然变得灵活起来,他很快向旁边一纵,靠在桥沿上。这下子司机当然不怠慢,放开刹刹,一踏油门,卡车加大速度朝前开去,象一阵风一样掠过吴国桢的身边,把这个怕死的“英雄”吓得脸色煞白。车上的和四周的人都哈哈大笑,在笑声中,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去远了。
这列象长龙一样的车队开进北火车站的时候,站上已经实行成严,除了武装的警察以外空无一人,铁轨上也是空荡荡地,既没有车头,也没有车厢。主席团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找站长办交涉。这时,宣传组活跃起来,在候车室门口,用两张板桌临时搭了一个小戏台,山茶社的两个同学上台合演一出“双簧”:演员鼻子上擦了白粉,点头哈腰,一面连称“兄弟愿意鞠躬尽瘁”,一面却偷偷地把钞票从“教育级费”的小箱子里掏出来,放进“内战费用”的大箱子里去。这付模样,正是那个当众山丑的“校友”赵局长。
同学们围观着,哄笑着,穆汉祥在人丛里挤来挤去,散发刚刚出版的第一期“快报”。“快报”上有他在五分钟内赶面出来的一幅漫画:“螳臂挡车”,画面上是一只大螳螂,长着一颗人头,肥头大耳,礼帽眼镜,寥寥几笔,活象吴国桢。这个“螳螂”举起胳臂要想挡住向他滚来的大车轮,看来免不了落想一个粉身碎骨的下场。这幅犀利的漫画受到很多人的赞赏,穆汉祥听了很高兴。他发完快报,又急急忙忙地想去赶印第二期,刚走到候车室门口,迎面碰见老章,老章一把抓住他的胳臂说:“汉祥,就用你的画笔去作战吧,它是很有力量的武器哩!”
他们两个人一路走着,忽然在月台上有一群人吵嚷起来,他们急急跑过去,只见当纠察的电机系的李胖子揪住一个人,厉声责问他:
“你是什么人?你敢骂交大学生是暴徒!”
“骂你怎么样?我是市党部宣传处处长。”那个人瘦瘦小小的个子,梳着西式分头,蓄着短发,鼻梁上架着一付银丝服镜,他被胖子始在手里,好像老鹰捉小鸡一样,但他还是挣扎着装出一付强硬的样子。
周围围拢来的同学愈来愈多,大家上分气愤:
“市党部的处长就可以乱骂人吗?”
“叫他解释,什么叫暴徒?”
那个人强自镇静,把头一扭,做出一付傲慢无礼的模样,两顺眼珠在镜框后面转来转去,拼命在找附近有没有可以解救他的警察,嘴里还咕噜着:“识相点,当心吃官司!”
“什么?你骂了人还要别人吃官司!打他!”后面有一个同学激愤地喊起来。
“打他!”“打!”“打!”穆汉祥也跟着大家嚷。
胖子一把抓住这个坏蛋胸前的衣襟,围着的人群往前跨了一步,大家拔出拳头,圆睁双目。那人看见形势不对,吓得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口气马上软了下来;
“咦,咦,对我动手算啥?这话又不是我说的。”
“什么?不是你说的?刚才说了还想赖!”
“打!”
“打!”
这时,老章从人从里挤出来,向大家摆了摆手:
“同学们,先别打他,要他讲是谁骂我们交大学生是暴徒。”
“对!”“对!”“讲!”“快讲!”
“哼……哼……是潘公展讲的……潘议长讲的。”
“胡说!”胖子发起火来,”潘公展今天又没有来,他在哪里讲这种话?”
“哼……哼……是他讲的,他前天在我们市党部开会的辰光讲的,我亲耳听到的……”这个家伙急于为自己开脱,把底子都供了出来。
“潘公展是堂堂上海市议长,他说话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我们要公开和他评理。杀人放火的不算土匪,搜括民脂民膏的不算强盗,难道我们学生要求读一点书就算暴徒了吗?”胖子声色俱厉,把那人问得哑口无言。
“要他把这句话写下来!”老章在旁边点了一句。
“对,要他写下来!”旁边有的人递来了纸条钢笔。
“这个……”那人用讨饶的顺光望着大家。
“写!”“写!”“不写的话要你负责!”大家丝毫也不肯放松。
他只好拿起钢笔,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一行大字:
“潘公展说交大学生是暴徒”
胖子还不肯饶过他,往纸上一指,说:“写上是你亲耳听见的,签名。”
那人迟疑了半响,看看大家围得象铁桶似的,他拿钢笔的手吓得簌簌发抖,只得低头再写:
“此话是我亲耳听见。”下面署名:“曾虚白”。
胖子收起纸条,松开手,一字一句地对那人说:
“回去告诉潘公展,要他在报纸上公开答复!”他向同学们挥一挥手,“放他走!”
旁边的人让出一条路,那人口里应着:“是,是,对不住,对不住。”脚底象擦了油一样,滑脚便走。大家嘘了一阵,纷纷议论着散去了。
老章要胖子把纸条交给穆汉祥,并且谨慎地嘱咐他:
“这是你们快报的头条新闻,按照他的笔迹刻印出来;原件好好保存,等一下我们还要开记者招待会派用场呢。他们表面上装着和我们谈判,实际上早在背后密谋破坏我们,我们要警惕地团结起来,揭露他们的阴谋,提高更多人的觉悟,使大家对他们不再存在什么幻想。”
穆汉祥领悟地点点头,他觉得自己在这场斗争中间,学了很多东西。
学校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和站方交涉了半天,毫无结果,站长推说没有机车,同时通知沿途各站不放列车进上海站。主席团在候车室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有人主张找校友,因为铁路局负责人有不少是交大出身的。老胡背后找老章个别商议了一下,老章提出了新的主张,他说:“找校友的办法可以试一下,但是他们是靠不住的,当我们的行动触犯到他们的阶级利益的时候,校友的情面就顾不得了。我看我们应当去找找铁路上的工人弟兄。”
老胡把老章的建议作为自己的意见在会上提了出来,博得了大家的赞同。散了会,老胡马上带领了由机械系和铁道管理系同学组成的驾驶小组,直奔机务段。在路上,他们碰到一个拿着小锄头的老工人,大家向他说明来意后,他一言不发,翘起左手大拇指朝后一指,把同学们带到一所大库房的旁边。大家往里一瞧,嘿!那儿稳稳当当地停着乌溜溜的火车头。
大家兴高采烈地一拥而上,有的加煤,有的加水,在老工人的指点下,这座火车头终于隆隆地开动起来了。他们在不远的地方挂上了车厢,向站台驶去。
在站上的同学们正等得焦急,忽然听见远远传来“鸣——鸣”的汽笛声,大家挤到月台上望去,只见一列长长的火车“呼哧、呼哧”地喷着大气驶进站来了,老胡从驾驶室里伸出半截身子,热情地向大家挥着帽子,他用手把汽门一拉,火车又“呜——呜”高叫了两声,好像在向同学们致敬,又好像在向敌人示威。这时,一千八百多人齐声欢呼起来,汽笛声、欢呼声汇成一片,把屋宇都震动了;这声音,把站在月台入口处的国民党警察头子和车站站长吓得目瞪口呆。
穆汉祥在人群里兴奋得蹦跳了几下,他又和左右的同学拥抱在一起,接着,他提起油印机,夹着白报纸,抢先跳上列车。一进车厢他就把白报纸铺在角落里,提起蘸饱了墨汁的毛笔,飞快地画起画来。一瞬间,一座雄伟的火车头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在火车头上写着几个大字:
“交大万岁!”
他拿起这幅墨迹还没有干透的画,跳下车去,奔到前面,爬上车头,把这幅画牢牢地贴在热呼呼的车头上。他的心激烈地跳动着。这时,老章走近他的身边,用坚定的声音说:“对!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应当做火车头!”
不管站长的拼命阻止,也不管警察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火车终于轰隆轰隆地开动了。同学们坐在车上激昂地呼着口号。
“进京请愿是合法行为!”
“反对用教育经费打内战!”
“保卫交大完整!”
火车缓缓地驶出上海市区,穆汉祥从他的油印机前面抬起头来,车厢外是一片明媚的春光,车厢里的同学随着火车的节拍放声歌唱:
我们是姊妹兄弟,
大家团结在一起,
不分我,不分你,
一条大路把手携。
………
穆汉祥起劲地摇起他的大明速印机,小周在他对面把印好的快报整齐地折叠起来,他们对视了一下,焕发的脸上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他们随着大伙一起唱了起来。
火车行驰了不多久,忽然速度缓慢下来了,接着“吱——”地来了个急刹车,车前闹哄哄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家正在焦急地探问,广播器里传出了主席团的命令:
“同学们!前面的铁轨被破怀了!我们的列车暂时停驶,但是我们一千八百人的意志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主席团号召全体男同学在土木系带领下抢修铁轨……”
话还没有讲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前拥去,连女同学也不甘留在车上。敌人原来是想拆去了一段铁
轨一定能把大家阻挡住,乖乖地回学校去,谁晓得来了那么一群不怕麻烦的学生,里面还有懂得土木的“内行”。人多势众,你搬枕木,我铺铁轨,他敲道钉,不消片刻就把一段撬掉的铁轨修复了。主席团一声命令,火车又乘风前进,这下子才真正把南京的“国民政府”震动了!
火车开到真如车站附近,敌人第二次又把路轨破坏了,这次破坏得相当彻底,他们把一长段铁轨撬起来都丢在旁边的河里,生怕同学们再来一次筑路运动。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也急急忙忙地从南京赶来了,他和主席团的同学在车站附近正式进行谈判。
天色黑下来了,谈判还没有结果,同学们都在火车里等待着新的命令,大家起劲地唱着歌。朱家骅恐怕事态扩大,只能答应暂时不取消航海系和轮机系,至于其他增加经费等要求,他坚决不肯让步。老章和上级党委派来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觉得请愿的目的基本上巳经达到,同学们通过这次事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教育,再僵持下去敌人可能会进行更大的破坏,这洋反而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决定同意主席团和朱家骅订立初步协议。
夜深了,广播器里传出了老胡的激动的声音:
“同学们!谈判的结果教育部答应不取消航海系和轮机系,我们的请愿取得初步胜利了!我们回到学校里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胜利。交大万岁!”
“万岁!”“万岁!”一列车的人都欢呼起来
穆汉祥站在车窗前,听着同学们的欢呼声,他心里特别地感到不平静。车窗外的沉沉夜色,和他1946年乘火车去上海时并无两样,但是他此刻的心情却和那时大不相同了,他不再觉得优郁和孤独,也不再感到前途茫茫。他意识到只要大家组织起来,团结得象一个人那样,就一定能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老章的话不断在他的耳边回响:“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应当做火车头!”这时,他忽然想到:今天的这场斗争一定也有一个火车头,卡车队出发前的遭遇,火车站寻找车头的经过,国民党市党部处长丑态的被揭露,和朱家骅的谈判……这一切都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越发肯定:有一个火车头在正确地引导着。这火车头是什么?他想起老章借给他的“群众”杂志上的一句话:
“领导全国人民去争取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就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对,这火车头一定是中国共产党!想到这里,他眼前陡地一亮,在这沉沉夜色里,他第一次看到了光明!
(未完,待续)
注:(1)当时地下党委领导学生运动的组织。
(2)K.M.T.隐语:国民党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