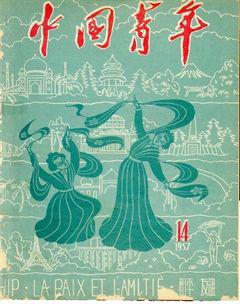春假所见
(一)
一个雨后的清晨,我站在大门口的水渠旁边。忽然听到:“喂!志亭,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我们乡上的大个子党支部书记——萧文康,在那斜对面的墙角子里面,一上一下不知在干什么?
“嗨!萧书记,是你啊!我是昨天下午来的,你为什么在这儿解大小便,浪费了肥料!”我开玩笑地,一边说一边往他跟前走。
“不是的,这附近的一些小孩子经常在这儿大小便,我来收拾收拾,还准备在这儿砌一个厕所。这回你大概能多住几天吧!”他笑着,亲热地握住我的手。
“噢!这回我们学校建‘五一节带礼拜天,一共要放五天假,可玩个痛快。”
“那等一会儿到我那儿来玩。”他说着便提起大粪筐向墙拐子走去了。
望着他那高大的后影,我强烈地感到:我们的支部书记变了!真的变了。回想去年,咱们的农案生产合作社刚成立的时候,这位支部书记的“官僚主义”作风是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的。他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农村“基本建设”上花费了很多的劳动力,未曾获利,反而使农业社的收入减产。群众一提意见,他就给你来一个:“保守思想”,当头一棒。因而,社员们一提起他,就不高兴地说:“咱们这样人,有啥用呢?只是听着人家的使唤。”但今年的情况看来已有好转了。
(二)
听说,咱乡又买了一部新的柴油抽水机,正在赶着安装,准备浇那盼水的麦苗。
早饭吃过,便领着侄儿去看抽水机。黄河已经看见了,网下土坡一拐弯,便听到抽水机咙!咙!咙!……的吼叫和铁锤敲砸着的声音混成一片。靠近搭着席棚的坑边时,才听见有人在笑着说:“老牟呀!你何必这样做呢?油一把泥一把的,昨天刚来,明天又要走,今天应该在家里休息,休息!让老婆做些好的吃一吃。”惹的大家一阵笑声。偷眼从席棚缝里看去,说话的是一位穿着黑布褂子,蓝裤子,个子不高的胖子,他一面扶着枕木,一面张嘴在笑,显然因自己说的俏皮话很得意。
“咳!看你把话说到那儿去了,人家萧书记都在早晚提着大粪筐头加班,难道我就能在家里呆的住吗?我在家里多住一天,就应该为咱乡多帮一点忙。”
我认出来了,这就是在解放前几年里:头一年失去了母亲,第二年父亲也死了,弄的无法生活,被迫离乡,后来在外面学成了个汽车司机的牟大愚。现在他在城里的一个汽车公司工作。近几年来,咱乡安装或是修理抽水机,牟大愚都出了不少的力。人人都称赞牟大愚这人老实,能够干活,为咱多热心,就在去年给介绍了个好媳妇。
(三)
我顺便走进饲养院,看见那对面槽棚底下拴着两个骡子。我又看见了他——萧书记,他这次可不是提着大粪筐头来饲养院拾粪,而是和我们那“赵院长”抬着一个大筐子,一趟一趟地从马圈里往外抬马粪,并且边抬边说着:“我们前天打来的那些豆子,现有的这几个牲口可以吃几天?”这是萧书记的问话。
老赵答:“足够吃五天。”
“咱们那大黑青骡子,跟这趟车来,就能套到辕里上北路去吗?”
“能去了,自从前天钉了那付掌以后,现在一点也不瘸了。”……
老赵跟支部书记谈的那么亲热。
“怎么?老赵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愕然了。谁都知道,老赵这人,年有四十多岁,干活挺老实,可就是有一个怪脾气;过去他看见那些干部站在院子当中,掏出小本子,“八字”脚一蹬,问这问那,他不但不愿意答复,并且眼里都冒气。和干部说话,也是粗里粗气像吵架的样子。
当我站在那向阳的台阶下跟一些谈天的老汉打了个招呼以后,萧书记已经挟着个小本儿从后门出去走了。
“赵大叔,你老人家的脾气也变好了!”我上前去握他那粗壮的手笑着问。
“看这娃又揭腾起我过去对干部们的那种态度来了。你不知道,我过去生气的是那付臭架子,而不是哪一个人。自从去冬“整风整社”运动以后,我看那些干部们都变了,报纸上登了让领导干部参加劳动生产的号召以后,萧书记可猛的变了;早晚有时间,就帮着捡粪拾柴,在搞工作当中,看见能够做的活,着手就做。就拿到我这儿来说吧!他来了以后,看见我干什么,他拿手就干。有时一面谈问题,一面干活,发现问题,小本子放到大腿面子上就写。人家变了,我也变了,不知乍的,见了面,不但眼里不冒气了,有了问题,也爱跟他谈了。还有,如果收拾果子的人,有时给我一个破苹果,我都想等着跟萧书记分着吃哩!”
(四)
“看!叔叔,那么多的人。”走出饲养院门,侄儿喊了一句。看时,只见前边麦田里有着很多女人在锄草。我们慢慢地靠近,谈话的声音听清楚了。
“哟!秀珍太算不过账了,爱人一月要挣百八十块钱哩!两口儿人,吃啥不够嘛?穿啥没有的,何必这样整天的三股子叠在大日头下受这洋罪哩!再说,昨天爱人来了,今天应该陪一陪,让他好好地休息休息,做些好吃的,好喝的让他吃一吃,不然的话,明天走了你也不后悔吗?”一位穿着蓝布偏襟衫的中年妇女对着一位年轻的小媳妇说。
“你光会说这些话,怎么不看人家萧书记,有闲时间就提着个大粪筐头不肯闲着。眼看新的抽水机就要装好,等着浇水哩!地里草还这么多!”这正是那牟大愚在新年刚结婚的爱人
——秀珍。她虽然这样说,其实,在一个月前就算到她爱人在“五一”节要回来,就给做新鞋,补新袜子……在前几天还割了二斤猪肉,等爱人来了给包饺子吃。因为地里活很忙,这天早上她很早就起来,吃完了饭,准备好了晚上包饺子的东西,二人商量好:一个下地劳动,一个去安装抽水机。
“这才叫里应外合哩!牟哥今天安抽水机,来浇嫂子锄的田禾。”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俏皮地说。
一位鬓间带有自霜的看起来有四五十岁的老大娘说:“秀珍刚才说,咱们的支部书记也拾起大粪来了,那才不是玩哩!还不是哄着把咱们这些人的腰折的早些儿。”
秀珍把扎着两个水缸绣球的辫子向后一甩说:“大娘看你怎么说这种话,人家萧书记一月要积十车肥料哩!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收入,施到地里,能多打多少粮食啊!”
“还不是表面上作样子,去年的事情不是明摆着。”又一位女人接一句。
秀珍着急地分辩说:“那去年是去年的事啊!可不能和今年来比。去年刚开始,他的错误很严重,但是在后来的“整风整社”运动中,上级批评了他,群众给他提了很多意见,指出了错误和缺点,他都能一一接受,并且很快地就改正过来了。今春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他在春耕中间,收集了很多有经验农民的意见,适当地安排了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不是做的都很好吗?目前他又提着一般人都不愿意提的大粪筐带头积肥。在工作和劳动中,和社员们打成一片,他对咱社真是贴心贴意,这样的干部,咱还有啥好说的。现在社员们的劳动情绪不是挺高吗?”
“是呗,人家干部的作风已经改了,我们只有更相信他,何必去翻那老账啊!”另一个年轻姑娘接着说,其他一些妇女都点头回答“对呀,对呀,”这时候那位老大娘也难为情地低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