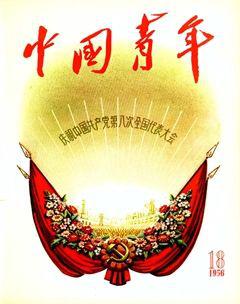偷天火给人的人
曹靖华
毛泽东主席所称的“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文化活动是极为丰富多采的。就文学艺术范围来说,他不但在创作、搜集、编纂、校刊、研究及版画介绍等方面,都作了极出色的贡献,即以外国文学介绍来说,也是一位极伟大光辉的开拓者。
鲁迅说:“路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来的。”在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介绍方面,鲁迅是一位新荆棘辟道路的先驱者。
鲁迅介绍外国文学,主要以日文为根据,有时也参照德文本。
鲁迅的文学活动是以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和结束的。他从1903年译法国儒勒·维恩的“月界旅行”①起,
直到1996年逝世前译俄罗斯果戈里的“死魂灵”止,在
33年中,共译了32种②之多。其中包括俄罗斯、苏联、荷兰、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的作品。约300多万言。从译品的性质说,有小说、剧本、童话、散文、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自然科学等。这300多万言的译作中,俄罗斯和苏联的著作,就占160多万言。这数字占他的全都著述量③的四分之一强。为什么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能引起鲁迅这样注意呢?
这就是:“俄国文学是为人生的”,是“叫喊和反抗的”,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是“火与光”……他怀着火热的心,要借这些反抗黑暗统治,争取光明未来的俄罗斯文学的力量,来启发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鲁迅不论在创作方面或外国文学介绍方面都是如此的。这种积极的为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而奋斗的精神,贯彻了他生平的全部活动。远在1907年他写的“摩罗诗力说”,就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着重地指出了他们的作品是“立志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称赞他们的作品为“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归俗;发为雄声,以超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当年正是要把这种“刚健不挠”,“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介绍到中国来,想借此“疗救”中国人民精神上的病症。也就是他所说的“借他人的酒杯”。他在好多文章中,都重复着这同样的思想。
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回忆到他的文学活动的初期,就想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说他当时“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全集卷5,页106-107)。
在“域外小说集”的序中,也谈到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进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全集卷11,页188一189)。而作为俄罗斯文学主流的“为人生的文学”,就紧紧吸引住了鲁迅的注意。正符合了他所主张的“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他“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他痛斥“为艺术而艺术”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
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鲁迅更明确而肯定地说到,在几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处在黑暗时代里的中国青年,“已经觉得压迫”“痛楚”,他们在挣扎,“在寻切实的指示了”。“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面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
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全集卷5,页54-55)。
鲁迅正是要借俄国文学的火,来照中国的晤夜的。他当时是“肩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他本着这目的,从1908年起,先后就译了安得莱夫、迦尔洵、果戈理、萨尔蒂珂夫、契诃夫、高尔基、阿尔志跋绥夫、契里珂夫、雅各武莱夫、卢纳卡尔斯基、蒲力汉诺夫、法捷耶夫、札弥亚丁、斐定、理定、左祝黎、英培尔、绥甫林娜、略悉珂、聂维洛夫、玛拉式庚、孚尔玛诺夫、唆罗诃夫、班菲洛夫、伊连珂夫、班台莱耶夫以及俄罗斯和苏联其他作家的作品。编校了勃洛克的“十二个”、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唆罗诃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一卷、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聂维洛夫的“不走正路的安得偷”、草拉特考夫的“士敏土”以及瞿秋白同志译的“海上述林”等等。正由于鲁迅的数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坚韧不懈的努力,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在中国反动统治的高压下,“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祝中俄文字之交”,全集卷5,页57)。
中国当年的反动统治者,正是“用秕谷养青年”,用愚民政策,把人民制造成聋子和哑叭,正是用一切手段,把“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堵塞”起来,而鲁迅是要打通这一条“航路”,给读者运送“精神粮食”的。(“由聋而哑”,全集卷5,页325)。
可是这条“输送精神的粮食的航路”并不是轻易地,一帆风顺地被打通了的。因为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同世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一样,把苏联看作洪水猛兽。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从直、奉军阀起,一直到蒋介石,都是如此的。十月革命后,直、奉军阀就明令把一切凡有“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等等字样的书刊,一律禁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更变本加厉,凡有“俄”、“苏俄”、“苏联”、“阶级”、“唯物论”、“辩证法”、“无产阶级”以及凡有这一类“不顺眼”的字样的书刊,都一律被禁止了。连19世纪作家契诃夫的“决斗”也被禁止了。因为在反动统治者看来,“斗争”可怕,“决斗”也可怕。所以当年所有进步刊物上不得不用“卡尔”去代替“马克思”,用“伊里奇”或“乌里亚诺夫”去代替“列宁”,用“普罗”去代替“无产阶级”以及诸如此类的回避反动统治检查的大批的代用语。当年书刊上除了这些代用语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口口口或×××,或者索性开一面天窗。后来连这些口口口,×××以及天窗也禁用了,因为这些要引起读者种种的猜想。从此读者就被投入到闷葫芦里去了。不但这样,当时还禁到书刊封面的颜色。凡红色或黑红两色的封面以及封面上画着锤子镰刀的,也都遭到了禁止。因为这是鲁迅当年喜用的封面,他以为红色象征革命,黑色代表钢铁,所以也遭到禁止,而且还有不问文章的内容,因人而禁文章的。这就是鲁迅之所以用了87个笔名的原因了。有个时期,几乎每篇文章都要换新的笔名,后来连换笔名也不行了,特务认出了鲁迅的笔迹,于是原稿写成后,再着人重抄发出。
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摧残文化上,是走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前边的,他不但禁止苏联作品,连俄罗斯契诃夫和安得莱夫的小说也都被禁止了。于是书店“只好出算学教科书和重话,如Mr.Cat和MissRose谈天,称赞春天如何可爱之类——因为至尔妙伦(H.zurMuhien)所作的重话的译本也已被禁止,所以只好竭力称赞春天。但现在又有一位将军发怒,与动物居然也能说话而且称为Mr.,有失人类的尊严了。”(“黑
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全集卷4,页271-272)。
当年反动统治者不但封闭进步书店,没收进步书刊,禁止进步作家文章的发表,而且对进步作家进行严酷的迫害、捕杀。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等作家,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于1931年2月杀害的。而这次鲁迅如果不是闻风立即出走,也要和他们同遭毒手了。鲁迅在追念他们的文章中说:“在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又说:“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为了忘却的记念”,全集卷5,页85,83)。鲁迅就是在这样漫是的黑夜里,在残酷的血泊中,在白色恐怖的“刀丛”中工作呢。而反动统治者对作家的迫害,正是有加无已。1932年后,更采用了所谓“经济封锁政策”。这就是:禁止书店印行进步作家的书籍,禁止报刊发表进步作家的文章,禁止读者阅读进步作家的文章,以及禁运、禁购等等。这样使作家断绝生活来源,因而困死、饿死。这就如鲁迅所说:“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同上,页83)。
“上有御用诗官的施威,下有帮闲文人的助虐”(“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后记,全集卷18,页824)。当时鲁迅所受的不但是正面的迫害,而且是几面的围攻。他当初介绍俄罗斯的“为人生的文学”的时候,就遭到了“三标新旧大军的痛剿”!这以后,在介绍苏联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的时候,又被人斥为“不甘没落”、“投机取巧”,斥为“不顺”、“硬译”、“死译”等等,要抹杀他这些工作,要把他这些工作“踢开”。事实上,当时那些主强“宁顺而不信”和“误译胜于死译”的人,对鲁迅的围攻,其目标是对苏联文学介绍的。这是进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另一种手法。这一点,瞿秋白同志在
“关于翻译的通讯”里,明白剥露出来了。(全集卷4,页364)。
鲁迅当时无情地剥露这些帮闲文人的面具,勇敢地卫护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是他的最光辉的战绩。当时他对这种以“胡译”、“乱译”为“顺译”的烟幕,是全力扫荡的。他在“几条‘顺的翻译”、“风马牛”、“再来一条‘顺的翻译”、“‘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以及这一类的文章中,指出这些反对者的本质是愚民政策,是在反对苏联文学的介绍,是在帮闲。而这也正说明鲁迅当时介绍苏联文学的重要。尤其是苏联文艺理论著作的介绍。他迫切地感觉到当时的需要,他念念不忘地关心着这些。他反复地吐露着自己的意见:“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文学的阶级性”,全集卷4,页136)。“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绍到中国来”(“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全集卷4,页147)。“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全集卷17,页186)。他在译“文艺与批评”时,特别重视卷末“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他在“译者附记”里说:“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全集卷17,页446)。他概叹于当时可供参考的文艺理论著作太少了。所以“大家都有些胡涂”,他一连介绍了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苏联“文艺政策”等等。他愿大家都看见这些“火和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全集卷4,页222)。
这些文艺理论著作的介绍,武装了进步文艺工作者,使他们有了“解剖刀”,能“刺进敌人的心脏里去”,以便击败敌人。这不但使大家“有所借鉴”,不但澄清了文坛上的混乱现象,而且对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建设,起了奠基的作用。这意义决不是平平常常地介绍几部书而已。这在当时是火热的斗争。这是中国革命文艺占领阵地的斗争。当时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创子手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全集卷4,页270)。鲁迅在1933年11月25日的通信中说:“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给我们没有投稿的地方。我尤为众矢之的……”(鲁迅书简,页512)。在1935年1月26日的通信中说:“检查也糟到极顶,我自去年以来,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于被扣住原稿,接连的遇到。听说检查的人,有些是高跟鞋、电烫发的小姐,则吾辈之倒运可想矣!”当年不仅他的文章受到这样的遭遇,而且还把他加上一个“堕落文人”的恶名,加以盯哨、查缉、迫害。他就在这样白色恐怖的高压下,在御用文人的围攻中,浑身带着血淋淋的伤痕,一面作着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介绍工作,一面进行着扫荡战!“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全集卷13,页378)。鲁迅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卫护了“荒野中的中国革命文艺的萌芽”!
在反动统治者的对文坛横加摧残,各收店都战战兢兢,不敢承印进步书籍的时候,鲁迅从极艰困的生活中,拿出钱来,印行了“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等书。无论如何,他总是要用一切力量,在那“岩石似的重压之下”,要“宛委屈折”地使这些作品“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铁流编校后记”,全集卷7,页805)。使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介绍进
来,传布开去。”这结果,就如他所说的:“近十年中,
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祝中俄文字之交”,全集卷5,页57一58)。
鲁迅当时介绍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作用;诚如他的战友瞿秋自同志所说:“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于像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贡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N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关于翻译的通信”,全集卷4,页360)。
鲁迅就是把介绍俄罗期和苏联文学的工作,当作庄严的革命的政治任务完成的。他把这当作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他曾把希腊神话中的普洛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的故事来比这种工作。他这“博大坚忍”,偷天火给中国人民的精神,贯彻了他的一生,直到不能执笔的时候为止。他最后的一篇文章,就是他逝世前三天写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他逝世前几天写的最后的一封信,还念念不忘地关切到苏联作品的出版问题。
鲁迅用殉道者的精神,用普洛米修斯偷天火传给人类的精神,在当年反动统治的高压下,不顾血腥的迫害,冒着生命的危险,打通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输入中国的“航路”,替中国读者输送了“精神粮食”,在敌人的“刀丛”中奋战了一生。斩荆棘、辟道路,猛烈地扫荡着文坛上的反动腐烂的现象,卫护了“荒野上的革命文艺的萌芽”。二十年后,我们重读当年他写的这样话的时候,心情是不能不激动的:“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介绍,已有富家贤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输,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磁针 将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苏联版画“引玉集”序,全集卷7,页847-848)。
在先驱者鲁迅和他的战友瞿秋白同志所开拓的关于介绍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道路上,在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春光普照的中国,开遍了鲁迅当年所殷切期望的“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俄罗斯,尤其是苏联文学作品,不但成了中国广大读者所最爱的作品,而且成了“生活的教科书”,成了鼓舞我们为了美好的未来面奋斗的力量的源泉!①本书原为法国儒勒·维恩(J:lesVerne,有译为焦士威奴或儒勒·凡尔纳)所著,鲁迅全集误为“美国培伦”。
②其中少数短篇集是同别人合译的。
③现行20卷全集约580万言。
编者注:文内插图是鲁迅当时所编译各书的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