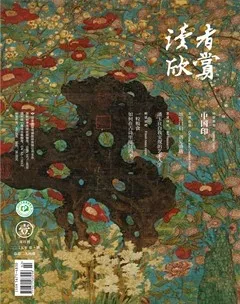《好东西》“新”在哪儿

上海电影的新面貌
近年来,随着以《罗曼蒂克消亡史》《爱情神话》《繁花》等为代表的沪语影视作品的上映,被大量影像抽空能指的上海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这些典型性的地缘影像不仅纵向探索了上海城市叙事资源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也在横向上为地缘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叙事途径。
《爱情神话》通过沪语在电影中的全面回归,生动抒写了这座城市独有的性格色彩,但这份亲切、熟悉、浪漫的影像书写更像是写给上海观众的一封情书。对沪外观众而言,这部电影的“异质感”一方面带来地缘空间上的文化陌生感,但也会加剧“上海它很好,但与我无关”的心理认知距离。因此,如果说《爱情神话》通过极致放大本地“腔调”的叙事策略锚定了上海地域空间的文化,那么《好东西》则提供了“如何更好讲述上海故事”的多元视角。
《好东西》的故事依旧发生在上海,导演几乎放弃了沪语表达,却依然讲述了一个“很上海”的故事。一方面,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富有辨识度的上海城市日常空间场景。电影在上海25处取景,涵盖51个风格各异的点位,其中洋房、街道、小酒馆、咖啡厅、展览馆这些具有鲜明上海城市标识的文化空间,融汇在川流不息的车流、忙碌的生活流之中,形成具象化的上海风土人情。
更为重要的是,电影深入展现了当代上海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向度。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异乡人状态或许才是这座城市情感的最大公约数。影片中铁梅与“小孩儿”多次坦然地说自己是“山西人”,她们不再需要回答关于“上海人”的身份问题,能够自在、自洽地驻足街道、老洋房、天台、摩登天空以及酒吧等上海任意的城市空间意象之中,充分感受这座城市带给自己生理与心理的双重体验。

电影中,作为异乡人的“沪漂”与上海这座城市不再是充满结构张力的二元对立关系,铁梅、小叶、“小孩儿”这些女性角色既是异乡人,也是“新上海人”,她们在工作、情感、学习上遭遇的迷茫与困境,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中三位女性日常出入的场所,以及和她们打交道的人们,共同勾勒出了上海都市人群的生活场景。
影片中,在路边席地而坐弹琴唱歌的年轻人、带有上海人特有的幽默感的门卫保安大叔等群体形象,淋漓尽致地描摹出当代海派风情与都市生活烟火气,与影片的主人公们共同构筑了上海文化多元互动的景观全貌。
由此,“沪漂”与当地人的地域标签消解为都市景观中的“一般大多数”,这座城市与城市里的人们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情感汇合,进而生动折射出海纳百川、大气谦和、开明睿智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当《好东西》不再需要以强烈的“沪语文化”标记上海,但影片的每一处都漫溢出更加浓郁的上海味道时,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更为清晰,上海故事也变得更加鲜活。
当代喜剧的新表达
《好东西》不仅延续了《爱情神话》“讲述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这一主题,同时延续了其先锋话题与喜剧风格,甚至在喜剧类型的演绎上显得更为游刃有余。
《好东西》的喜剧特质首先体现在对人物角色的反差处理上。由于影片囊括爱情、亲情、友情、女性职场与家庭处境、教育理念等新时代人们关注的多元社会议题,因而通过设置不同代际、不同性别、不同人生经历的关系层次,不仅让角色对这些社会议题的探讨显得合乎情理,也为喜剧效果的发生预留了充足的互动空间。
如果把单亲妈妈王铁梅、女儿王茉莉、乐队主唱小叶这三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女主人公经历单拎出来,都能够达到传统苦难叙事的书写预期,但导演并没有选择重复这一叙事,而是放大了三位女性角色性格中的“另类”气质,通过挖掘角色之间互动的化学反应,从而展现超越苦难叙事的喜剧内核。

此外,通过泼水撕衣、比拼吃蒜等诙谐桥段,影片实现了对王铁梅前夫、男鼓手以及眼科医生等男性角色的颠覆性塑造。这些真实鲜活、反差生动的新型男女群像,为影片铺垫出轻松诙谐的基调。
《好东西》里情感丰富、妙趣横生的男女群像,是在高度凝练、精雕细琢的语言艺术中生动呈现的。该片延续了《爱情神话》里那种百无禁忌、短兵相接的语言风格。信息量大、包袱密集的语言文本,配合演员日常生活化的表演,将台词中蕴藏的喜剧能量最大化释放。犀利幽默、大胆前卫的台词不仅承载着社会热点及尖锐话题,也对这些社会议题做出先锋独特、有趣有梗的观点表达。影片中男性角色在讨论“性别文化”议题时,征用“上野千鹤子”“结构性问题”等学术性话术,不仅形成具有反讽意味的幽默感,也展现出语言艺术的思想性,值得反复品味。
《好东西》作为一部以对话文本为核心支撑的“话痨”电影,严格意义上是以情景为导向的喜剧类型(也可视作一种特殊的“情景喜剧”)。《好东西》里密集的台词信息,以每个特定的场景语境实现段落化切分。尤其是影片中几场精彩纷呈的餐桌群戏,通过高度浓缩的“饭桌闲谈”对现实进行换位模仿,“月经羞耻”、性别文化等社会敏感议题得以在轻盈、轻松的餐桌文化中被表述出来。
虽然影片中话锋交互的对白情节不胜枚举,但有关王铁梅为何离婚、小叶对原生家庭的态度立场、小马和父亲矛盾关系的细节等展现,电影尽量保持冷静与克制,选择将现实的面貌隐藏在嬉笑怒骂后的留白之中。导演对语言幽默性与思想性的兼顾,让她开辟出一条有别于开心麻花、宁浩、冯小刚的当代喜剧创作的新路径。
提供观察当代女性生活的新视角
显然,展现当代女性现实生活的不同侧面,关注女性成长话题,是《好东西》这部电影鲜明的特点。
和仅仅简单地将男性气质附加到女性身上,从而提供所谓“女性觉醒”的理想方案的电影作品不同,“女性已经觉醒”才是《好东西》的故事起点。它以三位在生活里面临各种问题的女性角色为样本,为观众提供了观察当代女性生活的多维度视角。
王铁梅就是一位典型的觉醒女性,她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稳定的情绪内核。当王铁梅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母职和外界的评判时,导演又以幽默的讲故事方法,缓解了这份附加在觉醒女性身上的“痛苦感”。王铁梅虽然是母亲,但她可以继续工作、谈恋爱,也能在面对“我为你去结扎”、撕衣服的男性话语、行为时,自在大方地说出自己的不舒服。

同样,小叶自身已然背负各种创伤,但她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在王铁梅、“小孩儿”的身边,也通过王铁梅找到了治愈自己的方法。影片通过一组富有想象力和生命力的蒙太奇对此做出了隐喻性表达:小叶带着“小孩儿”辨识各种声音,“小孩儿” 听到和形容出的各种声音的形式背后,恰恰是妈妈王铁梅生活的琐碎瞬间采撷。影片在蒙太奇的来回切换过程中,不仅让这位单亲妈妈美好坚韧、自由松弛的个人品质跃然纸上,也让三位女性之间的心灵愈发契合。


影片还对男女关系进行了探讨。《好东西》看似以大量性别角色反转的场景来进行“大女主”式的爽感叙事,但在轻松调侃,甚至有些嘲弄反讽的故事推进过程中,不难发现影片中的男性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女性也绝不是完美的化身。影片通过王铁梅前夫、鼓手老师之口,轻盈地点出男性在女性主义语境下虚与委蛇的态度,也善意地指出女性主义本身的局限与困境。
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并不是单纯的“工具人”。无论是认可大男子主义而离婚、之后懊悔的前夫,还是成长于女性缺位的原生家庭的小马,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超越女性主义框架的社会问题。
导演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女性主义从来不是通过压迫一方成全另一方,而是让每一方都意识到整个社会结构性力量对自身的影响,而这是男性和女性需要共同面对的社会议题。

影片最后还提供了“不再玩他们的游戏”的答案。王铁梅可以暂时不做“大女主”,“小孩儿”在做观众和上台表演之间,选择了写作;小叶最终拒绝了小胡医生,与原生家庭和解,做回潇洒的自己。
这些女性角色不再需要通过自身努力打破社会尤其是男性对她们的刻板印象,她们在破除标签、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找到让内心自洽的方式。影片关于女性议题的讨论皆没有定论,给观众留下充足的思考空间。因为一切未完待续的“好东西”,或许都在“等着你们长大后出现新的游戏规则”时,才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