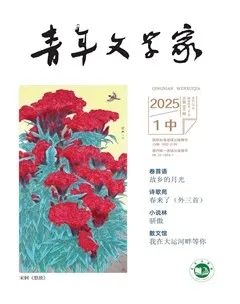论《素食者》中的荒诞与反抗
2024年10月10日,韩国作家韩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韩江的中文译作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于2021年出版的《素食者》。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平凡的女子英惠,在做了一个噩梦后,再也没有办法食用肉类,而丈夫、家人用尽一切方法强迫她继续吃肉,令她不断加剧反抗,最终也没有妥协。2016年,《素食者》获得了国际布克奖。在颁奖致辞时,韩江说:“我在写作时,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我希望《素食者》可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我想通过《素食者》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
一、双重叙述下的素食行为
(一)丈夫作为叙述者时的素食行为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一书中区分了叙事作品中“谁说”和“谁看”的重要问题,即叙事文本中的“叙述声音”是由哪个叙述者发出,谁的“视点”在决定叙事文本。关于“视点”问题,热奈特进行了详细的理论阐述,归纳为自己的聚焦理论。《素食者》主要有两个叙述者,即丈夫和英惠。小说的每个部分中,叙述声音和叙述者相对一致;又采用第一人称的内聚焦叙述模式,叙述视角也与叙述者相符合。所以,笔者认为,《素食者》可以从两个叙述者展开分析,即丈夫和英惠。
小说开篇以丈夫视点切入:“妻子吃素以前,我没有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的人。”第一人称下的内聚焦视角显然勾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留出一定的悬念:他的妻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会吃素?丈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妻子英惠的:“老实讲,初次见面时,我并没有被她吸引。不高不矮的个头、不长不短的头发、泛黄的皮肤上布满了角质,单眼皮和稍稍凸起的颧骨,一身生怕惹人注目的暗色系衣服。”“我之所以会跟这样的女人结婚,是因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同时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缺点。在她平凡的性格里,根本看不到令人眼前一亮、善于察言观色和成熟稳重的一面。”通过丈夫的描述,可以看出英惠是一个平凡无奇的家庭主妇,无论是容貌、穿搭、经历,还是性格,都没有任何让他感到惊奇的地方,这让他感到满意。只有一点,英惠不喜欢穿胸罩,但是她只会在衣服宽厚的季节不穿,并不会被外人发现,所以他大方地允许了。而在某天深夜,他半夜口渴醒来,发现英惠不仅没有睡觉,反而如同梦游症一样站在冰箱前。英惠声称自己做了一个噩梦,这让他感到荒谬,他一点儿也不想关心她到底做了什么噩梦,“甚至一句话都不想说”。第二天,英惠不仅没有为他做好早饭、熨烫衬衫,还把家中昂贵的肉扔出去了,“以自我为中心”“自私、任性”地宣布自己要改吃素;同时,不再与他亲密接触、发生性关系,理由是可笑的“因为你身上有肉味”。通过丈夫的视角和叙述,英惠无疑是荒诞的、奇怪的,明明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前几十年都是一个平平无奇、没有任何特异行为的人,却突然在某一天发狂似的打破规律有序的平静生活,做出令人难以理解的荒诞之事,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一个奇怪的梦。
英惠荒诞的变化让丈夫觉得她是不是得了偏执症或妄想症,甚至是神经衰弱,所以他开始在日常生活中悄悄观察英惠是不是变成了一个神经病,琢磨英惠的家族有没有家族基因病史。英惠暴瘦,心事重重,他也只是冷眼旁观。第一人称的叙述可以让读者清晰感受到丈夫的冷漠和对“不合群”的恐惧,当发现英惠没有熨衣服后,他手忙脚乱,边翻找衣服边打电话给上司道歉要迟到了;在之后和同事的聚餐中,他考虑的也是遮掩和转移话题,以免受到同事的孤立。当英惠回答别人关于素食的提问时,他“突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赶快岔开话,“我太太一直患有肠胃病,睡眠也不太好。但自从听了医生的建议以后,戒了肉才大有好转了”。此处的谎言带着荒唐可笑的意味。英惠明明是因为可怕的噩梦才睡眠不好,出现关于肉的心理障碍,但是丈夫的叙述却将一切因果倒置,仅仅因为他不想让别人察觉他的妻子是一个奇怪的人。
但是,这一切还是未能如丈夫的愿,众人因为他妻子的素食举动,也将他划分成了不合群的一员,“同情我的人偶尔会问我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我知道大家已经开始对我敬而远之了”。而当社长夫人与英惠社交,英惠没有作答时,他刹那间简直惊慌失措,“我觉得妻子的脑袋,我从未进入过的脑袋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深渊”。英惠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者,但因为举动不合乎社会世俗规定,而被打上了这种标签。双重叙述者下的荒诞性其实也是有双重的:第一重是为英惠所表现出的行为举止上的荒诞,但是这种荒诞却是表层的;第二重却是从丈夫这个看似精神健全的人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不合群”和违反社会规范的强烈恐惧和自我约束。英惠不吃肉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几个月,丈夫从未和她真正意义上聊过她的梦魇和心结,一直处在自私和压抑的自我世界中。作者体现出的这种双重性的荒诞最终指向的是现代社会下人和人之间的冰冷和距离。
(二)英惠作为叙述者的素食行为
而当文本的叙述者变成了英惠,英惠用惊恐不安的声音描述了自己可怖的梦境,黑暗的森林里,“恐惧与寒冷包围着我”,“数百块硕大的、红彤彤的肉块吊在长长的竹竿上。有的肉块还在滴着鲜红的血。我扒开眼前数不尽的肉块向前走去,却怎么也找不到对面的出口”。在做这个噩梦前,英惠因为丈夫的催促,手忙脚乱,切到了自己的手指,刀刃瞬间掉了一块碴儿。文本通篇的口吻平淡而克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刀碴儿这个细节,知道英惠应该伤得很严重,“我举起食指,一滴血绽放开来,圆了,更圆了”。而用餐时,丈夫丝毫没有注意到英惠的伤口,“你夹起第二块烤肉放进嘴里咀嚼,但很快就吐了出来。你挑出那块闪闪发光的东西,暴跳如雷地喊道:‘这是什么?这不是刀齿吗?’我愣愣地看着一脸狰狞、大发雷霆的你。‘我要是吞下去了可怎么办?你差点害死我!’”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有人杀了人,然后有人不留痕迹地毁尸灭迹。醒来的瞬间,我却什么都记不得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所有的一切让人感到陌生,我仿佛置身在某种物体的背面,像是被关在了一扇没有把手的门后。不,或许从一开始我就置身于此了,只是现在才醒悟到这一点罢了。一望无际的黑暗,所有的一切黑压压地揉成了一团”。她越来越难以入睡,“连五分钟的睡眠都无法维持”。“我能相信的,只有我的胸部,我喜欢我的乳房,因为它没有任何杀伤力。手、脚、牙齿和三寸之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会成为杀戮或伤害人的凶器。但乳房不会,只要拥有圆挺的乳房我就心满意足了。”
通过英惠的描述,我们看到了二人不同视角下,英惠举动截然不同的意味,丈夫口中的“不过是一个奇怪的梦”,却将她折磨到了这种地步,身心受到重创,日日夜夜活在痛苦、恐惧和不安当中。但是,英惠为什么会不停地做这种杀人的可怕的梦?又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后文中,英惠描述了自己的一段童年经历:家中机灵可爱的小狗因为咬了英惠的腿一口,父亲要将它打死。但是因为听说跑死的狗的肉更嫩更香,他便将它拖在摩托车后活活将它累死。“每当跟它四目相对时,我都会对它竖眉瞪眼。你这该死的狗,居然敢咬我!”“至今我还记得那碗汤饭和那只边跑边口吐鲜血、白沫的狗,还有它望着我的眼睛。但我不在乎,真的一点儿都不在乎。”
“肉”带有极强的象征色彩。现代主义文学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人吃人”现象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人与人之间充斥的是“他人即地狱”的恶意和伤害,基于这种情况,对于弱者的剥削和啃食也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不在乎,英惠怎么会噩梦缠身?又怎么会恐惧自己的牙齿、指甲?叙述者所发出的叙述声音并不意味着客观事实,从小说情节看,在经年噩梦后,英惠内心对童年时屠戮狗、吃狗肉的愧疚和惊恐被彻底激发了。
二、个体对荒诞的反抗
(一)英惠对食肉的反抗
文中有几次具体描写的强迫式的食肉活动。一开始,英惠的反抗是不被察觉的,后来演变为一种以自身行为为表征的剧烈反抗。第一次是英惠和丈夫去参加他公司的聚会时,她面对社长夫人等陌生人的询问和客套,只报之以沉默。第二次是丈夫决定在聚餐后“必须采取些措施”,给岳母、大姨子打电话,说了英惠几个月不吃肉,不让他在家中吃肉的事情,但是二人的劝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哪怕是历来严厉、参加过越战的岳父,也被英惠无视了。这次反抗使得英惠从对陌生人的反抗进展到了对亲人的反抗。第三次是去姐姐和姐夫家里给母亲过生日。这是“妻子娘家历年来少有的大型聚会。虽然谁也没开口说什么,但我知道全家人已经做好了在当天斥责妻子的准备”。在宴会当天,伴随着姐姐一句看似关心的“那个凉拌牡蛎,是我特意去市场买来给英惠做的。她以前可爱吃了……可今天怎么连碰都不碰啊?”一场“围剿”开始了,无论是关心还是呵斥,众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逼英惠吃下肉,以至于到后来父亲大发雷霆,可英惠只是“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呆呆地看着全家人的脸”。母亲见她一道菜不吃,又夹起一道菜,势必要逼她吃下去。而一贯沉默的英惠终于在这次“围剿”中,“用力往后倾了一下身子”,然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嘴里清晰地拒绝了母亲夹来的肉,说“我不吃”。紧接着是父亲的怒吼、暴打。此处的描写可以清晰地体现出英惠作为一个个体在这场活动中的失语和被动,她根本没有任何权利拒绝。可以说,这幅场景向读者血淋淋地揭开了叛逆个体在面对集体大众时无能为力且不被允许的可悲状态。但英惠没有妥协,她用刀割伤自己,重伤昏迷,被送进了医院。
在英惠住院后,母亲用尽方法,准备欺骗她,“来之前准备的黑山羊汤,听说英惠好几个月没吃肉了,怕她身子骨虚……你们一起喝吧。我瞒着仁惠带出来的,你就告诉英惠这是中药。里面加了很多中药材,应该闻不出味道。你看她瘦得跟鬼似的,这次又流了那么多血……”哪怕是积极融入这个荒诞社会的丈夫,此时也发出如此感慨:这种坚忍不拔的母爱真是让“我”吓破了胆。当英惠尝出里面的肉味时,她将所有喝下的肉汤都吐了出来,并且将黑山羊汤扔掉。母亲责骂、哭泣,劝说:“瞧瞧你这副德行,你现在不吃肉,全世界的人就会把你吃掉!”而英惠仍没有因为这些妥协。
(二)人性的觉醒
躺在病床上,英惠并不觉得自己身体上的伤口有什么大碍,甚至感觉不到痛,“痛的是我的心”,“某种咆哮和呼喊层层重叠在一起,它们充斥着我的内心。是肉,因为我吃过太多的肉。没错,那些生命原封不动地留在了我心里。血与肉消化后流淌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残渣排泄到了体外,但那些生命仍旧留在了那里”。英惠的这些思想活动与开头丈夫对她的描述形成了一种闭环:一个平平无奇的个体。所有人拼命劝英惠放弃素食者的身份,因为食肉意味着合群,符合社会规范,不必被社会当成一个“局外人”排除在外;同时,“食肉”也象征着自觉回归强者的身份,对弱者张开血淋淋的嘴巴,咀嚼生吞。在小说最后,英惠做出了最终的反抗,她拔掉针头,赤裸着胸部跑出病房,嘴唇沾着鲜血,手中紧攥着“一只被掐在虎口窒息而死的鸟”。当丈夫发出询问的时候,她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发出了一句反问:“不可以这样吗?”归根到底,英惠已不打算为了遵循社会冰冷的标准而任由自己吞噬“血肉”,这也是她反抗“荒诞”、不愿被这种社会吞噬的决心。
国际布克奖主席博伊德·唐金评价这部小说:“《素食者》以一种抒情却又撕裂的风格,将柔情和恐怖微妙地融为一体,揭示出强烈反抗对女主人公和她身边所有人的冲击。”生活中的荒诞来源于对人性的漠视,对于英惠来说,童年吃狗肉的经历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在前几十年看似融入社会的平凡生活中,她“咀嚼”了许多鲜活的生命,自己也成了一个同样被他人咀嚼,摄入新鲜血肉与活力之后的“平凡”个体。但是,经久的噩梦让她开始反抗,并越来越剧烈。英惠悲壮的反抗,让我们看到一种人性的觉醒。对爱的渴望、心的慰藉,这才是她反抗的最终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