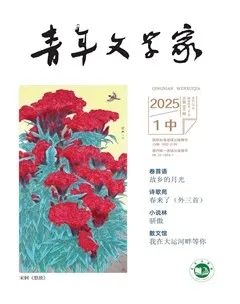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视角下的《蝴蝶梦》
英国小说《蝴蝶梦》的作者达芙妮·杜穆里埃(1907—1989)出生于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著名演员杰拉尔德·杜穆里埃,祖父乔治·杜穆里埃是讽刺画家和小说家。家庭文化的熏陶对她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她的作品以悬疑、哥特式文学作品闻名于世,通常充满神秘、惊悚和心理复杂性,尤其擅长描绘人物内心的焦虑与冲突。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写作风格深受维多利亚时代哥特小说的影响,但她的作品也表现出现代主义的特色。她的作品常常探讨身份认同、爱情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内心的黑暗面。
一、结构主义理论与二元对立
结构主义基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他提出了“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的区分,同时指出语言是一个符号构成的系统,这些符号的意义并非来自其自身,而是通过彼此的关系来定义的。索绪尔这种系统性的观点逐渐影响了文学批评,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如罗兰·巴特和特维托尔·托多罗夫开始应用结构主义思想分析文学文本。结构主义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也是一个符号系统,意义来自文本内部的结构、符号和相互关系,而不仅仅是作品的主题或作者的意图。文学批评家通过揭示文本的深层结构来分析叙事技巧、人物类型、情节模式和象征系统,并通过二元对立分析揭示作品中如何通过对比构建意义,进一步阐明文化中的深层结构。
二、《蝴蝶梦》中二元对立的运用
对《蝴蝶梦》进行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其在人物和空间方面体现了强烈的二元对立。分析这些对立,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小说如何通过这些冲突对立构建其叙事,并揭示出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情感张力、性格、婚姻权利和身份认同。
(一)人物的对立
运用二元对立分析文本,我们发现,达芙妮·杜穆里埃塑造了无名叙述者“我”和丽贝卡,她们是小说中的两位核心女性角色,性格鲜明,是小说中最明显的二元对立。
1.出身性格的对立
无名叙述者“我”出身普通,性格内向,极度不自信。她作为上流社会贵妇范·霍珀太太的“伴侣”谋生,时常以古板拘谨、沉默寡言、缩头缩脑的形象出现。她的胆怯和自卑在小说描述中展露无遗:“一头平直的短发,稚嫩而不敷脂粉的脸蛋,衣裙均不合身,还穿着我自己裁制的短褂,跟在范·霍珀太太的后面,活像匹害羞不安的小马驹。”范·霍珀太太常以高人一等自居,并见缝插针无中生有数落无名叙述者“我”。给范·霍珀太太这样势利虚荣的人作伴,她忍气吞声在所难免。除了忍受范·霍珀太太的专制,地位卑贱的她还得忍受旅馆接待员故意的冷淡,明目张胆的讥笑、挖苦。这也足以说明她因身份卑微而常遭人冷落。
关于丽贝卡的出身背景,小说没有过多的描述,从其贴身女仆丹弗斯太太那里得知,丽贝卡我行我素,生性要强,敢于反叛。在她14岁生日时,丽贝卡与表哥费弗尔争夺马鞭驾驶权并将其抽下马车;在16岁那年,丽贝卡骑了她父亲惯于撒野的烈马,连马夫都认为她驾驭不了,可她愣是稳稳骑在马背上,威风凛凛,“她扬鞭抽打胯下的坐骑,抽得它冒出血来,还用马刺夹紧那畜生的肚子。等她跨下马背,那匹马已是遍体鳞伤,血迹斑斑,满嘴白沫,不住打着哆嗦”。再者,从她与马克西姆结婚后在曼德里庄园的地位,她出色的社交能力,以及她与上流社会人士的广泛联系,我们可以推测,丽贝卡来自一个富裕、有影响力的家庭,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小说中,丽贝卡被描述为美丽、优雅、智慧集一身的女性。她精通社交礼仪,深谙人性,能够轻而易举赢得别人的喜爱。
2.婚姻态度的对立
无名叙述者“我”和丽贝卡对待婚姻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不仅显示出她们各自的个性,还透露她们与马克西姆的关系以及她们在婚姻中的定位。
无名叙述者“我”单纯、胆怯、自卑。她对婚姻有着浪漫化的幻想,希望婚姻能带给她归属感和情感的依靠。但在婚姻中她患得患失,极度没有安全感。她对马克西姆有深深的仰慕,并深爱着马克西姆。她曾表达马克西姆是她的生命,她的一切,“我像个孩子那样,像条狗那样,病态地、屈辱地、不顾一切地爱着他”,并幻想自己能与他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但很快她发现丈夫对她的态度是冷淡的,而且是不透明的。例如,马克西姆专断地为“我”选择能够看见他喜爱的玫瑰园的婚房,可在那房子里“我”却看不见自己当时喜欢的大海;在“我”摔坏爱神瓷像因害怕藏起来时,丹弗斯太太指责罗伯特私藏爱神瓷像,马克西姆却丝毫不留情面,气急败坏地说“我”一点儿不像这家的女主人,反而像不谙世事的侍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西姆和无名叙述者“我”的婚姻并不平等,他从不认真考虑她的感受,也让她的内心变得越发自卑与不安。尤其是在面对曼德里庄园的复杂关系和丽贝卡的影响时,她的浪漫理想逐渐破灭。曼德里庄园的仆人和亲朋好友,尤其是管家丹弗斯太太对丽贝卡持有深厚的敬仰和怀念,让她感觉自己始终被丽贝卡压制,无法摆脱丽贝卡,也无法得到他人(尤其是丈夫)的完全认可。这种情感让她在婚姻中显得极为被动,总是怀疑自己在马克西姆心中的地位。
随着故事的发展,在无名叙述者“我”从马克西姆口中得知丽贝卡可憎的真实面目后,确认他对丽贝卡没有爱,她逐渐从一个不安、依赖的妻子转变为一个更加成熟稳重的伴侣。她开始意识到婚姻不仅仅是关于爱和浪漫,还涉及复杂的现实问题,包括丈夫的秘密、权力斗争以及自我成长。她最终变得更为独立,并与马克西姆形成了更为平等和坚实的关系。
与无名叙述者“我”不同,丽贝卡对待婚姻的态度充满操控性、虚伪和权力斗争。她并不相信婚姻中的情感忠诚或道德约束,而是将婚姻视为一种展示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工具。她从未爱过马克西姆,她认为婚姻就是一桩交易,她提出把荒芜的曼德里庄园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宅子作为马克西姆不干涉她私生活的条件。她藐视婚姻的忠诚与责任。她公然维持着多段情人关系,甚至与马克西姆姐姐的丈夫和管家弗兰克调情。尽管她在外人面前伪装成一个完美的曼德里庄园女主人形象,深受仆人和客人的崇拜,还营造她和马克西姆是最幸福最美满夫妻的假象,但实际上,她不屑于婚姻中的情感投入,而是将它作为个人自由和欲望的工具。她的行为充满了欺骗与背叛。丽贝卡用她的魅力和权力控制了整个庄园,也控制了她丈夫的情感和心理。在查出患有不治之症后,她颇有心计地编造怀孕的谎言故意激怒马克西姆。最终,建立在虚伪之上的婚姻破裂了,并导致了她悲剧性的命运。
无名叙述者“我”和丽贝卡的婚姻态度分别代表了对婚姻的两种极端看法:前者以情感依赖和理想化为特征,后者则以操控、虚伪和权力斗争为核心。丽贝卡的婚姻态度虽然赋予了她短暂的权力,但最终带来了毁灭;而无名叙述者“我”的婚姻态度虽然一开始充满不安,但通过成长和自我认知,她最终找到了自己在婚姻中的真正位置。这种对比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冲突,还揭示了婚姻在个人成长和权力关系中的复杂性。
(二)空间的对立
丽贝卡和无名叙述者“我”不仅在性格、身份和心理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在空间上的对立也非常明显。达芙妮·杜穆里埃通过空间描写巧妙地将这两个女性形象进一步分隔开来,营造了紧张感和对立关系。
1.曼德里庄园—无所不在的丽贝卡空间
曼德里庄园是小说中的核心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也是丽贝卡和无名叙述者“我”空间对立的主要舞台。庄园本身充满了丽贝卡的气息,它象征着丽贝卡的控制和存在,无论她去世多久,她的影响力仍然笼罩着庄园的每个角落。无名叙述者“我”作为新的女主人,从一进入曼德里庄园开始,就感受到庄园对她的“排斥”。她不断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始终被丽贝卡的影子和她在庄园中的印记所困扰。“丽贝卡仍在这幢房子里,在西厢的那个房子里,在藏书室、展室以及大厅上方的画廊里,甚至还在那间小小的花房里—她的胶布雨衣仍然挂在那儿。丽贝卡还在花园里,在林子中,在海滩的小石屋里。走廊里仍回响着她轻盈的脚步声,楼梯上还留着她身上散发的余香。仆人们仍在按她的吩咐行事:我们吃的是她最喜欢的食物,她心爱的花卉摆满各个房间。她的衣饰依然在她房间的衣柜里,她的发刷扔搁在梳妆台上,她的鞋子还搁在椅子下面,睡衣还摊在她床上。丽贝卡依然是曼德里的女主人。丽贝卡依然是德温特夫人。我在这实属多余。我像个可怜的傻瓜,一不小心闯进了这片不容外人涉足的禁区……丽贝卡,无处无时不在的丽贝卡。在曼德里,无论我走到哪儿,无论我坐在哪儿,甚至在我沉思入梦之时,我都能遇见丽贝卡……丽贝卡,丽贝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我永远摆脱不掉丽贝卡。”从文章这段话描述中,丽贝卡留下的痕迹和影响强化了她在曼德里庄园的“在场感”,以至于“我”在曼德里庄园时常感到丽贝卡带来的压抑。因而“我”试图了解丽贝卡的过去,通过模仿丽贝卡,举办舞会等方式,向众人特别是马克西姆证明自己,来弥补自己内心的自卑与无力感。因此,曼德里不仅是生活空间,更是丽贝卡和“我”之间的无形战场。丽贝卡通过庄园继续影响、控制甚至压制新的女主人,形成了空间上的对立和紧张感。
2.无名叙述者“我”在曼德里庄园的空间困境与空间成长
无名叙述者“我”在曼德里庄园中一直感到局促和不适,她对空间的占有感极弱,始终无法完全融入这个环境。她的活动空间主要局限在公共区域和庄园的外围,始终被排除在丽贝卡曾经主宰的私人空间之外。她的卧室虽然名义上是她自己的,但位置布局远不如丽贝卡的卧室,在她心里,丽贝卡的卧室才是“真正的女主人”所应居住的地方,这加深了她的自卑和对自身身份的怀疑。她在庄园中的无名状态也象征着她在空间中的边缘化。她没有私人空间,每当她进入庄园的某个区域,如晨室、幸福谷,都仿佛是在进入丽贝卡的专属领域。通过这种空间上的对立,达芙妮·杜穆里埃进一步展现了无名叙述者“我”与丽贝卡的身份冲突和心理压力。
空间在《蝴蝶梦》中不仅是物理存在,也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丽贝卡生前无疑是曼德里庄园的主宰者、管理者,她的身份与庄园的每个角落紧密相连。而无名叙述者“我”尽管成了新的女主人,但她始终无法和庄园空间建立真正的联系。在她看来,这个庄园依旧属于丽贝卡,而不是她自己的。这种空间与身份的疏离感,使得无名叙述者“我”在整个小说中都处于不安和自我怀疑的状态。她被丽贝卡的空间支配,无法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这也反映了她在婚姻和社会中的边缘化位置:她没有名字,没有身份认同,甚至在属于她的庄园里,她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随着马克西姆的坦白和丽贝卡的秘密逐渐被揭露,无名叙述者“我”逐渐开始掌控她在曼德里庄园空间中的位置。她不再害怕丽贝卡,也不再对丹弗斯太太唯唯诺诺。空间的转变象征着无名叙述者“我”身份的成长。通过接纳和适应这个空间,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在与丽贝卡的无形较量中获胜。虽然曼德里庄园最后在大火中被毁,无名叙述者“我”和马克西姆离开了这个象征丽贝卡统治的空间,但无名叙述者“我”的内心空间已然完成了转变,她不再是那个迷失在丽贝卡阴影中的弱者。
丽贝卡通过她对曼德里庄园的空间占据,保持了对他人生活的控制,而无名叙述者“我”刚开始在空间中的迷失,反映出她在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困境。然而,后来无名叙述者“我”逐渐掌控了她在空间中的位置,这标志着她心理和身份的成长。空间的对立与转变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揭示了小说的核心主题:自我发现、身份认同和对过去的挣脱。
本文通过对小说《蝴蝶梦》中的人物对立、空间对立这两组二元对立项的分析,展示了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困境。无名叙述者“我”在丽贝卡的影子下成长,逐渐找到真正的自我。曼德里庄园作为空间象征着丽贝卡的力量,无名叙述者“我”最终挣脱了这种力量,并开始掌控这个空间。这种对立结构揭示了小说对女性身份、情感困境以及社会规范的深刻探讨,暗示了战胜自我怀疑、走向独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