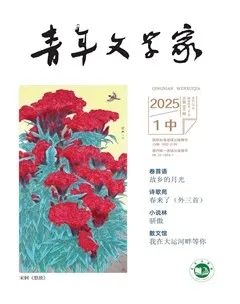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异同对比
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作为初唐时期的两篇佳作,共同展现了诗人对人生和宇宙的深刻思考,标志着唐诗意境的创造达到了新的高度。两首诗都采用了乐府旧题和七古的体式,巧妙地将情、景、理融为一体,语言自然流畅,既继承了吴楚民歌的柔婉清丽,又融入了文人体物细腻、抒情婉转的特点,超越了六朝以来宫体诗的绮靡香泽;两首诗在结构上都采用了嵌套手法,使得诗歌在形式上更加工整对称,情感表达上更加绵密细腻;两首诗在抒情手法上都运用了代言和曲笔等技巧,使得诗人的情感得以含蓄而深刻地传达;同时,两首诗都体现了诗人对宇宙意识的深刻领悟,对生命和宇宙的缺憾进行了哲学性的探讨。
刘希夷和张若虚的作品在初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他们的诗歌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同时代的作品。两首诗都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后世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体验和深刻的人生启示。
一、结构对称意宛转
首先,这两首诗诗意婉转,都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的复沓之美。
刘诗以“花”为主要意象和线索贯穿,开头起兴,中间“花相似”转喻过渡,结尾呼应,“悲”字点题为结,余音缭绕,愁意牵绵。“全诗每句七字,二十六句共用了六个韵,有两句一韵,四句一韵,六句一韵,甚至八句一韵。诗歌句式整齐,韵脚多变,节奏参差错落,宛转有致”(韩黎范《语新·情深·意远—读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更增回环之美、款款怨思。
张诗的五个主要意象“春”“江”“花”“月”
“夜”,共同组成了一幅连环长卷。这首诗前后一共转了九次韵,比刘诗更跌宕错落,丝丝入扣。“从月亮升起,花朵开放,春天来临,再到春天消逝,花朵凋零,月亮下落,有一个很特殊的圆形结构。中国人还相信‘九九归一’,全诗的结构如此不可思议,有一种特殊的完整性”(蒋勋《蒋勋说唐诗(修订版)》),诗境更显幽深。
其次,两首诗都用了嵌套手法,结构工整对称,读来更增绵密的质感,但其中也有不同。
刘诗的嵌套结构是:“今时”内嵌“旧日”,在今人叹落花的时刻,回忆往昔的风流。“此外,诗人还通过今昔对比的方法来写白头翁的过去与现在,明写白头翁,实暗写洛阳女儿,揭示出她的现在正是白头翁的过去,她的未来正是白头翁的现在。”(林启柱《〈春江花月夜〉与〈代悲白头吟〉比较》)
张诗的嵌套结构是:一个现实情境嵌套着一个虚拟情境。在虚拟情境里,诗人写了一对恋人彼此思念,写了一个扁舟子的想象和惆怅;在现实情境里,诗人在江边望月。“而‘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这一句,很好地把虚拟情境和现实情境缝合在了一起”(高盛元《昨夜星辰》),更凸显出“此时相望不相闻”的错位感。
两首诗的嵌套设置,刘诗突出的是今时所见的虚空之悲,张诗则表现的是此时未闻的远别之愁。两首诗回环往复的特色、嵌套对称的结构,为婉转多情的思绪、深邃复杂的宇宙之问奠定了阐发宣泄的空间。
二、主客代位诉情思
诗人主体在两首诗中并没有直接现身。刘诗为代言,是借洛阳女儿之“寄言”来写男女之旧情;而张诗为曲笔,表面写思妇闺怨,实则对面着笔,写的是游子之念。两首诗都是从“男、女两个方面展开的。男女的对立并非偶然,实际上潜藏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阴、阳的对立,‘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阴阳是世间万物的象征,由‘叹人’进一步转到‘叹万物’,感慨时间在整个万世万物的宇宙中都不可逆转。这样的转换,立刻生成出宽广博大、普遍感叹的诗境来”(徐扬《〈代悲白头翁〉的结构主义解读》)。
不同的是,刘希夷在诗中的视角是“故人”,而张若虚的身份始终是“游子”。
刘希夷是旁观者,也是繁华东都里寂寞的故人,仿佛来过这里一遍又一遍,但还是没有人在意过他。他笔下的白头翁、红颜老,都有自怜自哀的意味。“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洛阳女儿和白头老翁显然未与诗人的形象融会在一起,这两个形象仅是诗人创造出来借以融进其人生体验与感受的媒介。诗中的悲伤感情,是一个富有理想、失意坎坷的青年才俊所倾诉的空灵的感伤。”(万建军《〈代悲白头翁〉悲情美赏析》)
张若虚是诗的一部分,在游子身上留下了他灵魂的影迹。他有一个“思”的对象,所以他才不会沉溺于沉重的寂寞中。他漂泊天涯,固然感伤,但是他相信此情终可待。而刘希夷笔下的昔日美少年到了生命的尾声,他写尽了白头翁一辈子的枯荣,曾经那么风流倜傥、裘马轻狂,如今却是无人所知,更多是“不遇”心理的无可奈何。张若虚笔下的游子正处于生命花季、恋情浓时,因此他的口吻更加温柔缠绵,还增加了愿望—“愿逐月华流照君”,这是天真的恋人才会有的心理,这样的生命状态更加饱满浪漫。
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和创作时期,诗人也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不同的情思。故人悲,游子愁,都是一种清丽的感伤。不过,这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一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憧憬和悲伤。诗作尽管带有感伤之情,但终究不失轻快之感;虽有叹息之声,却总带着一份轻盈与洒脱。刘张那种“含泪的微笑”恰是初唐所特有的时代感伤情绪的流露。
三、宇宙缺憾有因果
宇宙是什么?宇宙就是时空。
“从蜣螂转丸式的宫体诗一跃到庄严的宇宙意识”(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两首诗终于造就了初唐诗坛不朽的开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刘张都有意识到“人”,即一个鲜明“自我”在永恒时空中的存在,也同样意识到了“人之情”在宇宙中同样存在,都看到了“相似”与“无穷”的轮回,看到了宇宙和人一样,都是缺憾的“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不知江月待何人,唯见长江东流水”。他们用简短的诗句勾勒出宇宙“公开的秘密”(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其认识却有着显著不同。
首先,刘希夷笔下的宇宙是无意识的,因此才会有所怨,“半为怜春半恼春: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曹雪芹《红楼梦》)。在生命最美好的时候,没有谁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年华的短暂,只有到了最后一刻才感觉到荒唐和幻灭,所以时间和时间里的人一样,都是无意识的。人无法确认今天的自己在未来的时间中会怎么样,也没有意识到时间具体的流逝,只能在参照中去摸索。因此,刘希夷才在诗中写“一朝”“须臾”这样的转瞬即逝,时间的跨度超乎寻常,却又是无情的现实。
而张若虚认为这个宇宙是有意识的,因此才会有“初”,他质问人类和宇宙的起源,以及他们什么时候联系;他也问江月有何“待”,他在这迷人的命题中,大胆构建“人”在这种不确定中的定位,也在思考是否有“中心我”的存在,所以他面对宇宙的浩渺并不悲伤,也不颓靡,他只是错愕,后来就化为江水一样,有种自得满足的平静。他知道这个深奥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他觉得至少人和这个宇宙万物是相互弥补的,是可以产生交流和共鸣的。没有被人赋予过意义的花和江月当然相似,但是人的情感是不同的,情是充满整个宇宙空间的,是可以无限延展甚至和这个宇宙互动和对话的。这就是情的美之所在,也是人确定出自我意义的所在。所以,他超越了恋人和诗人思维,变成了一个哲人。虽然其诗语句简短,但是将“公开的秘密”写给了众人,将人的独立意义公开给了众人,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而不只是如何去活着,从这一点来说,他超脱于芸芸众生,超越了宇宙给人设定的局限,他赋予了人以永恒的意义,赋予了情隽永的价值。
那么,面对宇宙,面对缺憾,人应该怎么办?
刘诗有一种典型化的“警世”的谶言作用。它告诉我们,不论是再美好的美少年,不论是看似年年都开花的桃李,甚至是现在这个唐朝繁盛热闹的东都洛阳,这一切存在于这个时间长河的过程都是“逝”,其结局都是“死”—这就是缺憾,它是无法逆转的事实。用《红楼梦》的主题来阐释,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要永远在盛世之时怀有危机感、清醒感。刘希夷就是把“缺憾”这个残酷而不变的真理摆在那些歌舞声色前,要在衰中窥见盛,要悟出此在非彼在。正如《红楼梦》中的《好了歌》那样,一曲道尽机锋,醍醐灌顶。
张诗中的宇宙,其最大的缺憾就是无法自己给自己赋予“意义”,而只有人可以,虽然人做不到宇宙那样广大和长久。人固然是有缺憾的,但是生命和宇宙本身一样,他们互相羁绊而存在,互相弥补而生辉。这世间唯有真情是那个永不止息的东西,情在人的生死离别轮回中产生,情本身也是一个因果轮回。所以,张若虚是超越的,他也是活在当下的,自然也是哀而不伤的。“诗人其实是将生命现象放到宇宙的共同意识当中,也让我们领会到,只有春、江、花、月、夜是人类共同的、永远的经验。不管距离如何遥远,不管彼此间是否有所关联,我们所拥有的都是同一个宇宙。”(蒋勋《蒋勋说唐诗(修订版)》)因此,没有必要纠结于不可知的宇宙之始,没有必要去定义不可知的宇宙之终,更没有必要去感到人生的绝望。“落月摇情江满树”,唯有眼前人,心中情,携手可珍重,在小小的个体之间,静水流深,生生不息,这样的生命才是丰沛的,这样的宇宙才是完整的。
四、时代新音昭盛世
“齐梁、陈隋,包括唐初,主流的诗歌是宫体诗,很艳丽,但是很颓靡,诗的语言完全堕落下去,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陈子昂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高盛元《昨夜星辰》)然而,刘、张二诗并没有软弱颓靡之感,他们终于跳出了传统的圈子,共同擘画出下一篇章的盛唐。
“这个时期的诗作流行风向是华丽、典雅、歌功颂德的风气,而刘诗所展现的风格则是清新自然、浅显易懂,这与当时的流行风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谷利平《唐代诗人刘希夷的诗体特征研究》)刘希夷“是唐代把感悟人生、体认哲理、与宇宙融为一体的浓郁情思表现为清新、流畅、明丽纯美的诗境的第一个人”(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罗宗强文集》)。但是张若虚比刘希夷更上一层楼,他的力量和格局更加宏大,尽显大唐将至的自信和风度,生命态度更加冲融。
张若虚在写人事、写情的部分恢复了自《诗三百篇》以来的游子思妇主题,他把我国优秀的诗歌传统彻底从艳情诗的堕落深渊中勇敢地自拔出来,使男女间纯真的爱情重新回到圣洁的境界中来。而张若虚之所以能彻底根除宫体诗的劣习,清算艳情诗的罪孽,应该说这同他对宇宙永恒问题的领悟是息息相关、互为表里的。“只有把爱情描写恢复到三百篇和古乐府的传统,它才有不朽的价值可言;也只有认识永恒的哲人才能领会到爱情(而非色情)所具有的永恒意义。”(吴小如《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这是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爱情,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对全历史、全人类的同情心,因此才造就了诗歌的大格局、大气度。
五、结论与启示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其实,在两首诗中,由生命的迷茫感所激起的感情涟漪,由现实的焦灼所生发的心灵花絮,既散发着所特有的芬芳,又洋溢着轻盈生动的气韵,给人以流畅婉转的美的感受,这都是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乐感文化”之体现。儒家认为,要在这稍纵即逝的短暂人生和感性现实中赢得永恒与不朽;如果生有意义和价值,就让个体生命自然终结而无须恐惧。所以说,在本质上,两首诗的审美情感仍是轻快的、清新的、健康的。两位诗人并不重在哀叹韶光易逝,而意在探寻宇宙无限、人生有限的意义和价值。代代追问,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两首诗可谓是同根同源,异曲同工。
因此,时代的积累都是作品共同的养料,没有长期的文化准备,就不可能有这么伟大的作品和诗人。这不是个人才气的表现,绝对是时代已经把很多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包括思想。如果佛学、老庄的思想没有一定的时间,没有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清谈,不会到达这种境界。文字也经过魏晋南北朝文人“四六骈文”的练习,到最后水到渠成。只有整个文化格局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学才能应运而生。我们应该理性看到两首诗重要的文学史和审美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