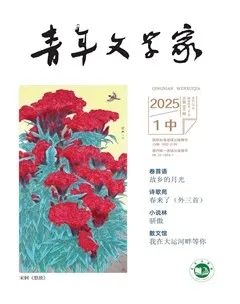保姆的儿子
我的母亲陈文昭,生于1933年3月20日,逝于2022年7月4日。
她生前常说起当年她家保姆娘儿俩的一些事情给我听。
当年我姥爷在开滦煤矿做买办,家境殷实,我大姨一出生,家里就聘请了一个不知姓氏的保姆。保姆有个独生子,叫王文忠,五岁时不幸丧父,寄养在他乡下的姥姥家,勤学上进,懂一些事理,深谙家道贫寒,母亲长年在外不易。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他十四岁时,他姥姥去世了,他在乡下孤苦无依。保姆欲辞去工作回乡下。我姥爷念她勤奋实诚,不偷奸耍懒,老少对她均有所依赖,便说:“不要紧,你把儿子接来,上学的费用你不用发愁,吃住、学杂费有我们开销。”就这样,十四岁的王文忠,从乡下的竹篱茅舍走进了大城市的朱门绣户,踏上了日后的人生跳板。
姥爷膝下两女一子,儿子是抱养的,年纪与王文忠相仿。我大舅眼见家中多个孩子,呆头呆脑,一双眼睛对他戒备谨慎;又见他学习成绩比自己好一大截子,更是火上浇油,总想找碴儿欺负他。
由于王文忠学习成绩好,第一学期学杂费由姥爷出,以后奖学金就够学杂费了。一天,为了羞辱王文忠,我大舅指着王文忠的鼻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成绩好点吗?你别忘了,成绩再好,你也是我家保姆的儿子,我才是真正的少爷,我叫你往东你敢往西吗?成绩再好,能改变你的地位吗?”
此话一出,王文忠的脸由白到红,由红到紫,加上周围一起哄,王文忠的眼神透着无比的悲凉与凄楚,低眉垂目,羞愧无比。
回家见到母亲劳累而平静的脸庞,王文忠再也控制不住,趴在床上声泪俱下,含冤负屈地说再也不去上学了。姥爷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揍了我大舅一顿,骂他再有下一次,就敲断他的腿。
王文忠连日走不出卑怯的阴影,成绩下滑,名次下降。一日,在去学校的路上他转回去取忘带的学具,一进屋门,见母亲松弛的面庞,绷得像满弓般有力,神色寒冷,正盯着他昨天的成绩单出神。王文忠的心像被刀子割了一样痛,喉咙酸酸的,一扭头回校了。
一连数日,王文忠的一双眸子都像秋泓一般深静。他反躬自省,打败自己的除了外部的挖苦讽刺,最重要的是自己内心的脆弱,内心强大的话,外界再怎么嚣张,也是无济于事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面由心起,运由心生。他,痛定思痛,一心用在学习上,把我大舅远远地甩在后面。
过了三年,姥爷因病去世,家道由此中落。加上局势动荡,战乱频仍,王文忠便辍学谋点事做。他投在一家老板门下谋得一个低职,由于勤奋上进,又有学识,稍试身手便脱颖而出,受到老板的赏识,职位不断提升。他的吃穿住行都由老板负责,过年过节才与他母亲相聚。
有一次,一位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的客人来他的部里,同事一看此人穿戴极为普通,都冷眼相待,恨不得那人能滚多远就滚多远。客人走出大门,正好与进来的王文忠擦肩而过。王文忠从他嘴巴紧绷的左下角捕捉到一丝稍纵即逝的轻蔑一笑,便劝住了客人。王文忠从这人的眼神中察觉了什么,便把他领到另一间办公室,不看衣着相貌,只盯他的眼睛,与客人喝杯茶水,又把报纸递到眼前,谈谈时局,聊聊日常,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消除了冷眼相待的怨恨,这才谈到纺织业的本行。原来,这人是江南一位富户,良田广袤,蚕丝颇丰,欲进城找位合作伙伴,特意穿戴随便,只为真心找一位善良可靠的人合作。进了几家店,店家都对他不理不睬的。但他没有灰心,继续找,不想也碰壁了。可没想到,王文忠平易近人,温暖地接待了他。二人一拍即合。王文忠将客人引荐给老板,老板得知真相后,与此人订立了供货合同,达成了双赢。老板自然忘不了王文忠的功劳,视其为心腹和得力干将。
1948年,王文忠携母随老板离开了上海,去了香港,这一别就是几十年。王文忠始终不忘姥爷一家对他和他母亲的恩德。
1994年,姥姥去世,大姨给远在香港的王文忠发去一封讣告。
那时,大姨一家日子不好过,姨父工资不高,两个女儿都是极普通的工人。其中,大女婿到新疆下乡插队,大漠戈壁,刺痛了这位上海人的神经;肆无忌惮的风沙,让他愁眉苦脸;人烟稀少的荒凉,让他心灰意冷。马马虎虎干了几年后,他便不辞而别,扔掉工作,狼狈地跑回上海,生活愈加拮据。姥姥的去世,更是雪上加霜。一家人正遭遇困难之际,远在香港的王文忠,出手阔绰,一笔打来十二万美金,折合人民币近百万,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天文数字!面对巨额汇款,一家人由唏嘘引为豪叹。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王文忠也频繁回来,在大姨家落脚。大女婿见别人炒股发了财,也想四两拨千斤,结果赔得一塌糊涂。颓废自暴自弃时,王文忠对他开导,让他从小事做起,干点力所能及的小买卖。这些年他的买卖由小起步,逐步好转,一家人也安稳和谐。
母亲陈文昭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一个人的出身重要也不重要,关键得记住一句话,‘树无根不长,人无志不立’。”